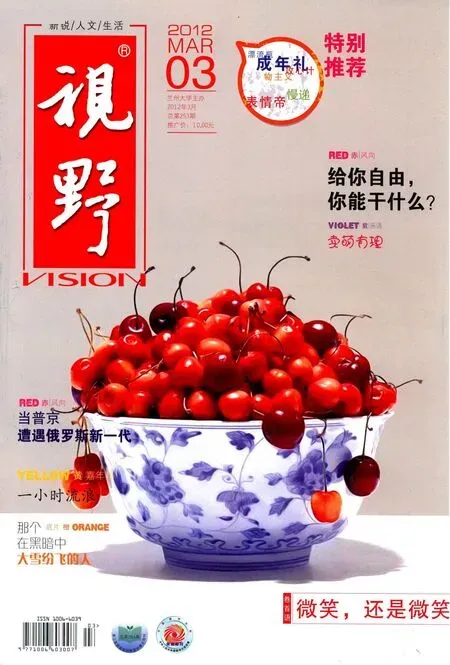古文驛館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春秋·孔子
賞評:用山、水類比和描寫仁、智,非常聰明和貼切。作為最高生活境界的“仁”,其可靠、穩(wěn)定、鞏固、長久有如山;作為學(xué)習(xí)、謀劃、思考的“智”,其靈敏、快速、流動、變遷有如水。真正聰明的人之所以常快樂,不僅因為能夠迎刃而解各種問題,而且因為了解人生的方向和意義而快樂。“仁”則似乎更高一層,已無謂快樂不快樂。他(她)的心境是如此平和寧靜、無所變遷,成了無時間的時間:壽。“樂山”、“樂水”,是一種“人的自然化”。“人的自然化”有好幾層意思。例如各種體育活動便有發(fā)展個體、肢體、身體的力量和能力,從社會異化中解脫出來(但今天的某些體育競技活動卻嚴(yán)重地被社會異化了),得到因它本身獲得實現(xiàn)而產(chǎn)生的享受和快樂。這種快樂不是社會性的如榮譽、成就等等的快樂,而是身體本身從而使心理也伴同的快樂。第二,即“樂山樂水”,回歸自然,免除各種社會異化,拾回失落感。它既是一種心境,也是一種身體心理狀態(tài)。第三,即由氣功、瑜伽等所達到的人與自然宇宙節(jié)律的同構(gòu)合拍。總之,“人的自然化”使人恢復(fù)和發(fā)展被社會或群體所扭曲、損傷的人的各種自然素質(zhì)和能力,使自己的身體、心靈與整個自然融為一體,盡管有時它只可能是短時間的,但對體驗生命本身極具意義。
流動不居(水)而又長在(山)。“紛紛開且落”,動亦靜;“日長如小年”,靜含動。生活情境如同山水,有此意象,合天一矣。此豈道德?乃審美也:主客同一,仁智并行,亦宗教,亦哲學(xué)。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春秋·老子
賞評:“道可道,非常道”用了三個“道”字,這三個“道”字屬于不同的語境,分別有不同的含義。第二個“道”是言說、用語言表達的意思。第一個“道”包含了天道和人道的雙重含義。簡單來說,日月星辰的運轉(zhuǎn)和四時的交替,都有著其中的規(guī)律,這就是天道;人間有需要共同遵守的規(guī)范,這就是人道。第三個“道”是“常道”,與第一個“道”不同,老子認(rèn)為第三個“常道”可以統(tǒng)攝天道和人道。而第一個“道”是現(xiàn)象界即經(jīng)驗世界建立一個規(guī)范、法則。不能光崇尚第三個道,注意本體、本根,發(fā)現(xiàn)前兩個“道”也至關(guān)重要。第一個“道”就像我們的地球村,這個經(jīng)驗的世界,有很多不同的紛爭,可以通過第二個“道”,討論、對話來溝通。
第三個“道”是“常道”,永存之道。我們現(xiàn)實世界的事物就是它的變動體。以前把“常道”翻譯為永恒不變的道,其實,“永恒”是對的,“不變”是錯的。老子的“道”是一個變體,所以《老子》中有一些話比如“反者道之動”,道是恒動的,是周行而不殆的,是“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的。有和無都是道體的一體兩面。所謂物固有形,形固有名,雖然無形但是存在的。比如手機響了,但是電波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我們的生存需要空氣,而空氣也是抓不到的。
萬事萬物有其源頭,本源、本根。作為本源、本根的“道”跟現(xiàn)象界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分割的,這是中國哲學(xué)與西方哲學(xué)的不同之處。西方哲學(xué)從柏拉圖開始就是本體界與現(xiàn)象界分開的,宗教上也有所謂彼岸、此岸,超自然與自然等等。自然兩極化,是西方哲學(xué)犯了兩極化的謬誤。相反,中國的宇宙觀則是有機聯(lián)系的整體。
對立關(guān)系不要把它絕對化,要相對性地對待對立關(guān)系。老子認(rèn)為相對關(guān)系是變化的,會轉(zhuǎn)化的,物極必反。反對絕對主義,唯我主義,獨斷主義。要有雙向思維,不要單向思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