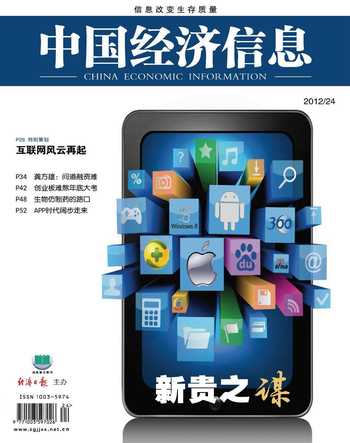金融創新的風險
徐建國
人們往往只看到了成功的創新,卻不太注意到每一個成功的創新之后都有很多個失敗的創新。
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羅伯特·席勒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演講的題目叫做“金融與美好社會”(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題目很有意思,基本的思想就是金融創新會幫助解決問題,構建一個更美好的社會。
席勒教授重點建議了五個金融創新,筆者的感覺是乍聽來很新鮮,但是大多經不起推敲,值得商榷之處頗多。
比如,席勒教授建議了一種叫做“Trill”的股票,每一股相當于一國GDP的萬億分之一,每年的“股息”也相當于一國GDP的萬億分之一。比如說,美國發行這樣的股票,那么看好美國經濟的人就會購買。更妙的是,美國政府就不用發行債券了。這就相當于是我國1998年那陣子搞過的“債轉股”。當時的目的在于幫助國有企業和銀行脫困,現在席勒教授的建議則旨在幫助美國和歐洲一些債臺高筑的國家脫困。
目的和意愿當然是好的,問題是如何實施?首當其沖的問題,是Trill的股利從哪里來?也就是誰出錢發這個股利。基本的常識告訴我們,公司發行股票的支撐物是凈利潤,是一個可以分配給股東的凈現金流,那么國家的“凈現金流”從哪里來?倘若把國家類必成公司,那么GDP就是每年的現金流,可是這個現金流不是“凈”的,而是各有其主的:工資歸勞動者,利潤歸資本所有者,租金歸特定的資產所有者,稅收歸政府。這里面并沒有“剩余”的“凈現金流”。那么誰會買一個沒有“凈現金流”的股票呢?實際上,歐美高負債國家不僅沒有凈現金流,其實現金流是負的,要不然就不會借那么多債了,他們實際上已經預支了未來的現金流。
所以,這個叫做“Trill”的新事物,大概很難叫做股票。倘若作為一種期貨,讓有意愿的人去對沖,看多的人做多,看空的人做空,相當于一個賭場,是一個零和的博弈,則是另一回事。不過,這樣就沒有了“債轉股”的功能,也幫不了債臺高筑的歐美政府。
而且,不知有意無意,席勒教授在提出這個想法的時候,好像忘記了他給本科一年級學生講解的關于資本結構的基本理論:債券的約束功能。簡單說,在一個公司融資的時候,如果通過債券融資,則公司需要定期還本付息,倘若不能履行償債義務則面臨破產風險。這樣一來,經理層就受到了約束,不能為所欲為。發股的話,則沒有這個壓力,因為股息是公司狀況好時才會分的。
倘若世界各國投資者,包括主權基金投資者,買的是歐美國家的“主權股票”,而不是國債,那就只能象無數中國股民一樣被“套牢”了,而且一點辦法都沒有,被逼得只好要求分紅。試問,強制分紅的股票,是不是有一點象債券?當然,你不能強迫破產清算。但是這種破產清算的威脅恰恰是債券給管理層的約束,可以促進公司管理和經營。
可見,席勒教授推薦的這個創新,在很多細節上需要推敲。其實很多技術和細節上經得起推敲的創新,現實中的效果也是不敢恭維的。例如,次貸危機愈演愈烈的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大量的信用違約對沖交易(CreditDefault Swap,簡稱CDS)。CDS其實技術上沒有什么問題,是一個不錯的新產品。可是,CDS客觀上幫助放大了金融危機,卻是一個事實。CDS的教訓是,一個產品本身可能沒什么問題,可是卻可能幫助放大其他問題。現實世界的復雜性,由此可見一斑。
我國恰逢金融改革的關鍵關口,利用金融創新來解決問題,當然是很有誘惑力的。可是創新一詞本來就包含了“嘗試”、“失敗”、“風險”這些聽起來不那么美好浪漫的可能。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的發展比較落后。作為后來者,仔細學習吸收先行者的經驗和教訓,穩中求進,或許是一條有效的道路。
曾經擔任過美聯儲的主席的保羅·沃克爾(PaulVolker)最近對金融創新有這樣一句評論:“近年來唯一有實際價值的金融創新就是自動柜員機(Automatic Teller Machine,ATM)。”這句話看似極端,但是出自保羅·沃克爾之口,讓人不得不深思。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