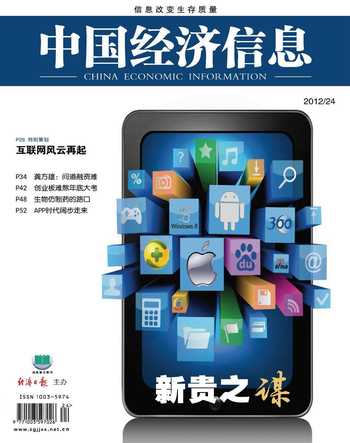中國制造面臨雙重危機
葉檀
中國制造業面臨雙重危機,一是低端制造業回流到東南亞、南亞等經濟區域,原有的產業鏈條被打斷;二是智能時代某些可以主用機器的制造業回流到美國。
過去一個世紀,工業中心從發達的西方國家逐漸轉移到東亞,上世紀70年代,制造業中心從日本轉移到亞洲四小龍(香港、臺灣、韓國和新加坡),上世紀90年代,制造業中心從亞洲四小龍轉移到中國。由于最近幾年中國的工資水平經歷了快速增長,制造業的接力棒正在從中國轉移到成本更低的“東盟七國”手里,即是泰國、菲律賓、越南、印度尼西亞、老撾、柬埔寨和緬甸。
美國最新一期《大西洋月刊》雜志,以美國制造業回流為主題,同時登載兩篇以流向變化分析近期制造業趨勢的文章。其主旨是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中國人力成本快速上升導致廉價優勢的削弱,使低端制造業外流;另一方面,美國智能時代的再工業化,使這一波美國國內制造業復蘇具有與以往不同的特征,并非經濟周期的簡單反映,這一變化值得國人密切關注。
在“內包繁榮(The Insourcing Boom)”一文中,Charles Fishman以GE在肯塔基的工業園區從五十年代以來的興衰為例,描述了一幅美國制造業復蘇的圖景。
該工業園區建于1951年,到九十年代,這一園區使然成為GE的雞肋,這是美國制造業夕陽西下的典型故事。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今年以來連續有新的生產線開張。究竟是哪些因素使得GE可以抗拒公認的廉價及高效的勞動力呢?這一案例提供的答案是,技術革新與能源消耗。這一案例的背后是幾個大環境改變:
石油價格高漲使的運輸成本成倍增長;美國天然氣繁榮使美國工廠能源費用減低,這也是美國不會出現上世紀70年代滯脹的主要原因;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美國工會近年的政策調整,及美國工人生產率的提高使得人工成本在產品中比重逐年下降。
制造業內包這一現在尚未大規模產生的現象,是否會在美國進一步擴展,還有待觀察。無論如何,隨著智能制造時代與新能源時代的到來,某些智能制造重新轉移回美國是大勢所趨。
可以肯定的是,創新需要寬松的環境和基本的制度保障。歷史上許多國家多次失去利用創新機會,重要的原因是舊有的從業人員對崗位可能被新技術取代的天然恐懼。
而在另一篇題為“Mr.Chinacomes to America”的文中,著名資深評論James Fallows根據他多年在中國國內的走訪經驗,向公眾指出,某些制造業從中國流向美國的可能模式。
在互聯網的幫助下,產品從設計生產到銷售服務的各個環節正在經歷一場變革。其中的特征是從點子到產品越來越容易成現實,而每一產品升級淘汰周期卻在縮短,以往的周期大概是幾個月,而今可能是幾個星期,在當地生產具有明顯的去物流成本優勢。
以舊金山為例,近年集中出現了一批新興高科技和針對特殊品位喜好者的小型制造企,大都由幾個剛出校門的年輕人創立,自己就地生產。目前已出現一個名為SFMade的聯盟,加盟的四百多家企業雇有大約三千多工人。其中120多家是在過去三年內成立,而他們的雇員去年增長10.5%,今年是12.5%。這些企業并不都從事高科技行業,其中不乏專門設計制造跟當地歷史文化有關的產品,也有可能面向中國觀光客人的紀念品。這一模式的要點是極快的設計、面世、用戶反饋過程。我們有理由憧憬這些小企業會產生下一代的蘋果和谷歌。
新一代智能制造與快速反應技術,降低了產品設計、制造的門檻,對市場的快速有效反映成了搶占市場的制勝法寶。這在中國的快消品領域同樣有所反應,只不過,市場對創業者遠遠稱不上友善。
中國必須借全球產業轉移契機,在中端制造領域占據一席之地,嵌入全球產業鏈中,這是未來中國制造的生路。
作者系財經作家,著有《拿什么拯救中國經濟》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