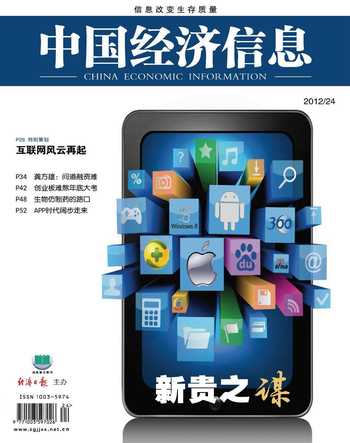中澳合作“錢景”可期
傅云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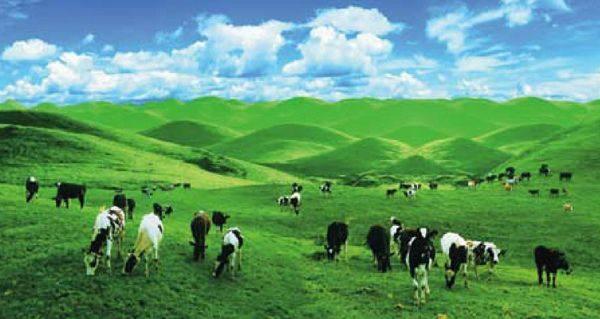
今后澳大利亞對華所求或將大于中方對澳所求,對澳經濟而言,中國投資將日益成為一種稀缺資源,今后澳方對華投資限制或有條件出現松動。
現如今,對很多國人而言,“限購”下在澳大利亞買嬰兒奶粉已不是件好差事,這個過程有時充斥著無奈乃至羞辱感。針對性的限購政策、冷若冰霜的超市店員、路人詫異的眼神,時常讓人有斯文掃地、無地自容之感。一位消費者對記者講道,比起體力消耗,精神上的煎熬更讓人難受。
事出有因。在悉尼市中心Woolw?orths超市工作的約翰告訴記者,每撥中國游客光顧之后,超市各段嬰兒奶粉會出現不同程度的缺貨乃至脫銷。據他說,為維護必要的市場秩序,超市一度規定每位游客每次只能購買4罐,即使這樣也無濟于事,因為中國人似乎不在乎多跑幾趟。
這樣的現象的背后,是中澳乳業合作嚴重滯后,澳乳品對華市場渠道不暢,澳乳業投資不足,制造業日漸式微,產量受限等深層次問題,當然,更主要的是澳商人未充分認識到中國的更大市場需求。
據澳大利亞乳業局(Dairy?Australia)統計,2010至2011年度,澳大利亞乳業產奶量為91.01億公升,奶粉產量為37.38萬噸,乳品出口額為27.5億澳元,占全球乳品貿易份額8%。
事實上澳大利亞不是不想出口,而是能力不足。盡管在氣候、草場、牛種等資源領域得天獨厚,多年來,澳乳品行業明顯存在資本金不足、生產效率不高、深加工能力有限、產品附加值不高、品牌戰略缺失和抗風險能力薄弱等先天不足,嚴重制約了其國際競爭力和發展后勁。
據記者調查,目前市場上鮮有國際知名的澳大利亞自主品牌奶粉,也鮮有來自中國等發展中大國的乳業投資項目。因受到大零售商擠壓,目前澳鮮奶零售價每公升僅1澳元,批發價則更低廉。鮮奶價格甚至遠低于瓶裝水,不少中小奶農處于虧損邊緣。
分析人士指出,這種國內惡性競爭、國際市場難有突破的局面表明,澳乳業發展亟待以外來投資促整合,以整合促產業升級。
合作臨界點
產業升級首先需要的就是資金支持。澳大利亞Sinogie咨詢公司首席執行官布魯斯?邁克勞林指出,許多澳大利亞農牧業公司以及家族農場在融資方面“營養不良”,它們無法從本國資本市場獲得新融資,唯一現實的選擇就是外國投資。他說,沒有外國投資,農牧業就無法獲得新的設備,無法從事商業活動,無法實施擴張,無法提高效率以及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而中國既能帶來巨大的市場,又能帶來投資。
據統計,中國每年從澳進口10.3萬噸乳品,其中多數為奶粉,且進口量仍在飛速增長。市場分析人士指出,今后數年中國很可能超越日本成為澳第一大乳品出口市場。
同時,目前在澳中國投資僅占澳方吸引海外投資總額的1%,而歐美投資的這一占比卻高達80%以上。從2006年到2012年,中國對澳投資451億美元,其中近80%的投資為礦業項目,12%的投資為油氣項目。
上述數據表明,較之歐美國家,中國在澳投資的總體規模相當有限,與中國作為澳頭號貿易伙伴的地位很不相稱;同時也說明,中國在澳投資過于集中,缺乏多樣性,兩國在投資領域合作潛力巨大,亟待拓展和深化。
正如澳大利亞通訊部長馬爾科姆?特恩布爾所言,在農牧業領域,澳方有擴大產能、提高效率的需求,中方則擁有巨大市場需求。
可以說,兩國投資合作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或拐點。特恩布爾指出,這一時期何去何從,將決定兩國投資合作的長遠走向。雙方亟待增加溝通和互信,突破發展瓶頸。
意識形態心結
中澳農牧業合作方面有著現實的需求和巨大的潛力,但是近年來,雙方在這一領域的合作并不順暢,中糧、光明食品、山東如意等中資企業對澳農牧業頻繁表現出收購意向或行動,其過程艱辛復雜。
中國駐悉尼總領事館商務參贊凌桂講到,造成中資舉步維艱的根本原因在于某些澳大利亞人頭腦中“念念不忘的意識形態”。例如,中國的奶業投資就是因為涉及土地所有權轉移等敏感問題,屢屢受限。凌桂如認為,要改善投資環境,吸引更多中國投資,澳方就需解開意識形態的心結。
另外,中國投資的某些特征比較惹眼,也容易引來澳監管當局的格外“關照”。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和悉尼大學日前聯合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指出,中國對澳投資以國有企業為主,多集中于大型項目,且偏好投資上市公司。上述特征很容易讓人浮想聯翩,以為中資行為受中國政府指導而非出于商業目的,這會引起無端的猜疑和焦慮。
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道格?弗格森指出,事實上,中國國有企業的海外行為很多方面與跨國公司無異,它們的投資決策更多取決于利潤而非政治考量。“實踐證明中國投資者可以成為創造就業的積極貢獻者,澳方應更為務實而細致地了解中資企業,這有助于消除疑慮,更多地受益于中國投資。”他說。
對此,澳大利亞資源、能源部長兼旅游部長馬丁?弗格森說,近期某些政治家就海外投資發布了消極言論,這無助于澳大利亞贏得像中國這樣的市場。澳大利亞需要對來自中國的投資更加開放。他呼吁相關政黨領袖拿出務實姿態,停止向國際社會發布無益的“混淆信息”。
中國投資將成為稀缺資源
除雙方戰略層面的互信,要讓澳方對中資“脫敏”,技術層面的拿捏同樣重要。
凌桂如指出,中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必須努力學習澳大利亞法律、法規,適應當地商業文化。比如,相關企業可強化本土化策略,更多融入澳主流社會;也可適時考慮放棄中國企業青睞的全資控股方式,轉而通過部分控股的辦法實施投資。
他認為,駐澳中資企業還應當適時對外公開其經營管理情況、業務增長目標等細節情況,有時候大大方方比遮遮掩掩更加明智,會更容易贏得監管當局信任,更容易為當地主流所接受。
凌桂如還說,中資企業在進行對外宣傳時,也應當注意淡化“國有”背景,而要以國際化企業的面目示人。譬如,某些企業在海外還熱衷于對外展示“領導關懷”,這類國內常見的宣傳手法確實需要改一改。
就澳方監管政策,邁克勞林指出,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FIRB)的某些規定讓人困惑,亟待改觀。他舉例說,據規定,外資收購資產規模為2.43億澳元企業90%的股權時,不需申請當局批準;而外資收購資產規模為2.5億澳元企業20%的股權時,就需申請批準。他介紹說,在農業投資領域,上述性質的怪異規定大量存在,阻礙了中資進入。
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增強,大宗商品價格跌落,澳大利亞貿易條件走軟,中國經濟結構調整、對外投資放緩背景下,中澳之間十多年來的經貿互動態勢正發生微妙變化。一些分析認為,今后澳方對華所求或將大于中方對澳所求。對澳經濟而言,中國投資將日益成為一種稀缺資源,今后澳方對華投資限制或有條件出現松動。
分析人士據此指出,在此關鍵節點,中方相關部門適時發力,促進對澳雙方貿易與投資,無疑有利于中資乘勢而上,加緊控制澳大利亞土地等戰略資源,有利于我國鞏固農產品的供應安全,有利于實現中澳經貿更深入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