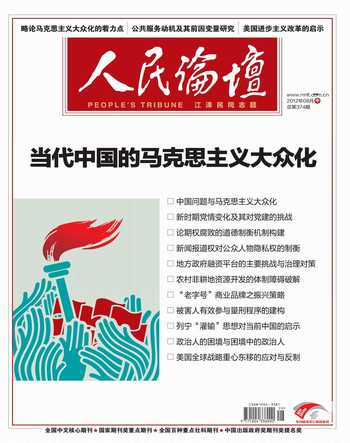論勞動權(quán)的保障及其完善
趙寶華
【摘要】勞動權(quán)保障在我國工業(yè)化浪潮中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公權(quán)力在其中扮演著決定性的作用。近年來,勞動關(guān)系矛盾的發(fā)展表明我國公權(quán)力在保障公民勞動權(quán)方面還要不斷加強(qiáng)。首先,完善勞動權(quán)的立法保障必須轉(zhuǎn)變理念,樹立勞動者利益為先的指導(dǎo)思想。其次,要彌補(bǔ)立法漏洞,加強(qiáng)立法的可操作性,全面負(fù)起保障公民勞動權(quán)的職責(zé)。
【關(guān)鍵詞】勞動權(quán) 社會權(quán) 合法權(quán)益
勞動權(quán)是人權(quán)的重要組成部分,基本含義是指有勞動能力的公民有獲得參與社會勞動和領(lǐng)取相應(yīng)報酬的權(quán)利。在人權(quán)的發(fā)展史上,它屬于第三代人權(quán),即社會權(quán),是獲得生存權(quán)的必要前提和保障。由于在勞動權(quán)法律關(guān)系中,權(quán)利人是公民,義務(wù)人是國家,也因?yàn)閯趧訖?quán)直接導(dǎo)致私有財產(chǎn)權(quán),所以,作為公民個人享有的勞動權(quán)還帶有更多的私權(quán)因素。由此可見,勞動權(quán)相對于公權(quán)力的擁有者—國家來說,是一種積極人權(quán)。而國家作為公權(quán)力的代表,有義務(wù)保護(hù)公民的勞動權(quán),有責(zé)任為公民勞動權(quán)的實(shí)現(xiàn)提供條件。
勞動權(quán)保障的特質(zhì)
據(jù)史尚寬先生的論述,勞動關(guān)系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即為勞動力由權(quán)利客體進(jìn)至主體地位,并與勞動者本身的人格合一的過程。這一論述,揭示了勞動權(quán)區(qū)別于人身權(quán)和財產(chǎn)權(quán)的獨(dú)有特質(zhì)。人身權(quán)和財產(chǎn)權(quán)的實(shí)現(xiàn)是基于平等自愿、等價和誠實(shí)信用原則,勞動權(quán)的實(shí)現(xiàn)表面上也要基于民事權(quán)利實(shí)現(xiàn)的這些原則,但是勞動權(quán)的平等,具有一種觸發(fā)性,即一旦勞動關(guān)系正式建立,勞動關(guān)系的平等性即為隸屬性所替代。當(dāng)然,這種替代是一個量變的過程,是在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形成一種權(quán)力關(guān)系,即勞動者隸屬于用人單位,勞動合同一旦簽訂下來,勞動者與用人單位的勞動關(guān)系就變?yōu)殡`屬性為主、平等性為輔。同時,用人單位對勞動力的使用會帶來高于原定勞動力價格的財富,這些都決定了勞動權(quán)實(shí)現(xiàn)的獨(dú)特性。勞動權(quán)一般是以個體的形態(tài)存在的,勞動權(quán)是在一種雙方地位懸殊、勞動者處于弱勢和服從地位、勞動商品使用帶來的增值信息不對稱的情形下實(shí)現(xiàn)的。因此,勞動權(quán)必須要求第三方的保障,特別是對用人單位用工行為進(jìn)行規(guī)制。
社會權(quán)理論的產(chǎn)生,就是雇傭勞動發(fā)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后,由人權(quán)保障現(xiàn)實(shí)催生的。社會權(quán)不同于傳統(tǒng)的自由權(quán),自由權(quán)要求國家不作為,給公權(quán)力劃定非請莫入的范圍。而社會權(quán)則要求公權(quán)力積極介入,比如勞動權(quán),勞動者沒有公權(quán)力支持,就無法與強(qiáng)勢的用人單位相抗衡,甚至無法防御來自用人單位的或明或暗、或軟或硬的侵害。
那么,在勞動權(quán)的保障方面,公權(quán)力的積極介入要達(dá)到什么程度呢?這種程度取決于國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即國家財力狀況。就各國保障社會權(quán)的立法所共同承諾的情形來看,一般都以“使國民享有維持健康且文化性的最低限度生活”的標(biāo)準(zhǔn)為限。而這種標(biāo)準(zhǔn)又具有強(qiáng)烈的不確定性,特別是像中國這樣各地區(qū)經(jīng)濟(jì)發(fā)展水平極不均衡的社會。于是,各地方政府,甚至具體到區(qū)縣政府都要履行自己保障勞動權(quán)的職責(zé),確定本管轄區(qū)域內(nèi)的最低工資標(biāo)準(zhǔn)和最低生活保障線。
作為社會權(quán)的勞動權(quán),其不確定性還表現(xiàn)在權(quán)利內(nèi)容上。公民有勞動的權(quán)利,但這往往表現(xiàn)為一種國家的義務(wù),個人不能向政府要求給予就業(yè)崗位。而政府作為公權(quán)力的持有者只能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jī)會吸引無業(yè)或失業(yè)的公民去有關(guān)用人單位應(yīng)聘。
憲法對勞動權(quán)的確認(rèn)及勞動立法
公權(quán)力對勞動權(quán)的保護(hù)首先體現(xiàn)在憲法中。其正式全面入憲是在《德國魏瑪憲法》中,二戰(zhàn)后被聯(lián)合國1948年《世界人權(quán)宣言》所承認(rèn)。在我國,勞動權(quán)的確認(rèn)和保護(hù)也經(jīng)歷了一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lǐng)》中,只在第八條中規(guī)定了人民的“遵守勞動紀(jì)律”的義務(wù)。1954年憲法規(guī)定了公民的勞動權(quán)和休息權(quán)以及獲得社會保障的權(quán)利。但是在人權(quán)保障上,沒有對公民基本人權(quán)邊界的明確規(guī)定,也沒有保障方式的規(guī)定。
1975年憲法將公民勞動權(quán)和獲得物質(zhì)幫助的權(quán)利并列作為第二十七條的一款,而對于權(quán)利的邊界和權(quán)利保障的方式,沒有條文體現(xiàn)。1978年憲法在勞動權(quán)方面不僅原則性地規(guī)定了公民有勞動權(quán),而且明確強(qiáng)調(diào)了國家在安排勞動就業(yè)方面的義務(wù);還規(guī)定了公民的休息權(quán),強(qiáng)調(diào)了國家在限制勞動者工作時間和建立法定休假制度方面的國家義務(wù);同時規(guī)定了公民有獲得物質(zhì)幫助的權(quán)利,國家在建立公民社會保障方面的義務(wù)。
1982年憲法在勞動權(quán)的規(guī)定方面,首次明確地將勞動定位為公民的義務(wù),不只是權(quán)利,這在我們民族憲法史上還是第一次。2004年憲法修正案增加了概括性地保障人權(quán)的條款,這是1949年以來憲法中人權(quán)保護(hù)發(fā)展的最高點(diǎn)。
從以上憲法文本上看,勞動權(quán)為各個時期的憲法在不同程度上獲得了肯定,其內(nèi)涵也逐步豐富。從勞動立法上看,建國之初,勞動部相繼頒發(fā)了《救濟(jì)失業(yè)工人暫行辦法》、《關(guān)于勞動爭議解決程序的規(guī)定》,政務(wù)院頒布了《勞動保險條例》。這些法規(guī)在調(diào)整勞動關(guān)系方面發(fā)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在1956年以后,勞動爭議機(jī)構(gòu)被相繼撤銷,勞動爭議處理改由人民群眾來信來訪的方式處理,上述法規(guī)被棄之不用。
隨著改革開放的實(shí)行,勞動立法迎來了大發(fā)展的時代。1978年到1982年短短幾年間,國家就頒布了450余件勞動方面的規(guī)范性文件。1994年7月,歷經(jīng)30余次修稿的勞動法草案終于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奠定了我國勞動法制的基礎(chǔ)。隨后國務(wù)院相繼頒布了有關(guān)工作時間、工資支付、工資集體協(xié)商、勞動監(jiān)察、社會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方面的勞動法規(guī),充實(shí)和完善了勞動立法。進(jìn)入21世紀(jì),為了適應(yīng)新形勢,勞動立法加快了步伐。2002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安全生產(chǎn)法》,2007年《勞動合同法》、《就業(yè)促進(jìn)法》和《勞動爭議調(diào)解仲裁法》相繼出臺,2010年《社會保險法》出臺。這些重要法律的頒布施行,健全了勞動法律法規(guī)體系,促進(jìn)了對勞動權(quán)的立法保障。
公權(quán)力在保障勞動權(quán)方面要積極作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同時也積累了大量的社會矛盾,而基于勞動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矛盾也已逐漸成為我國諸多社會矛盾的一部分。國家工商總局的材料顯示,到2010年底,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yè)吸納的就業(yè)人數(shù)占全部新增就業(yè)人數(shù)的90%;很明顯,非公有制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的勞資關(guān)系已經(jīng)成為我國勞動關(guān)系的主體。2010年前三個季度,各級勞動爭議仲裁機(jī)構(gòu)共受理勞動爭議案件約44.3萬件,是2007年勞動爭議仲裁機(jī)構(gòu)受理案件35萬件的126.6%。這些數(shù)據(jù)都表明,我國已經(jīng)進(jìn)入一個勞動關(guān)系矛盾高發(fā)、多發(fā)期。同時,勞資矛盾也正在影響著社會的和諧穩(wěn)定。在2008年釀成的“群體性事件”的各種因素中,勞資關(guān)系排在第一位。另據(jù)北京市第一中級法院統(tǒng)計,2009年勞動爭議案件涉案勞動者的平均年齡為37歲,低于2008年39歲的平均年齡,其中35歲以下的勞動者比重也在不斷加大,2009年已達(dá)到42.3%。
這表明公權(quán)力對勞動權(quán)的保障還很不夠。無論用人單位侵害勞動者合法權(quán)益,藐視踐踏勞動法,還是執(zhí)法部門執(zhí)法不嚴(yán),對勞動違法懲處不力,解決問題的核心都在勞動立法的完善上。
首先,在指導(dǎo)思想上,立法應(yīng)進(jìn)一步向勞動者利益保護(hù)上傾斜。因?yàn)楫?dāng)前勞動關(guān)系矛盾主導(dǎo)方在于用人單位,而勞動權(quán)的社會權(quán)屬性必然要求公權(quán)力的保護(hù)。更為重要的是,我國實(shí)行的根本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所有改革都不能脫離這個基本國情,不能超越它,否則就不能稱之為完善的改革。以前我們僅僅把勞動關(guān)系視為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關(guān)系,這忽視了勞動權(quán)的特質(zhì),將勞動爭議應(yīng)用一般的民事訴訟程序進(jìn)行審理,是需要在立法上進(jìn)行糾正的。
其次,公權(quán)力應(yīng)當(dāng)積極介入,切實(shí)擔(dān)負(fù)起保護(hù)勞動者權(quán)的職責(zé)。改革開放以來,放松管制保障企業(yè)的經(jīng)營自主權(quán)的改革,取得了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良好成績。同時,勞動力的低成本更是經(jīng)濟(jì)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但是長期的勞動力低成本,使勞動者不能享受改革開放、經(jīng)濟(jì)發(fā)展所帶來的成果,已經(jīng)成為引發(fā)勞動爭議的最主要因素。目前看來,勞動關(guān)系矛盾的頻發(fā)已經(jīng)嚴(yán)重影響了社會公正,問題正在演變成強(qiáng)資本弱勞工情勢下的勞動者維權(quán)困境。而國家目前仍沒有出臺工資法、勞動監(jiān)察法等切實(shí)體現(xiàn)公權(quán)力節(jié)制資本、保障勞動者權(quán)益的法律,這就使得用人單位認(rèn)為欠薪不需要承擔(dān)法律責(zé)任,甚至,只要沒證據(jù)證明用人單位惡意欠薪,清欠以后他們還可以被當(dāng)?shù)卣頁P(yáng)。由此可見,公權(quán)力的掌握者確實(shí)需要加強(qiáng)自身在勞動權(quán)性質(zhì)方面的理論素養(yǎng)。
最后,在勞動權(quán)保護(hù)方面,其核心問題仍然是勞動收入分配不合理。據(jù)有關(guān)資料,近年來,我國企業(yè)工人的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急劇下降,從2000年的51.4%降到了2007年的39.7%,七年的時間下降了11.7個百分點(diǎn)。改變這種狀況,政府責(zé)無旁貸。除此之外,政府還需要在勞動保障、勞動者組織、勞動監(jiān)察等方面建立健全相關(guān)制度,切實(shí)負(fù)起保障勞動者合法權(quán)益的責(zé)任。
(作者為濰坊學(xué)院法學(xué)院副院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