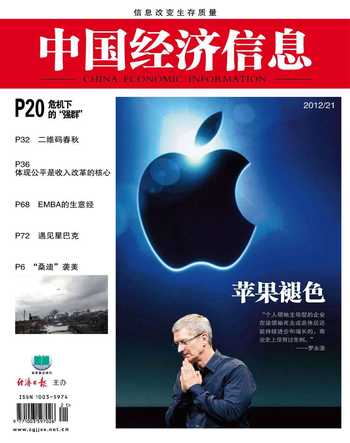小步跨越導向繁榮之路?
馬丁?沃爾夫
一個國家必須胸懷大志,但決不能想一口吃成個胖子。這種想法很好地概括了新加坡和韓國等國的發展歷程。
不久前卸任世界銀行(World Bank)首席經濟學家一職的林毅夫(Justin Lin),寫了一本既雄心勃勃又優秀的書:該書旨在為經濟發展指明道路。說它雄心勃勃,是因為自經濟學誕生以來,為經濟發展指明道路就是該學科孜孜以求的目標。說它優秀,是因為這位中國經濟學家總體上論述得很成功。你不一定要認可林毅夫的所有主張,但你得承認,他的這番貢獻具有極高的價值。
林毅夫思想的主要特點是務實。作為中國已故領導人鄧小平的崇拜者,林毅夫也信奉“不管黑貓白貓,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他認同市場力量的決定性貢獻,但同時也主張政府有責任將這些力量推向正確的方向。他認為,只有這樣,貧窮的國家才能通過漫長的努力實現繁榮。
更確切地說,該書倡導“新結構經濟學”。該學說與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影響經濟學家的舊結構經濟學有所區別,也與芝加哥學派的新古典經濟學有所區別。林毅夫上世紀八十年代曾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求學。
與舊結構經濟學相同的是,林毅夫倡導的學說也認識到了企業家無法獨力克服的經濟發展障礙的重要性。但與舊結構經濟學相反的是,受自身教育背景和東亞經歷影響的林毅夫,還提到了利用一國比較優勢的重要性。他拒絕接受他所謂的“違背比較優勢”的戰略,這種立場與新古典經濟學相符。但他同時還強調了積極的政府在引導經濟、克服經濟持續發展之障礙中發揮的作用。這就是非正統的思維了。
不過,這種思想如何轉化為實際政策?在林毅夫所說的“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框架”(Growth Identification and Facilitation Framework)中,我們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框架分為六步。首先,為本國挑選一個參照國,參照國應與本國有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但人均實際收入為本國的兩倍。然后,找出參照國過去20年一直在增長的可貿易行業。其次,如果國內企業在這些行業已經很活躍,那就找出進一步升級和新企業入行的瓶頸限制,然后采取行動消除它們。第三,如果國內在這些行業不存在活躍的企業,那就吸引外國直接投資(FDI)進入這些行業。第四,找出國內企業已獲得成功的行業,扶持這些企業進一步發展:改善基礎設施或支持研發都是可能的選擇。第五,在基礎設施和營商環境較差的地方,將活動聚集在經濟特區或工業園區。第六,向先行企業提供有時間限制的激勵。
框架的基本想法是,發展可以走“小步跨越式”道路——這是有道理的。一個國家必須胸懷大志,但決不能想一口吃成個胖子。這種想法很好地概括了新加坡和韓國等國的發展歷程。
林毅夫把他的框架應用于一些明顯的挑戰:前社會主義經濟體的改革歷程,以及那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的困境。他的一些說法很有趣。但他提出的、葉利欽(BorisYeltsin)曾面臨與鄧小平相同政治經濟選擇的假設,卻很難說服我。
實際上,我們并不清楚這是否是一種普適的經濟發展理論。例如,林毅夫忽視了“合成”問題:讓每個窮國都在同一時間遵循相似的發展道路可能有較大難度——全球對服裝的需求量能有多高?我的另一項異議是,他低估了在資源型行業(包括農業)擁有比較優勢的國家所面臨的問題。還有一個難點是,某些國家面臨格外難以消除的瓶頸限制:被基礎設施不足的貧窮鄰國環繞的內陸國家就是明顯的例子。同樣,林毅夫還忽視了當世界各國都在發展時出現的資源瓶頸
不過,這只是些瑣碎問題。毋庸置疑,林毅夫的學說是一項重要的貢獻。也許是身為內部人士的緣故,林毅夫對東亞發展道路何以成功的解釋,比其他任何人都精辟。當然,他的學說存在一個條件,即政府要能干且富有支持性。但是,如果沒有這一條件,發展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取得成功的。
作者系英國著名經濟評論員、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