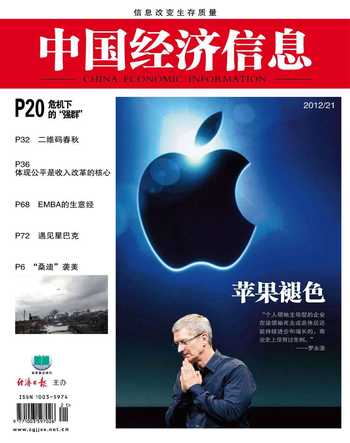西方“白領”的生存狀況
白旭 李雪笛 傅云威 楊琪
他們行色匆匆,奔向城市的高樓大廈,女子妝容精致,男子西裝革履;他們和電腦、電話在一起的時間,要比和朋友在一起的時間多很多;在競爭殘酷的現代社會,他們是城市的中堅力量;他們很忙,他們掙得也不算少,這個階層被稱為“白領”——他們過著令很多人羨慕的生活,但其中的艱辛,冷暖自知。
倫敦:工作十年買不起房
英國的“白領”不難辨認。站在街上,如果你看到西裝革履提著公文包的男人,或者身穿正式裙裝的姑娘,那八成就是了。
伊恩·邁爾斯就是一位典型的英國“白領”。他來自格拉斯哥,在倫敦一家知名的公關公司工作。
“我喜歡倫敦,因為這里有很多的機會,人們總說,‘倫敦的道路是金子鋪成的。”他說。
邁爾斯從小在鄉下長大,現在生活在倫敦,他的抱怨也不少,“倫敦的節奏太快了,平時總是要加班,到六七點鐘才能回家,最晚的時候要到10點。”
在英國人的傳統中,周末是盡量不工作的。“上帝用了六天創造了萬物,第七天的時候,他認為該休息了。”盡管邁爾斯不是嚴格的基督徒,但他非常喜歡這個解釋,因為他覺得,正是這個解釋讓英國的“白領”們至今仍保持著周末享受家庭生活的習慣。
其實在工作日,忙碌了一整天之后,“白領”們到了晚上也很愿意進行一下社交活動。邁爾斯說,“我們通常會找一家不錯的酒吧,約上三五個好友,要上一杯啤酒,一起談天說地。”
邁爾斯坦言,他的生活也有壓力,主要體現在住房上。
他現在和女朋友一起住在倫敦西南部的切爾西。房子是他媽媽十年前買下的,邁爾斯以付房租的形式每個月給媽媽一些錢供她還房貸。
邁爾斯的房子距市中心有些距離,因此不是很貴,但是目前也要4500鎊一平米(約合人民幣4.5萬元),這個價格已經比當初購買時漲了25%到30%。
“我是名牌大學畢業,在一家知名的大公司,工作了十年仍然買不起房子,其他人的生活壓力就可想而知了。”像邁爾斯這樣的年輕“白領”,月收入大約為2000多英鎊(約合2萬元人民幣)。
東京:還是一個人過日子手頭寬裕
日本的“白領”主要指在公司有固定工作并且領取固定工資的人。“白領”聽起來很誘人,但在日本人眼中,這兩個字總會牽出一絲憂傷和無奈。
大塚畢業于東京名校,2012年春天在一家大型上市公司謀得了一份工作,半年時間,他已逐漸從學生轉型為一個標準的“白領”。在日本公司里,通常是等級森嚴,規章制度名目繁多,這無時無刻不讓人感到壓力很大。
相比于男性,日本的女性“白領”會輕松不少。緒方馬上就要工作滿5年了,她在公司主要負責打理部門日常雜務,標準的朝九晚五,有時上司還會讓她提前下班。
緒方擁有仔細打理過的栗色卷發、精心修飾過的指甲和一副甜美的笑容,為了保證每天都光彩照人地出現在同事面前,她早晨要提前兩小時起床化妝打扮。
在日本,不少女性結婚之后會立刻辭去工作,所以公司一般不會對女性員工委以太重要的工作,她們也很難得到升遷。如果女性想要出人頭地,要付出比男性更多的努力。緒方覺得,作為女孩子沒必要讓自己太累,她寧愿在穿衣打扮上多花些心思。
在日本,除了公司高層以外,普通“白領”的薪水與年齡基本成正比。根據日本國稅廳2010年的統計,大學畢業生的平均年收入約為250萬日元(約合20萬元人民幣),50~54歲時達到最高值,在650萬日元(約合52萬元人民幣)左右。
大塚每月的工資為20萬日元(約合1.6萬元人民幣)出頭,發到手里之前會被扣掉兩成用來支付健康保險、失業保險、養老金和所得稅。而租房、伙食費和交通費等生活成本又要占去剩下的一半多。和同事出去喝酒時,大塚一般采用AA制,去的次數多了,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
他現在還打算存錢買車,最后算下來每月自己可自由支配的額度為2萬~3萬日元(約合1600元~2400元人民幣)。他周末不太出門,宅在家里看電視打游戲比較省錢。
與大塚和緒方相比,在一家公司擔任中層管理人員的前田是個有房的“白領”。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繁榮,房價不斷攀升,他在那個時候貸款買下了一套公寓。但90年代之后,日本經濟開始陷入衰退,如今,前田的房子舊了,房價也跌了近乎一半,他卻還有每月15萬日元(約合1.2萬元人民幣)的房貸沒有還完。前田說,這么多年過去了,政府也換了許多屆,但經濟仍并不見起色,現在他的工 資已大不如前,還得努力工作多攢些錢養老。
悉尼:“拿手術刀的不如拿鐵鍬的”
在澳大利亞,典型的“白領”指的是有一定的專業素養,擁有較為穩定、體面的工作和收入,追求時尚,定期參加體育鍛煉,愿意從事公益、環保活動的都市工薪階層。
朱莉亞就是這個群體中的一員。她住在悉尼的CBD,供職于一家全球500強公司,崗位是文員。朱莉亞年薪大約7萬澳元(約合45萬元人民幣),收入水平在澳大利亞屬中等偏上。
除去稅收,朱莉亞每年可支配收入為4萬多澳元(約合26萬多元人民幣)。但她每月要支付住房按揭貸款,還要扣去吃、穿、水電、交通和通訊等用度,可以說所剩無幾。
雖然日子不甚寬裕,但朱莉亞依然身兼物業管理委員會成員的角色,積極投身公益。她說,代表居民同物業公司交涉停車、用水、用電、公共區域裝修等事務完全是志愿,沒有報酬。她還說,在澳洲,投身公益是一種文化。
與朱莉亞一樣,愛麗絲也是一位“白領”。不同的是,在悉尼擁擠的街頭,常常能看到她頭戴安全帽,手舉交通標識。
愛麗絲平時在一所大學從事行政工作,是典型的“白領”職員。經建筑行業的朋友介紹,她在業余時間接受了建筑業資質培訓,而后常在相關領域找些零工,補貼家用。
愛麗絲說,最常見的工作是在施工地點臨近的道路上設立標識,或手舉標識疏導車輛和人流。這種工作按小時計費,一般每小時50~70澳元(約合320元~450元人民幣),周末或晚間收入更高。
但近十多年來,在新興經濟體旺盛需求的支撐下,澳大利亞的資源能源產業贏來了百年難遇的繁榮發展,隨之而來的,是礦工、建筑工人等工程類“藍領”的薪資大幅上漲。他們的收入開始超越一些行業的“白領”,他們也開始躋身社會高收入階層。
根據Suncorp銀行新近發布的報告,當前,澳大利亞“藍領”人士平均工資為每周1229澳元(約合8000元人民幣),較“白領”人士高144澳元(約合900元人民幣)。在澳大利亞報酬最高的10個行業中,6個是“藍領”行業。
澳大利亞統計局的相關數據表明,“取得大學學位方能謀求高薪”的觀念已經過時。統計數據顯示,在西澳大利亞的油氣開采企業,雇員的平均工資為每小時75澳元(約合485元人民幣),每周可掙得3000澳元左右(約合19000人民幣),年薪超過10萬澳元(約合64萬元人民幣)。而一個澳大利亞醫生每小時的報酬為68.5澳元(約合443元人民幣)。“拿手術刀的不如拿鐵鍬的”,這句曾經的笑談,如今正在澳大利亞變為現實。
實際情況可能比統計數據更具說服力。據了解,昆士蘭州西北部的伊薩山礦區的礦工收入更高。在當地一處銅礦開車的保羅告訴記者,他每年能掙15萬澳元(約合97萬元人民幣),他的同事甚至能掙20萬澳元(約合129萬元人民幣)。
在西澳大利亞首府珀斯,不時能看到休假的礦工和他們的家人出入星級酒店等高檔場所消費。當礦工們脫下制服,開上房車,在海邊沖浪,或在綠茵上揮動高爾夫球桿時,若不是因為他們曬得發紅的臉龐,你絕猜不出他們是“藍領”還是“白領”。
紐約:當“白領”不會讓你感覺有所不同
“被稱為‘白領意味著你有一份體面的工作,但這并不會讓你感覺自己和其他人有所不同,因為美國有太多太多這樣的人了。”在紐約出生長大并在此地就讀大學的霍伊如此告訴記者。
他是典型的紐約客,家住皇后區,每天早晨大約要乘40分鐘地鐵趕到曼哈頓島去上班。大多數紐約“白領”的一天都是這樣開始的。因為曼哈頓寸土寸金,房價頗高,他們只能住在相對便宜的地區,好在地鐵可以到達城市的各個角落。
霍伊工作的公司是一家金融市場信息服務機構,他已在這家公司工作了5年。在紐約,“白領”的年收入應該在7萬美元(約合44萬元人民幣)以上,但紐約的稅率比美國其他地區要高,倘若年薪10萬美元(約合63萬元人民幣),稅率大概會達到35%左右。
霍伊每月消費大約為2200美元(約合1.39萬元人民幣),其中最主要的開銷就是房租。剛開始工作的幾年里,霍伊并沒有刻意儲蓄,但他現在已經開始準備攢錢買一間屬于自己的小公寓。這個愿望最快兩三年就可以實現,但他需要向銀行貸款。
除去房租,和朋友聚餐是霍伊每月最大的開銷,接下來是參加一些娛樂活動的費用以及其他生活支出。
目前,健身已經成為紐約“白領”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霍伊幾乎每天下班后都會去健身房,“健身讓我放松,并且保持身體健康。”健身后,霍伊會回到家給自己做一頓健康的晚餐,然后看電視劇或他最喜歡的橄欖球比賽。
“生活在紐約最大的優點就是你隨時可以找到各種各樣的社會活動,我經常在網上找關于社交舞的信息,參加社交舞既能讓我享受舞蹈又可以認識很多新的朋友。”霍伊現在還在參加網球和攀巖培訓,有時間還會約朋友一起打籃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