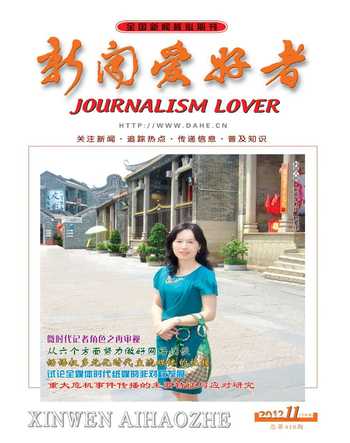新聞?wù)Z言的最高要求是準(zhǔn)確
孔祥科
聶部長讓我講講新聞?wù)Z言問題。這是一個(gè)大題目,不好講。而且我平時(shí)學(xué)習(xí)不夠,研究不多,恐怕講不好。
但是聶部長提出的這個(gè)課題可是個(gè)好題目,是一個(gè)做好新聞工作必須要解決的基本問題和基礎(chǔ)性的問題。新聞業(yè)務(wù)水平的提高,應(yīng)該和必須從這些基礎(chǔ)性的問題抓起。
這些年來,我國漢語教育水平的下滑是有目共睹的事情。前幾年,臺灣的國民黨、親民黨的領(lǐng)袖連戰(zhàn)、宋楚瑜來大陸訪問,北大、清華的校長都讀了錯(cuò)別字,鬧了笑話。我有一次聽清華一位知名教授講課,他連續(xù)兩次把“掣(chè)肘”說成“zhì肘”,一時(shí)讓我感到莫名其妙,回過味來才明白他原來講的是“掣(chè)肘”。
今年(2008年)3月12日,新華社發(fā)了一篇通稿,是記者訪問上海著名語言文字期刊《咬文嚼字》主編郝銘鑒的,他提出了一個(gè)口號,說:“要像保衛(wèi)黃河一樣保衛(wèi)我們的漢語。”
這是說別人。我也經(jīng)常讀錯(cuò)別字。我從小長在農(nóng)村,不會講普通話,漢語拼音的ei與en不分。今天,有說錯(cuò)的,敬請大家不吝賜教。
一、什么叫“新聞?wù)Z言”?或者說“新聞?wù)Z言”有哪些特點(diǎn)?
新華社編輯出版的《中國新聞實(shí)用大辭典》沒有“新聞?wù)Z言”這個(gè)條目,只介紹了“新聞?dòng)谜Z的特點(diǎn)”,列舉了以下一些屬性。即真實(shí)性、時(shí)效性、客觀性、新鮮性、傾向性、可讀性、知識性、趣味性等。
這個(gè)歸納比較全面,是就整個(gè)新聞?wù)Z言的特點(diǎn)來說的。但是這八種屬性不可能同時(shí)體現(xiàn)在每一句具體的新聞報(bào)道中。
上海復(fù)旦大學(xué)的徐培汀教授說:“新聞要用事實(shí)說話,憑借對事實(shí)的客觀敘述來吸引人,新聞的這一特點(diǎn)決定了新聞?wù)Z言的個(gè)性——可信性、可讀性、易讀性,既要確切又要具體,既要通俗又要簡練,既要新穎又要生動(dòng)。”
這個(gè)歸納強(qiáng)調(diào)的是新聞?wù)Z言的“個(gè)性”。對于新聞?wù)Z言的“寫作要求”,他提出:忌夸張,求確切;忌空泛,求具體;忌深?yuàn)W,求通俗;忌繁復(fù),求簡練;忌老套,求新穎;忌枯燥,求生動(dòng)。
中國人民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的研究員劉保全先生也寫過論新聞?wù)Z言的文章。他說:“第一,新聞?wù)Z言必須準(zhǔn)確;第二,新聞?wù)Z言要樸實(shí);第三,新聞?wù)Z言要精練;第四,新聞?wù)Z言要生動(dòng)。”
這都是學(xué)者專家對新聞?wù)Z言特點(diǎn)的很好的總結(jié),值得我們認(rèn)真地去體會。
我個(gè)人認(rèn)為,新聞?wù)Z言還應(yīng)當(dāng)這樣來分類:
(一)新聞媒體的“版面語言”,包括紙質(zhì)媒體的版面編排問題和電子媒體的節(jié)目編排問題。當(dāng)然,電子媒體也可以叫“時(shí)段語言”。
(二)我們現(xiàn)在所講的是這種形成文字或廣播電視用聲
音傳播的語言。當(dāng)然,一般說,廣播電視的新聞也要先形成文字。現(xiàn)場直播、現(xiàn)場報(bào)道至少也要打個(gè)腹稿。總之是要用語言來表達(dá)。
我們今天不研究“版面語言”或“時(shí)段語言”的問題,主要討論新聞稿件的語言問題。從上述我們介紹的幾個(gè)關(guān)于“新聞?wù)Z言”的論述來看,都把準(zhǔn)確性放在第一位。因此,我們今天就把準(zhǔn)確性的問題作為討論的重點(diǎn)。
二、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xiàn)實(shí)”
關(guān)于準(zhǔn)確性的意義,這里不用多說。“真實(shí)性是新聞的生命”這句話是我們新聞工作者的口頭禪。對新聞事實(shí)的表述不準(zhǔn)確,就背離了新聞事實(shí),受眾就不認(rèn)可你的報(bào)道。這幾年,在河南新聞獎(jiǎng)評獎(jiǎng)的過程中,因?yàn)橛迷~不準(zhǔn)確而遭淘汰的作品屢見不鮮。①
如果不“因人廢言”的話,我覺得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xué)問題》一書,還是很值得一讀的。他說:“語言是同思維直接聯(lián)系的,它把人的思維活動(dòng)的結(jié)果、認(rèn)識活動(dòng)的成果用詞和句中詞的組合記載下來,鞏固起來,這樣就使人類社會中的思想交流成為可能了。”這本書還在對話中引用馬克思恩格斯的定義,強(qiáng)調(diào)說:“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xiàn)實(shí)。”
我們的一些文章、作品、新聞報(bào)道,之所以不能準(zhǔn)確地表達(dá),首先是由于沒有對我們的報(bào)道對象、反映的目標(biāo),做到深刻地、準(zhǔn)確地認(rèn)識和把握。對于問題、人物、事物的認(rèn)識淺嘗輒止,你就不可能做到使用生動(dòng)形象的語言,準(zhǔn)確地說明它、反映它。所以語言反映準(zhǔn)確不準(zhǔn)確,根本上說是思想認(rèn)識深刻不深刻的問題。自己“以其昏昏”,不可能“使人昭昭”。我參加某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的研究生論文答辯,發(fā)現(xiàn)個(gè)別等待答辯的碩士論文的題目就有問題。比如一篇論文的題目是《試析穆青新聞創(chuàng)作與文學(xué)的“聯(lián)姻優(yōu)勢”及其現(xiàn)代意義》。作者在題目中、論述中多次使用“穆青的新聞創(chuàng)作”這樣的詞匯,僅從這一點(diǎn),我們就可以斷定,作者及其導(dǎo)師連新聞是根本不允許“創(chuàng)作”的這個(gè)原則都不知道。再論什么新聞、什么文學(xué)、什么“聯(lián)姻”,都是白搭。
我們有些新聞報(bào)道之所以在語言上出毛病,也和記者的新聞理念有很大關(guān)系。特別是在正面報(bào)道中,他們把報(bào)道事實(shí)的新聞和宣傳某種觀念混淆起來。以為正面報(bào)道、成就報(bào)道、對重要事件的表態(tài)性報(bào)道和反映性報(bào)道,可以沒有根據(jù)、不要具體的來源,可以信口渲染、夸大其詞。這是不對的。什么“群眾反映”“同志們紛紛表示”“大家說”“一致認(rèn)為”等,一看就是“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心中之塊壘”。劉保全先生在講新聞?wù)Z言時(shí)舉過20世紀(jì)50年代葉圣陶改新聞稿件的一個(gè)例子:新聞稿《首都八十余萬人大示威》原有“綠色的林蔭馬路”和“紅色的天安門廣場”這樣的字句,圣陶老人說,林蔭馬路開辟不久,樹還沒有長大,五一節(jié)那天,樹木剛剛有點(diǎn)兒嫩綠,并沒有郁郁蔥蔥綠成一片,怎么能說“綠色的林蔭馬路”?至于天安門廣場,也不都是紅色的,只有一些建筑才是紅色的。葉老這樣說才真正是“有實(shí)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
有了比較深刻的認(rèn)識、感受,就要千方百計(jì)地尋找比較準(zhǔn)確的語言來形容它、反映它。這個(gè)過程,實(shí)際上也是進(jìn)一步加深認(rèn)識的過程。你要認(rèn)識、你要反映,就得使用一種工具。這種工具就是語言。
如果你說:“我明白,但我說不上來。我是啞巴吃餃子,肚里有,就是倒不出來。”
我說:“你這只是一種感覺,還停留在感性的階段,還沒有上升到理性的階段。你認(rèn)識明白了,想清楚了,你就能用準(zhǔn)確的語言明白地表達(dá)出來了。”
我們說的遣詞造句,就是要用比較得當(dāng)?shù)恼Z言,準(zhǔn)確地表達(dá)自己的思想和認(rèn)識,就是要準(zhǔn)確地反映新聞?wù)鎸?shí);用語用詞不準(zhǔn)確,就不能真實(shí)地、準(zhǔn)確地、恰到好處地傳遞你想要傳遞的信息。中世紀(jì)的意大利詩人、《神曲》的作者但丁(1265—1321)說過:“語言作為工具,對于我們之重要,正如駿馬對于騎士的重要。最好的駿馬適合于最好的騎士,最好的語言適合于最好的思想。”因此,我認(rèn)為,“準(zhǔn)確性”是新聞?wù)Z言的最高要求。沒有這個(gè)“準(zhǔn)確性”,其他都談不上。雖然我們習(xí)慣于把“準(zhǔn)確性”作為對新聞最基本的要求,但想要真正做到準(zhǔn)確并非那么簡單。而只有真正做到準(zhǔn)確,其他的幾個(gè)要求才可以“錦上添花”。
美國一個(gè)叫梅茲的新聞學(xué)教授說過:“對于你——一個(gè)記者來說,爭取報(bào)道的準(zhǔn)確無誤,必須成為你的精神狀態(tài),成為你的習(xí)慣……”解放軍報(bào)社的高級編輯黎昂在引用這句話以后,深情地呼吁:“讓我們記住一本新聞教科書的這句話——‘新聞工作者能夠犯的最大罪行是不準(zhǔn)確。”
法國有一個(gè)非常著名的小說家叫莫泊桑。他是19世紀(jì)后半葉歐洲最優(yōu)秀的批判現(xiàn)實(shí)主義的作家之一。他的短篇小說《羊脂球》《我的叔叔于勒》等,我們中的許多人都讀過。他在開始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時(shí)候,得到文學(xué)大師福樓拜(福樓拜是他母親和舅舅的好友)慈父般的指導(dǎo)。福樓拜教導(dǎo)他用精確而不是近似的語言描寫所觀察到的事物:“你所要說的事物,都只有一個(gè)詞兒來表達(dá),只有一個(gè)動(dòng)詞來表示它的行動(dòng),只有一個(gè)形容詞來形容它。因此就應(yīng)該去尋找,直到發(fā)現(xiàn)這個(gè)詞、這個(gè)動(dòng)詞和形容詞,而決不應(yīng)滿足于‘差不多,決不應(yīng)利用蒙混、哪怕是高明的蒙混手法,不要利用語言的戲法來逃避困難。”這就是我們通常說的,要敘述或描寫一件事情或一個(gè)事物,最準(zhǔn)確的詞匯只有一個(gè);作者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gè)詞兒找出來。
三、語言要用得準(zhǔn)確,必須有一個(gè)端正、認(rèn)真的態(tài)度
我們必須一絲不茍地對待我們筆下的每一個(gè)詞、每一個(gè)字和每一個(gè)標(biāo)點(diǎn)符號。這方面,古今中外,許多先賢、名作家,留有許多意味雋永、發(fā)人深思的故事。“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和“春風(fēng)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shí)照我還”的故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它們都是用字“推敲”方面的經(jīng)典,是我們民族寶貴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
在講究語言的準(zhǔn)確性方面,鄧小平同志可以做我們的榜樣。上世紀(jì)80年代,空軍出了個(gè)“學(xué)習(xí)雷鋒的標(biāo)兵”人物,叫朱伯儒。他不是一般的戰(zhàn)士或基層干部,而是飛行員出身的團(tuán)職干部。朱伯儒同志的事跡宣傳以后,有關(guān)方面請鄧小平同志題詞。小平同志寫了“向朱伯儒同志學(xué)習(xí),做一個(gè)名符其實(shí)的共產(chǎn)黨員”。同時(shí)交代說:“請不要急于拿去發(fā)表,應(yīng)該請語言學(xué)家推敲一下,看看有沒有用字不準(zhǔn)確的地方。”辦公廳的同志去請教語言學(xué)家王力先生。王力先生看后說:“好,寫得好!不過,‘名符其實(shí)的‘符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使用了。如果就這樣寫,用字不規(guī)范。最好用‘副字。”說著,王力先生還用鉛筆在“符”字旁邊寫了一個(gè)“副”字。工作人員匯報(bào)給小平以后,小平同志連聲稱贊王力先生改得好。他說:“雖然過去用這個(gè)‘符字,但現(xiàn)在不用了,就是錯(cuò)別字了。老師寫了錯(cuò)別字,貽誤了學(xué)生,國家領(lǐng)導(dǎo)人寫了錯(cuò)別字會影響國民的文風(fēng)。這叫上行下效嘛!你去替我好好謝謝王老!”對照小平同志的胸懷舉止,那些老愛題詞又老是寫錯(cuò)字的朋友,應(yīng)當(dāng)感到羞愧。比如,毛主席開辟的革命根據(jù)地井岡山,我們都知道是這個(gè)“岡”,約定俗成的也是這個(gè)“岡”。可是當(dāng)我們?nèi)ゾ畬浇邮芨锩鼈鹘y(tǒng)教育的時(shí)候,發(fā)現(xiàn)有個(gè)大學(xué)的牌子寫成“井崗山”了還照掛不誤。
由于作風(fēng)的浮躁,一字之差,鬧出笑話、造成損失的例子實(shí)在是太多了。改革開放之初,人民日報(bào)批評過這樣一件事情:新疆一個(gè)部門要出口一批產(chǎn)品,但在包裝說明上,把“烏魯木齊”印成了“鳥魯木齊”。多了這一點(diǎn)不要緊,光收回重印,就損失了十幾萬元。
還有一個(gè)故事:20世紀(jì)30年代,蔣、馮、閻中原大戰(zhàn)時(shí),馮玉祥將軍的一個(gè)參謀沒有分清楚河南“沁陽”和“泌陽”,調(diào)錯(cuò)了部隊(duì),貽誤了戰(zhàn)機(jī)。這個(gè)真假我們不必查考了。《參考消息》報(bào)上的《翻譯一字之差〓延長俄格戰(zhàn)爭》的報(bào)道卻是有根有據(jù)的:
上月停火協(xié)議的核心內(nèi)容是在俄羅斯與格魯吉亞分裂地區(qū)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這兩個(gè)地區(qū)目前實(shí)際處于克里姆林宮控制下)之間建立“緩沖區(qū)”。協(xié)議的斡旋人是法國總統(tǒng)薩科齊,因?yàn)榉▏F(xiàn)在是歐盟輪值主席國。不過,歐盟先前的外交策略遭到了令人尷尬的失敗。
……
現(xiàn)在,沖突延續(xù)的原因之一似乎在于協(xié)議中的一段俄文翻譯,那段文字的內(nèi)容是“為”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恢復(fù)安全。英文版的說法是“在”那兩個(gè)地區(qū)恢復(fù)安全。
這一差別非常關(guān)鍵,因?yàn)槎砹_斯仍然“在”格魯吉亞領(lǐng)土上駐留了坦克和武裝部隊(duì)。國際社會則希望“為”南奧塞梯和阿布哈茲恢復(fù)安全局勢的同時(shí),俄羅斯軍隊(duì)并不駐留在格魯吉亞。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認(rèn)為,停火協(xié)議的措辭使俄羅斯聽起來就像是侵略者。他表示,格魯吉亞的理解“完全曲解了原意”,包括把介詞“為”換成了“在”。
法國人一直認(rèn)為法語是為世界各國人民使用并理解的一門通用語言。這次的鬧劇給了他們一個(gè)沉重打擊。
這是由于翻譯的一字之差,造成雙方不同的理解,拖延了停火時(shí)間的例子。對雙方來說,還沒有造成什么惡果。
另外,關(guān)于美軍之所以在日本廣島投下原子彈的原因,也有“錯(cuò)譯”的說法。人民日報(bào)辦的《學(xué)員報(bào)》曾刊登過這樣一條資料: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期,日本的敗局已定。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發(fā)表,日本當(dāng)局看到公告中盟方提出的投降條件比他們原先想象的要寬大得多,喜出望外,決定把公告分發(fā)各報(bào)刊登。7月28日,首相鈴木接見新聞界人士時(shí)說,日方對《波茨坦公告》采取“默殺”政策。他的原意是日本內(nèi)閣決定對公告暫時(shí)不加公開評論。同盟通訊社將“默殺”一詞錯(cuò)譯成“不予理睬”。消息播出后,美方認(rèn)為日本拒絕公告的要求,決定予以懲罰。8月6日美軍在廣島投下了威力巨大的原子彈。這個(gè)差錯(cuò)造成的后果是導(dǎo)致數(shù)萬生靈涂炭。
差錯(cuò)發(fā)生后,日本內(nèi)閣對鈴木的用詞和同盟通訊社的錯(cuò)譯十分惱火,但這時(shí)消息已傳遍世界各國。
這個(gè)說法有幾分真實(shí),我們不敢妄斷,但是錯(cuò)譯給日本幫了倒忙應(yīng)該可以肯定。所以,文字問題,白紙黑字,代表的是一方的觀點(diǎn)、認(rèn)識,甚至是承諾和法律責(zé)任,可不敢掉以輕心。毛主席說,粗枝大葉,往往搞錯(cuò);我們千萬要小心、仔細(xì)。
四、對不甚明了的詞匯一定要查字典、查詞典,切忌“想當(dāng)然”
這方面我有深刻的教訓(xùn)。一件事是在上世紀(jì)70年代,我們幾個(gè)年輕人在報(bào)社做校對工作,見到一篇強(qiáng)調(diào)思想政治工作的文章,說抓好了思想政治工作,再做其他工作就會“事半而功倍”。這里的“事”指工作,“功”指功效、效果。“事半功倍”這個(gè)成語,用在這里是不錯(cuò)的。但我們不懂,把它理解反了。以為“功”是指用去的功夫、精力,而“事兒”是指做成的事情。那時(shí)剛到報(bào)社工作,沒有經(jīng)驗(yàn),加上本身文化基礎(chǔ)差(那時(shí)“文化大革命”尚未結(jié)束,手邊能找到的工具書也很少),幾個(gè)人一嘀咕,就把它改成了“事倍功半”。這樣,意思就完全說反了,把政治思想工作的正面作用,貶成負(fù)面的作用了。見報(bào)以后,編輯部不得不作了更正。②
如果說這件事的出錯(cuò)不全在我的話,那另一件事出錯(cuò)就完全在我了。那是我當(dāng)編輯以后,約請中國人民大學(xué)的薄浣培先生撰寫一篇關(guān)于新聞導(dǎo)語方面的文章。薄先生的文章強(qiáng)調(diào)新聞導(dǎo)語要抓住最新的新聞事實(shí),不要等到時(shí)過境遷,事物、事情成了“明日黃花”了再去抓它,黃花菜都涼了。那時(shí),我對“明日黃花”這個(gè)詞也不懂,心想:應(yīng)該是“昨日黃花”吧!昨天的“黃花”,今天看來可以認(rèn)為過期了;而“明日黃花”,不是還沒有來到嗎,怎么能算過期呢?這就是“想當(dāng)然”,就是自以為是。殊不知,“明日黃花”是一個(gè)成語,“黃花”指菊花,“明日黃花”特指重陽節(jié)后的菊花。古人多于重陽節(jié)登高賞菊;重陽節(jié)過后,賞菊漸少,菊花對他們來說意義就不大了。宋代大詩人蘇東坡在《九日次韻王鞏》詩中說:“相逢不用忙歸去,明日黃花蝶也愁。”意思是說,既已相聚在一起就不要著急回去,還是趁這菊花盛開的重陽節(jié)日賞花為好。因?yàn)椋鹊鹊健懊魅铡保仃栆堰^,不但人觀之無趣,恐怕飛舞的彩蝶看了那過時(shí)的菊花也會犯愁的。這就是“明日黃花”一詞的出處和本意。而我不解其意,又輕率為之,至今猶覺臉紅。這兩件事對我的教訓(xùn)、觸動(dòng)實(shí)在是太大了,使我一生都不能不對筆下的文字心懷戒懼。
五、要準(zhǔn)確地表述新聞事實(shí),還要正確地使用標(biāo)點(diǎn)符號
標(biāo)點(diǎn)符號的作用,就是為了限制歧義的產(chǎn)生,讓句子的意思更明確。標(biāo)點(diǎn)符號使用得不正確,可能會給閱讀帶來極大的不便。標(biāo)點(diǎn)符號用得好,會增強(qiáng)文字的表現(xiàn)力,傳達(dá)的信息會更準(zhǔn)確更感人。可是,現(xiàn)在標(biāo)點(diǎn)符號的濫用、錯(cuò)用現(xiàn)象比較普遍。自己不會正確地使用標(biāo)點(diǎn)符號,對于正確地使用標(biāo)點(diǎn)符號的文字也不能給予正確的理解。
比如,2008年中國政府的國防白皮書發(fā)表以后,中國許多媒體都做了“解讀”。而在所謂的“解讀”中,又把所謂“承諾停止研發(fā)新型核武器”作為該白皮書的一項(xiàng)重要內(nèi)容。于是,國外媒體也紛紛跟風(fēng)炒作,大肆宣傳“中國已經(jīng)承諾停止研發(fā)新型核武器”,大有逼中國政府就范之意。其實(shí),中國政府發(fā)表的白皮書中根本沒有這個(gè)意思。中國政府的國防白皮書關(guān)于“核武”的那句話是這樣寫的:
“中國主張所有核武器國家明確承諾全面、徹底銷毀核武器,并承諾停止研發(fā)新型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在這句話中,“中國”是主語,“主張”一詞是謂語,“所有核武器國家明確承諾全面、徹底銷毀核武器,并承諾停止研發(fā)新型核武器”等是我們“主張”的具體內(nèi)容。它的意思表述得非常明確,怎么成中國單方面承諾“停止研發(fā)新型核武器”了呢?2009年1月30日《參考消息》有一篇《國防白皮書誤讀“罪在句逗”》的文章,分析了問題所在。它說:
白紙黑字是怎樣引起“斷章取義的誤讀”呢?原來,問題就出在句逗上。原文的本意是“中國主張所有核武器國家承諾停止研發(fā)新型核武器”,并非中國本身做出承諾。但這句話(特別是中間的逗號)令人產(chǎn)生了歧義,似應(yīng)改為:“中國主張:所有核武器國家明確承諾全面、徹底銷毀核武器,并停止研發(fā)新型核武器,降低核武器在國家安全政策中的作用。”
這個(gè)修正意見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們國內(nèi)媒體的編輯人員漢語水平不夠、不能正確地理解和使用標(biāo)點(diǎn)符號,恐怕是更主要的原因。今年(2008年)5月,陳力丹教授來鄭州大學(xué)講課,專門講到標(biāo)題中間亂用冒號的問題。這個(gè)問題,我也感同身受。現(xiàn)在,無論是新聞報(bào)道的標(biāo)題還是新聞?wù)撐牡臉?biāo)題,中間夾個(gè)冒號的用法,像瘟疫一樣在流行傳播。可這種用法,往往把人弄得莫名其妙。2001年4月,美國偵察機(jī)在南海上空撞毀我飛機(jī),飛行員王偉犧牲,引起全國人民的激憤。有一家報(bào)紙?jiān)趫?bào)道江澤民、李肇星等領(lǐng)導(dǎo)人對此的表態(tài)時(shí),將冒號這樣標(biāo):
江澤民:必須向中國人民道歉
李肇星:這件事情沒有完
多虧報(bào)紙文字是供閱讀的文字;如果是廣播,那就可能造成更多錯(cuò)誤的理解。在參加今年(2008年)河南省新聞獎(jiǎng)的評比中,我看到這樣一個(gè)標(biāo)題:
焦裕祿女兒:父親能歌善舞〓多才多藝
在參加研究生的論文答辯中,我看到了這樣的論文標(biāo)題:
體制內(nèi)外:1990年代中國××××創(chuàng)作研究
我不明白,作者為什么要在這里使用冒號。有時(shí)候?yàn)榱烁魑侣剺?biāo)題要做兩行或三行。中間加冒號,好像是把兩行合并成一行了。這樣的合并如果引起了歧義,就不應(yīng)該使用了。我認(rèn)為“江澤民”“李肇星”和“焦裕祿女兒”后,都應(yīng)該加一個(gè)“說”字,而“體制內(nèi)外”和“××××研究”中間夾個(gè)冒號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明白了。因?yàn)榘凑諊艺Z委的說明,“冒號表示提示性話語之后的停頓,用來提示下文”;也可以“在總括性話語之前”用冒號。而冒號的濫用,卻給我們的閱讀帶來了麻煩。
我想起英國作家王爾德的一個(gè)故事:有一次,他在家中舉辦宴會,賓客們濟(jì)濟(jì)一堂,在客廳里等了好久,也不見他的到來。預(yù)定開始的時(shí)間馬上要過了,王爾德才急匆匆地趕來,并且連忙向客人表示歉意。客人問他干啥去了,他說在修改詩稿。客人說:“這么長時(shí)間一定做了不少工作吧”王爾德認(rèn)真地回答說:“我做了一件極其重要的工作,我刪去了一個(gè)逗點(diǎn)兒,但后來經(jīng)過反復(fù)思考,我又把它恢復(fù)了。”
愿我們在使用標(biāo)點(diǎn)符號時(shí),能像王爾德那樣仔細(xì)斟酌。
六、我們在追求用詞準(zhǔn)確的同時(shí),對于“準(zhǔn)確性”的理解也不能過于偏執(zhí)或拘泥
前面,幾位專家關(guān)于新聞?wù)Z言的說法,除了“準(zhǔn)確性”的概念外,還提到“新鮮”“生動(dòng)”的要求。在準(zhǔn)確的基礎(chǔ)上求生動(dòng),或用生動(dòng)的語言使對新聞事實(shí)的表述更準(zhǔn)確,也是新聞寫作一個(gè)正當(dāng)?shù)囊蟆j愅老壬v修辭學(xué)有“三種境界”“兩大分野”。“三種境界”分為:記敘的境界,以記敘事物的條理為目的(如法律條文、科學(xué)記載);表現(xiàn)的境界,以表現(xiàn)生活的體驗(yàn)為目的(如詩歌);糅合的境界,是以上兩界糅合所成的語詞(如雜文、口頭閑談)。“兩大分野”一為積極的修辭,一為消極的修辭。陳先生說,記敘的境界需要消極的修辭,對語詞進(jìn)行種種限制,以防產(chǎn)生任何歧義。積極的修辭適合表現(xiàn)的境界,要帶有個(gè)人的體驗(yàn)性、具體性,要讓讀者、聽眾“感受”。因此,可以使用比喻、夸張、借代等修辭形式。對于新聞的寫作,我以為,既不全是記敘的境界,也不全是表現(xiàn)的境界。它在多數(shù)情況下,是糅合的境界。現(xiàn)在,有一種新聞報(bào)道形式,叫做“精確新聞報(bào)道”,不但要用事實(shí)說話,還要精確到用數(shù)據(jù)說明事實(shí)。對于數(shù)據(jù)、數(shù)字的表述,你當(dāng)然必須用消極的修辭,不能含糊。比如GDP、各種數(shù)據(jù)等,一旦出現(xiàn)錯(cuò)誤,整個(gè)新聞事實(shí)就改變了。而對其他一些新聞事實(shí)的表述,有時(shí)是需要用積極的修辭方式去表現(xiàn)的。甚至有時(shí)候,使用“模糊語言”來表現(xiàn)具體的新聞事實(shí)卻更加具有表現(xiàn)力,更能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比如,獲得中國新聞獎(jiǎng)二等獎(jiǎng)的消息《請過路吧〓親愛的藏羚羊》,不少地方用的就是擬人手法,屬于積極的修辭。如:
昨晚,約有500只藏羚羊帶著剛滿月的兒女們,通過可可西里青藏鐵路建設(shè)工地,向黃河源頭的扎陵湖、鄂陵湖遷徙。
……
潛伏下來的觀察哨稱:跨越鐵路線,母藏羚羊若無其事,像跨過自己家的門檻一樣;小羊羔緊依著母羊,流露出一種莫名其妙的驚喜。
每年6至8月,藏羚羊集結(jié)成群,長途跋涉,前往可可西里腹地的卓乃湖、太陽湖一帶產(chǎn)崽,去完成一年一度的延續(xù)種群的歷史使命。小羔羊滿月后,再由母羊呵護(hù)著返回原棲息地。
今年6月20日前后,兩萬多只雌性藏羚羊北上產(chǎn)崽,鐵路夜間停止施工10天,為它們開辟通道。一個(gè)多月里,兩萬只小羔羊誕生在那塊神秘的“天然產(chǎn)床”上。估計(jì),從8月4日到8月15日,將有4萬只大小藏羚羊跨過鐵路安然回遷。
讀讀這樣的新聞報(bào)道,積極的修辭是不是更多一些呢?現(xiàn)在許多新聞報(bào)道為了給人以更深刻的感受,都很注意使用有“張力”的語言,傳達(dá)出更具體的形象。這里忌諱的只是對于事實(shí)的夸張和渲染。如果不了解這兩種修辭方式的不同及其適用的范圍,有時(shí)候會出“關(guān)公戰(zhàn)秦瓊”那樣的笑話。有一則笑話這樣說:蘇州寒山寺的墻壁上有一句詩“一片清光照姑蘇”。有一位領(lǐng)導(dǎo)看了后直搖頭。他說,“清光”者,月光也。“姑蘇”者,蘇州也。月光,怎么能只照蘇州一地呢?于是揮筆改為“一片清光照姑蘇及其他各地”。他以為,這一改就全面了。可是,這樣改還稱其為詩嗎?1984年,我寫過《做事與做官》的雜文,舉了一個(gè)老干部離休后潛心練字,書法日進(jìn),后來“墨寶”被送到日本展出的例子。當(dāng)值的編輯搬著字典堅(jiān)持要把“墨寶”二字改為“墨跡”。這樣一來,稱頌、客套的意味沒有了,反而生出一些貶意來。(這個(gè)事情的結(jié)果是,在我的堅(jiān)持下,“墨跡”又恢復(fù)為“墨寶”。)
今天我們講新聞?wù)Z言,主要強(qiáng)調(diào)“準(zhǔn)確性”的問題。生動(dòng)、通俗、簡明、新穎等來不及細(xì)說。其實(shí),要做到語言表達(dá)的準(zhǔn)確,首先是對基本新聞事實(shí)的把握要準(zhǔn)確。這是一個(gè)前提條件。而影響人們對基本事實(shí)準(zhǔn)確把握的因素,除了認(rèn)識上的原因,除了調(diào)查研究不夠、深入了解不夠之外,還有立場的原因、政治傾向的原因。有句話說:“偏見比無知距離真理更遙遠(yuǎn)。”這個(gè)問題是保持新聞?dòng)谜Z準(zhǔn)確性的前提,但已不在我們今天討論的范圍之內(nèi)了。
附 記:
①在修改這篇講稿時(shí),梁衡送來范敬宜同志的文章《以后這樣的人不多了》,說范敬宜“寫稿、編報(bào)至細(xì)。一次,我當(dāng)夜班,他出國,遠(yuǎn)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兩次來電話只為稿中的一個(gè)字。真如古詩所說‘吟安一個(gè)字,捻斷數(shù)莖須。——他給我講過一個(gè)例子,說年輕記者對舊典不熟,易出笑話。有一篇言論批評我們的干部和市場走得太近,說是‘倚市門,殊不知‘倚市門是指妓女拉客。他骨子里還是一個(gè)文化人,繼承了中國報(bào)人的正宗一脈,警醒于政治,厚積于文化,薄發(fā)于新聞,滿腹才學(xué),發(fā)為文章,并帶出一批高徒”。(見2010年第12期《新聞戰(zhàn)線》)
注 釋:
①在2009年度河南省新聞獎(jiǎng)評比中,有一篇題為《丹江北去》的新聞通訊,復(fù)評被評為三等獎(jiǎng)。定評中,認(rèn)為它反映淅川人民為南水北調(diào)做出的貢獻(xiàn),比較深刻,文字比較優(yōu)美,建議提升為一等獎(jiǎng)。但在大會討論時(shí),有評委發(fā)現(xiàn)它的數(shù)字中的小數(shù)點(diǎn)錯(cuò)了。差之毫厘,謬以千里。這是個(gè)教訓(xùn)。
②那篇文章是空軍報(bào)社副總編輯章鎮(zhèn)同志撰寫的。在那種政治氣氛很是緊張的情況下,事后,他沒有責(zé)怪我們,而是發(fā)了一個(gè)更正了事。這里,我向他表示敬意和懷念。
(本文根據(jù)作者2008年在平頂山市礦工報(bào)的一次講稿補(bǔ)充修改而成。文中所提到的“聶部長”,指平煤集團(tuán)宣傳部長聶世勇同志。)
編校:董方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