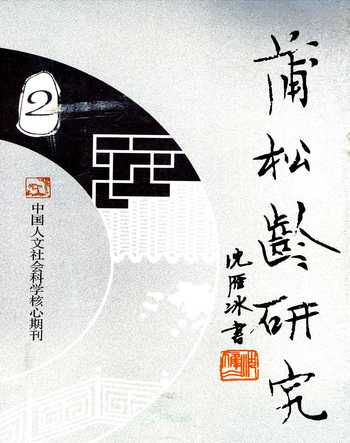鮮血為他作證
黃道炫
當蔡協民剛剛來到閩西工作時,他也許沒有料到,前面的路遍布荊棘。
其實,看一看和他同時被派到閩西工作那批人的命運,就知道他的遭遇并非偶然。譚震林、江華、曾志……這些人日后大都被扣上了右傾的帽子遭到打擊。只不過他們挺過了難關,迎來了最后的勝利,而蔡協民,卻在個人和蘇區命運最艱難的時刻,倒在了槍彈之下。他的名字,也就慢慢被時間的長河湮沒了。
【招致疑忌】
1931年4月,福建黨內老資格領導人羅明給中共中央組織部報送福建干部履歷,關于蔡協民的情況是:“中等學生。1926年在湖南入黨。在湖南做過農運,后隨四軍來福建。”蔡協民來閩之前,曾任紅四軍第8縱隊黨代表,可以說是毛澤東的得力助手之一。
1929年6月,毛澤東在紅四軍“七大”上落選前委書記,7月到閩西特委駐地上杭蛟洋,陪同他的就是譚震林、江華、賀子珍和蔡協民、曾志夫婦。蔡協民隨之擔任中共閩西特委常委、組織科長,鄧子恢為特委書記,蔡在特委中的作用僅次于鄧。這段時期的生活,后來曾志回憶:“我們駐地不遠處有一條小溪,溪上有座小橋。晚飯后,我們經常陪同毛委員夫婦去那里散步,欣賞暮色中的田園風光和落日的霞輝……有時我們也學著別人的樣子去撈魚,毛委員總是興致勃勃地在一旁看著。毛委員很愛吃魚,而且特別愛吃魚頭,因此,我們大家也很高興去干這樁事。總覺得自己撈回來的魚會特別好吃。”(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
1930年5月,蔡協民任中共福建省委秘書長,后任軍委書記。羅明對他的評價是:“對農運有經驗……懂軍事,能寫。”
蔡協民真正獨當一面,表現出忠誠特質是1931年3月。當時,福建省委被破獲,幾個骨干被捕,處于癱瘓狀態。蔡協民、曾志夫婦臨危受命,組成臨時省委,蔡協民為書記,實際是由蔡、曾夫婦負起福建省委的重任。倉猝建立的臨時省委毫無基礎,原省委機關“幾乎連馬桶都被解往司令部了”,臨時省委經費無著,既要“保護未破壞機關的安穩,又要設法保護外來同志的安全”,還要指導全省工作,事物繁冗,“每天兩腳忙起灰來都解決不了”。(《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信,1931年4月5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7冊)
不僅如此,省委所在的廈門地方不大,曾志又經常代表組織出面活動,很容易被人認出。一次不巧碰上原省委駐地房東家兒媳,向她討要省委機關被破獲后損失的房錢。曾志回憶,被纏住幾小時后,幸遇一大戶人家出殯,熱熱鬧鬧,“趁著那房東兒媳正探頭探腦看得出神之際,我一轉身,撒腿往街邊的一個小胡同跑去”,算是逃過一劫。蔡協民后來報告:曾志“被他們扣留了五點鐘,幸設計逃脫,未遭大害”。短短幾句話,后面卻埋藏著生死一線的動魄驚心。
雖然生命安全時時受到威脅,雖然“現在蔡、曾還未找到住的地方”,而不得不到處奔波;但是,蔡協民在給中央的報告中仍堅決表示:“假若我們離開廈門,一點下層基礎,必然更難保存。所以我與曾在中央未批準省委搬位置和廈市組織沒有相當健全以前,決不離開廈門。”正是在這封報告中,蔡協民寫下了后來給他惹下無窮禍患的一段文字。當時,閩西蘇區正開展大規模肅反,一大批蘇區干部被當作社會民主黨遭到清肅并被消滅肉體。1931年7月閩粵贛省委報告:“六月份總共槍決了842個社黨……半年來所扣留的社黨不下四千人(整個閩西),槍決的也不下二千人了。”蔡協民對此憂心忡忡,本著對組織負責的態度,他認真地提出建議,要求肅反時“主要還要在群眾中肅清反革命派的影響,宣布反動政綱的破產。對反動分子務須慎重處置,不可使被反革命造謠中傷的同志無辜就戮”。(《蔡協民關于福建工作情況報告,1931年4月13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7冊)
蔡協民這番話在肅反的狂熱氣氛中馬上被視為立場動搖的證據。報告送出不久,中共香港交通站已有報告說蔡協民負責領導的中共福州市委盡是社會民主黨分子。1931年6月,中共中央決定在福州成立福建省委辦公會,蔡協民到福州和王海萍、鄧子恢一起組成辦公會。7月,由于福建省委暫難成立,決定組建福州和廈門兩個中心市委,負責指導全省工作。蔡協民任福州中心市委書記兼軍委書記,鄧子恢為五委員之一。
新市委成立后,中央派出的巡視員即趕來檢查。曾志在回憶錄中提到了這個巡視員,她的觀感是:“我見他幾天不出門,一人躲在樓上寫東西,寫了又揉,揉了又寫。事后我才知道他是給中央寫報告,大大告了蔡協民一狀。”不過,從巡視員的報告看,他雖對蔡協民等不無批評,但在最關鍵的社民黨問題上,他未落井下石,而且肯定:“他們幾人的工作情緒還是很好。”或許正由于此,蔡協民等人才逃脫了馬上被清洗的命運,但在被視為立場傾斜、觀點可疑后,仍成為社會民主黨的嫌疑人物。這時,閩粵贛省委又將廈門派往閩西的三名干部以社會民主黨罪名逮捕,在“打了頓,供一點”的狀況下,供出曾在廈門工作的一大批干部,蔡協民也在其中。9月,當福州市委派人到上海中央匯報工作時,上海中央專門派人詢問“福州的社會民主黨活動情形怎樣”,顯然,蔡協民和福州市委已成為重要懷疑對象。從此,他的一切行動都要在有色眼鏡下檢驗了。
【小山城之敗】
1932年1月,蔡協民由于所謂“右傾機會主義”被撤銷福州市委書記職務。歸結其錯誤,是在“九一八”后領導群眾運動時提出“要求省政府驅逐日艦”、“擁護馬占山”等口號。其實,在當時民族危機的背景下,這樣的口號符合民族利益,也恰恰是最能爭取群眾的,但在當時的中共中央看來,這顯然是用民族矛盾掩蓋了階級矛盾。更要命的是,他們還提出蔡協民“認為閩西社會民主黨的反革命暴動不是階級分化”(《仲云巡視福州給中央信,1932年1月25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7冊)這樣一條錯誤,在肅反問題上如此不“堅決”,撤銷職務已算客氣了。蔡協民離開福州后,調到廈門任巡視員,參加下層工作,“在工作中幫助他克服不正確的觀點”。
到廈門不久,蔡協民、曾志夫婦就發現自己陷入了不可思議的尷尬中。廈門市委經費缺乏,聽說曾志生了孩子,把孩子用一百大洋換給了別人。在組織面前,蔡、曾夫婦哪有討價還價的余地,曾志記下了孩子送走前的情景:“我和蔡協民抱著孩子,特意去中山公園玩了一次。我將小鐵牛放在草地上,發呆地看著他,使勁地記住他的模樣。然后又一起去照相館照了張全家福。我抱著鐵牛坐著,蔡協民立于一旁。照完相后,我給小鐵牛喂完最后一次奶,才依依不舍地把孩子交給同志抱走了。送走孩子后,蔡協民便奉命到惠安、泉州等地巡視工作去了。”(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
雖然降了職,雖然遭遇骨肉分離,蔡協民的工作熱情并沒有減退。3月,他在惠北深入農村,領導當地民眾反抗鴉片捐,數千群眾與地方軍閥部隊血戰數日,大大擴大了中共的影響。惠北中共基礎薄弱,蔡協民和同事們十分艱苦,正如他們的反對者所描述的:“槍都沒有一枝,僅一張嘴巴比人會說,身上穿二件薄薄的衣服,齷齪得要命,鞋子也沒有穿,胡子頭發一樣長。”
1932年4月,毛澤東率中央主力紅軍攻占漳州。作為毛澤東的老部下,蔡協民來到漳州,和毛澤東、羅明等同住于原潯源中學校長樓里,他們討論了在這一地區繼續堅持斗爭的策略方針。根據既定方針,中央主力紅軍很快就要離開漳州,地方部隊將擔負起保衛漳州小山城根據地的重任。此時,原漳州縣委書記李金發犧牲,廈門市委書記王海萍原準備自己留在漳州指導一段時間工作。5月初,他在漳州給廈門市委寫信談道:“蔡、曾兩同志還沒有完全轉變過來(蔡比較轉變),因此決定我留此工作一個月或至兩個月,蔡準備隨紅軍出發泉屬,領導泉屬的斗爭。”(《哇利同志(即王海萍——引者注)給廈門市委信》,《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9冊)
王海萍的信說明一直到5月初,蔡協民的去向尚未決定。5月中旬,廈門中心市委決定成立中共漳州中心縣委,由蔡協民暫任縣委書記一職,曾志為組織部長兼軍委秘書。在給中央的報告中,廈門市委說蔡協民“工作能力本不差”,“不過觀念上比較成問題”。顯然,對他的使用是有保留的。所謂觀念問題,在廈門市委不久后的報告中有進一步解釋,即指責蔡協民在惠北領導的抗捐斗爭是“富農路線與機會主義”。這和當時中央領導人對毛澤東的指責如出一轍。
不管上級領導如何橫加指責,在紅軍退出后的緊要關頭,蔡協民仍負起了領導保衛小山城根據地的重任。當時,漳州地區中共武裝力量是新組成的閩南紅軍獨立第3團,集中在以小山城為中心的縱橫一百多里地區。這支部隊最早是陶鑄用綁架地主孩子得來的3000元贖金,買了30多支槍建立起來的。后來,在主力紅軍幫助下,滾雪球般發展,蔡、曾到達時,擴大到800人左右,中共廈門市委對其要求是在“小山城建立政權,鞏固起來向外擴大”。(《陶鑄關于漳州工作及紅軍在漳活動情況的報告,1932年5月22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12冊)事后看來,這一任務事實上不可能完成。
5月28日,中央主力紅軍離開漳州。6月1日,福建地方軍閥張貞出動兩個團的部隊在民團配合下進攻小山城地區。由于對方的兵力十倍于紅3團,紅3團處境十分艱難,幾次戰斗均告失利,政委王占春犧牲。政治上的沉重包袱使蔡協民這個個性極強的漢子沒能堅持游擊戰的方針,幾次否決了包括曾志等提出的將部隊拉出去,以免被動挨打的建議,堅持留在游擊根據地作戰。6月下旬,紅3團在社本一戰中遭到重創,團長馮翼飛戰死,全團僅剩一百余人。小山城保衛戰以失敗告終。
【“失去組織的痛苦,比饑寒交迫更不堪忍受”】
小山城之戰失敗,蔡協民的“右傾”錯誤再次連帶歷史問題被端上臺面。1932年10月,廈門市委專門召集蔡、曾開了三天會,批判蔡協民、曾志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指責兩人犯下忽視群眾工作、錯誤估計政治形勢、逃跑主義等一系列錯誤。
確實,在保衛小山城游擊根據地的過程中,由于群眾工作的不足,紅軍沒有得到民眾的有力支持,在赤白對立的環境下,甚至遭到一些被蒙蔽的白區群眾的攻擊。但是,蔡協民5月中旬才到漳州負責工作,6月初即開始保衛戰,群眾工作非一日一時之功,將這一問題加于他身上,未免有欲加之罪之嫌。
其實,蔡協民對自己的錯誤有清醒認識,錯誤的實質就是低估了對手的力量,沒有及時避敵鋒芒;在力量對比不成比例時,沒有堅持以保存實力而不以保存地域為主要原則。蔡協民和曾志沉痛總結道:“絕對不要機械的不量敵我力量,為保護根據地某一個鄉村不受摧殘,與敵硬戰損失或削弱自己的主力——紅軍。”他們強調:紅軍游擊戰術“是經過血的經驗得來的結晶”。正因如此,他們坦誠表示:“錯誤的性質我們認為是一種立三路線”,是“左”的錯誤。(《蔡協民、曾志對市委檢閱決議的意見書,1932年10月30日》,《福建革命歷史文件匯集》第10冊)
心底無私天地寬,蔡協民確實做到了這一點。在當時“左”的錯誤在黨內占上風的情況下,他直承自己犯了“左”的錯誤并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而且,當廈門市委指責其試圖以“左”的錯誤掩蓋右的實質時,他直言不諱地反問道:“難道左的錯誤比右的錯誤好些、禮面些嗎?不然,‘半斤與八兩的錯誤分量,都是一樣丑的面孔……”
應該說,當主力紅軍離開后,在漳州這樣一個離統治中心十分接近的地區,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當國民黨政權集中優勢兵力進攻時,地方紅軍想要保持根據地更是難上加難。廈門市委要其鞏固并發展政權的指示,本身就是不切實際的空想。蔡協民背負著沉重的政治包袱,又要承擔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其失敗的命運在他剛剛開始工作時就已經注定了。要蔡、曾為此承擔全部責任,無疑是不公平的。但既然蔡協民早就在政治上被懷疑,中共廈門市委7月給中央的報告中更直指“蔡協民夫婦大有社黨嫌疑”,此時又出現這樣的問題,由他們來擔負失敗的責任,不僅是應該的,而且簡直就是政治原則邏輯推演的合理結果了。
1932年11月,在重重壓力下,尤其是和中央巡視員談話后,蔡協民改變了10月份給廈門市委答辯書中的態度,基本上接受了市委對他的指責。不清楚蔡協民為何會作出這樣的轉變,但從廈門市委一個星期后決定給蔡協民留黨查看三個月處分看,如果他繼續堅持原來的立場,等來的肯定會是更嚴厲的處分,很可能面臨著被開除出黨的命運。大概只有這樣的威脅,才能使他低下自己的頭顱。
廈門市委的處分還僅僅是一連串打擊的開始,當時,市委仍安排他參加廈門中共外圍組織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對此,中央巡視員不以為然,嚴厲批評“市委沒有更進一步斗爭精神”,要求廈門市委推行左傾中央正積極貫徹的所謂“殘酷斗爭”。在中央巡視員干預下,蔡協民在反帝大同盟的工作被撤銷,同時市委決定進一步加重處分,留黨察看九個月。
在越來越重的打擊下,蔡協民沒有被完全壓服。此時,曾志已與陶鑄結合,前往福州,他不得不獨力撐頂著壓過來的陣陣陰霾。蔡協民一度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申述。到滬后,上海中央卻斷絕了與他的聯系。蔡協民彷徨無著,流落上海街頭。幸好天不絕人,在黃浦口法租界躑躅時,巧遇老同學,借錢買船票返回福建。曾志記下了她和蔡協民在廈門的最后一次見面:“本來年紀就較大的蔡協民,此時幾乎變成了一個衰弱的小老頭。他痛苦地告訴我,自從廈門分手到上海后,與中央機關派來的同志接上了頭。開始還是好好的,在第二次聯系之后,便再沒有人來理睬了……失去組織的痛苦,比饑寒交迫更加不堪忍受。他有時夜里盡做噩夢,醒來后冷汗淋漓,氣得他腳踢拳砸,把被單撕扯成布條。”(曾志《百戰歸來認此身》)
面對被拋棄的痛苦,蔡協民徹底放棄抵抗,又一次承認錯誤,要求市委“分配他的工作,不論什么工作都可以”。蔡協民對工作的熱情、對中共的執著,使此前對他甚有偏見的廈門市委也不能不懷疑:“他是不是有社會民主黨的作用呢?”確實,很難讓人相信,如果真是與中共同床異夢,他還會在這種狀況下要求回到黨內工作。經市委安排,蔡協民來到打石場做最艱苦的打石工。在繁重的勞動中,他仍不忘黨的工作,力圖在打石工人中建立中共的關系。
6月,由于安溪工作亟待開展,干部需求急迫,廈門市委派他到安溪做兵運工作。到安溪后,蔡協民發揮自己豐富的經驗,工作積極,在頭上戴著右傾機會主義“蔡協民路線”大帽子的情況下,得到自己人的支持,“居然成為安溪中心縣委的后臺老板”。努力工作的結果,并沒有為他贏得上級信任,反而再次遭到嚴厲批評,被召回廈門,此后一直被分派做外圍的下層工作。在某些人看來,此時的他已屬多余,棄之不去,用之不安。
1934年5月,蔡協民在廈門益安醫院從事中共外圍組織互濟會工作時,由于叛徒出賣被捕,旋遭槍殺,時年33歲。
鮮血終于可以為他作證,他是清白的。此時,能為他作證的,似乎也只有自己的鮮血。
(作者系文史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2年第8期,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