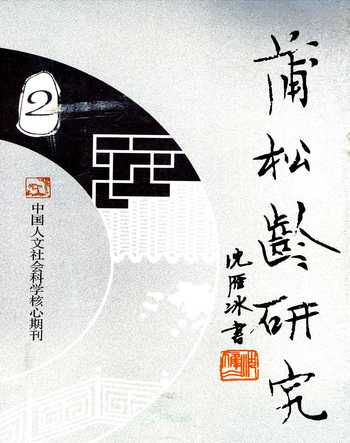歐洲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和靜鈞
【歐洲的沉淪對中國戰略發展不無影響】
20世紀80年代,美國國際政治學家喬治?莫德爾斯基提出了霸權周期理論,強調戰爭與國際政治周期性轉變的關系。莫德爾斯基認為,世界政治與經濟發展呈現一種長周期的特性:每一個周期由一個霸權國家主導,大約持續一百年;一個周期又可分為世界戰爭、霸權、非正統化和分散化四個階段;整個周期呈一種“平衡—非平衡—平衡”的過程。他認為,世界上自16世紀起有五個霸權周期,霸權國家分別是葡萄牙、荷蘭、英國、英國和美國。根據這種理論,霸權國家與挑戰國家的交替出現和相互沖突是國際體系變動的必然結果。
莫德爾斯基以20世紀40年代之前的歷史為考察點得出的結論,也適合于歐洲之興衰。二戰本來拉開了歐洲衰落的序幕,但“馬歇爾計劃”使歐洲重新“續命”50年,歐洲一體化的自覺運動,又助歐洲重新成為多極世界中的重要一極。然而,一體化進程中埋下的“財政炸彈”,最終轉化為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歐洲又有快速下沉之勢。
假如歐洲快速下沉,權力真空擴大,就會使處于霸權一方的國家及其盟國,有直接面對新興力量即挑戰者的可能,雙峰對立,在無緩沖地帶的情況下,雙方勢必掉入“修昔底德陷阱”,重蹈古雅典人被斯巴達人及其盟友圍攻的歷史悲劇。另一方面,歐洲作為新興國家重要的出口市場和技術來源地,也將受到威脅。統計數據表明,2008年中歐雙方貿易額達到4256億美元,歐盟連續5年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歐洲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其地位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日本和美國。然而,2011年的數據表明,中方在不斷提高進口的基礎上,對歐出口開始疲軟。歐債危機下的歐洲,更容易采取保護主義政策,而其需求下降則是主因。
中國的國際發展戰略中,有“新絲綢之路”戰略,表面看是止于敘利亞并以里海能源為核心內容的陸地戰略,實質上則是輻射于環地中海的、使中歐經濟更緊密的發展戰略。歐洲要是沉沒,中國花費巨大的“新絲綢之路”戰略也將變得代價高昂。
我們的判斷應是:歐債危機下的歐洲衰退,是歐洲自二戰之后衰退的延續,屬于大勢;缺少歐洲力量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對新興力量而言變得更加兇險;新興國家應重新接過“馬歇爾計劃”之接力棒,盡量延緩歐洲衰退的速度。
【中歐的雙邊認知差異應當克服】
中歐之間一直存在認知的差異,有些差異是可以溝通和逾越的,有些則難以消除和填平。能溝通的我們應盡量溝通,而對于無法消除的,則應防范差異的擴大和失控。
從2009年起,中國積極向歐盟內個別國家購買債券,中方把這一“債券外交”努力視為援助歐洲的一部分,而歐洲則把它視為中方試圖瓦解歐盟“集體意志”的一個陰謀,意在最終使歐盟取消對華售武禁令。隨著中國對歐直接投資的擴大,歐洲國家普遍擔憂其優質資源將以“割喉”價被中國買走,歐洲最終被中國所控制。由于中國至今在政府采購方面未能令歐洲公司滿意,歐洲人普遍覺得與之競爭的中國公司,是得到“歐洲納稅人”補貼的。這三種觀點并不屬“非主流派”,而是在歐洲有極高聲望的“歐洲外交關系學會”(ECFR)提交歐洲各國政府的報告要點。由于中方對歐洲存在1700億歐元的貿易順差(2008年數據),中方即使與歐洲大國簽下巨額采購合同,也被認為只是在玩弄“貿易武器”而已,這對中國“君子文化”是個極大挑戰。中國的“君子文化”遭遇歐洲“紳士文化”的阻擊,根源在于雙邊的認知差異。
中歐關系有利之處表現在諸多方面,如中歐無人權外交,卻保有人權對話機制;中歐雖無防務協議,卻在許多地區性沖突問題上保持協作。在部分國家積極布控對華禁運之時,中歐卻相繼有“伽利略計劃”等合作,歐洲是中國第一大技術貿易來源,“歐洲設計”與“中國制造”相得益彰。中歐之間有西亞、中亞和南亞的阻隔,在地理上處于相安無事的安全區……然而,正如著名詩人易卜生曾說過的,“東方就是東方,西方就是西方,它們從不相匯”。無論這些是產生于種族主義上的理由,還是產生于歷史文化的差別,抑或出于冷戰思維,中歐在相互打交道之時,應是智慧型的謹慎與開放。強硬地要求對方怎么做,不僅收不到好效果,反而會進一步擴大中歐認知差異。
【保護了歐洲,就等于保護了中國的戰略利益】
中國在援助歐洲的態度上,應是積極的。目前的問題是,我們是僅守住利他主義的立場,還是趁機也提出一些要求,利用“歐洲有求于人”的良機,逼迫歐洲從一些立場上撤退?
歐盟對華禁運起于1989年。1989年下半年,當時歐共體的決策機構歐洲部長理事會在馬德里開會,宣布對中國采取包括中止高層接觸、中止軍事合作和文化交流等在內的5項措施,其中有關軍事方面的措施是:“共同體成員國中止與中國的軍事合作并禁止與中國進行武器貿易。”這短短的一句話,構成了今天“歐盟對華軍售禁令”的法源。
為了達到解禁的目標,中方對各國廣下訂單,多頭下注,投入了很多,但最后解禁之路甚至比未明確提出之時還要難走。解禁要取得所有歐盟成員國一致同意,這就是一個“不可逾越”的制度障礙:只要其中一個國家阻止,中方就得下更大的成本促使其改變主意,這樣只會鼓勵一些國家故意“犯難”,借機使自己利益最大化。即便是暫時取得了一致同意,只要在表決前其中一個國家反悔,就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更不用說有美國在背后反對的因素了。
另一個問題是歐盟承認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相較而言,根據世貿規則,中國只要能等,數年后會自動獲得市場經濟地位,而軍售禁令則一直懸在那里,沒有一個自動機制能破除。所以,從中歐關系的意義上看,解除禁令至少能證明歐盟為對華關系發展付出了巨大努力。不過,“解禁”與“解禁努力”是兩個概念,“禁運”消失了,“軍控”還在,即便“解禁”,也不意味著中方就會買到真正想要的武器裝備,最先進的技術大部分依然不會輕易拿出來交易。這就像即使美國的盟國有時也很難買到美國的好武器,例如日本一直想購入美國的“猛禽”F-22戰斗機,美國卻一直未點頭。
近期外媒集中報道中國自主研發先進軍備的消息,漢和防務評論創辦人平可夫指出,中國的確已研發出可與美國第五代戰機一比高下的隱形戰機殲-20。外媒也注意到,中國海軍潛艇或掌控了只有極少數國家才掌握的AIP技術,而一直在海外議論的“航母殺手”遠程巡航導彈東風-21D,據傳也在開始部署,中國自己制造的航空母艦會很快駛入大洋。不論這些消息是真是假,我國通過二十幾年的潛心努力,已經具備了研發先進武器的一流實力,這恐是歐盟想不到的結局。總之,歐盟解禁與不解禁,現在只是一個政治姿態而已。
中方只要體認到一些敏感問題會導致歐盟內部分裂,并不再堅持這些問題的解決,中歐的認知差異就能最大限度彌合。當人們把解禁等不再視為妨礙中歐關系的最大問題之時,中歐就可以集中精力,以務實主義的精神解決更能產生效益和促進歐洲團結的問題。從根本上說,保護了歐洲,也就等于保護了中國的戰略利益。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2年第8期,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