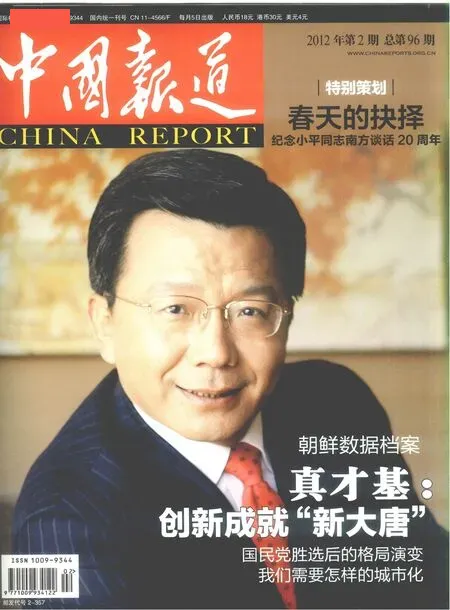從故鄉到荒野的自然沉思
丁歌
每一個地方,并不屬于這個地方所有的人,它只屬于對這個地方敏感的心靈。荷蘭導演迪格娜·辛克就是這樣讓Tiengemeten屬于了她。她以一顆詩人的哲思之心保留了那個富有田園氣息、名叫Tiengemeten的小島——一個已經不復存在的家園和故鄉。
迪格娜完成于2010年的紀錄片《懷念鄉野》(Wistful Wilderness)于2011年12月在北京iDOCS國際紀錄片論壇上展映,它那長鏡頭中鄉野的靜謐、畫外音的感傷和整體畫面的哲思意味,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懷念鄉野》記錄的Tiengemeten小島13年來的主要變化是將其從井然有序的農耕中移植出來,恢復其“原生態”的荒野狀態。作為以故鄉身份消逝的Tiengemeten,最終還是人們在考量人與自然的不平衡關系中而作出的決定。但迪格娜在這個基礎上走得更遠一些,她思考的是在這個過程中,人做了什么,又失去或者得到了什么?人之于自然的關系,正是迪格娜用鏡頭去努力追尋和探索的。
經過世代多年改造、擁有700畝良田的Tiengemeten島是荷蘭南荷蘭省的一個島嶼。上世紀90年代,在環保組織保護濕地和候鳥的吁求下以及基于航運對深水域的需求,荷蘭內閣批準了“退耕還海”方案。大片圍海造田得來的“開拓地”將再次被海水淹沒,恢復為可供鳥類棲息的濕地。
在“退耕還海”中,作為一些人的故鄉和家園的Tiengemeten就要因此而消逝。對于生活在Tiengemeten島的那些農場家庭,他們在這里保留了世代、記憶,形成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已經融入這塊土地以及這里的天空、大地、陽光和四季的風雨霜雪。這是他們相處和諧的自然。然而現在他們要搬遷,他們的家園將變成陌生的荒野。
《懷念鄉野》中導演選擇了7個定位拍攝點,從1996到2007年,在Tiengemeten島作為鄉野最后的這段時光里,記錄了這里的景色、四季和農民。那夏季瓢潑的大雨接天連地,冬天簌簌的雪落滿田野,在凝固的鏡頭中充滿了頗具力量的美感。農場主們的勞作也有一種天然的安寧,他們耕耘、收獲,田野充滿了豐收的意蘊,那些帶著新鮮泥土的土豆和山芋,從收獲的機器里骨碌碌地進入糧倉……這一切讓人想起荷爾德林那句:“充滿勞績,然而人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
迪格娜在《懷念鄉野》中用了很多長鏡頭,如同靜靜的凝視和對即將消失的一切的細致的打量和撫摸,加上款款情深而優雅的畫外音,讓人確切地感受到Tiengemeten島人對這片土地的眷戀和感情。在凝視的畫面鏡頭中,導演似乎一直在質問:我們要將這些淹沒嗎?我們要失去它了嗎?
2007年后,島內正式回歸自然。導演來到他們一個定位拍攝點——鄉村的丁字路口,開始搖拍,鏡頭緩緩轉動,現在這里已經是一片濕地,原先的道路消失了,農民們的房屋和谷倉飛走了,路旁的樹木已蕩然無存,除了凸起的高地就是海水……
略帶感傷的畫外音開始訴說,她在追問人類改造然后恢復如此循環往復的意義在哪里。影片末尾,一股悠揚的小提琴流進畫面,消逝了的鄉野歲月再次出現在鏡頭里,直到結束。
不管對迪格娜還是對觀眾,變遷的世事就是這樣復雜無常。后工業時代,人與自然脆弱的關系讓人格外焦慮和憂心。工業時代“開拓者”的形象及其文化開始隱退,而前工業時代那種“詩意地棲居”也無法重現。面對自然,我們承擔后果也努力對未來負責,但更為尷尬的是:我們改造自然,我們又恢復自然,然而我們卻難以融入自然。
——以《山河故人》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