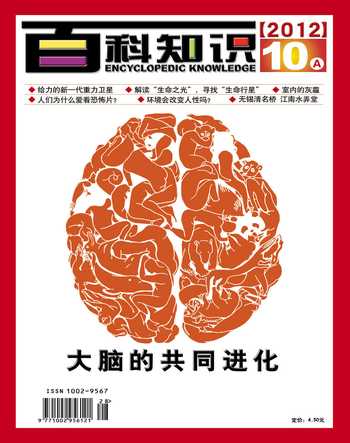古代的宴飲禮俗
朱筱新
宴飲是古人常用于招待賓客的一種方式。通過宴飲,既能表現主人的熱情和對賓客的尊敬,又能增進主人與賓客之間的感情。在宴飲中,增加一些娛樂性的游戲,則更能增添宴飲時的歡快氣氛。
遠在周代,天子或諸侯在與群臣宴飲之時常要舉行射箭活動,稱為“燕射之禮”。燕禮,亦作宴禮,是古代天子、諸侯與群臣的宴飲之禮。“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有功,故與群臣樂之”。可見,燕射禮在周代已成為一種宴飲中的娛樂活動,并被編入禮儀制度中。
燕禮中射箭的靶子稱為“侯”或“射侯”,系布或皮革制作而成,上面繪有各種動物圖案。按照周禮的規定,天子所射的侯為白色的熊皮制成;諸侯的侯則用紅色的麋鹿皮制成;大夫的侯用布制成,上繪虎、豹圖案;士亦用布制作侯,上繪鹿、豕(豬)圖案。燕射禮由射入(周代官名,又分大射正、射正、司正三級)主持,負責監督君臣射侯。射箭的距離為50步,無尊卑之分。凡射中侯多者為勝,少者則需罰酒。在宴飲中加入射箭活動,給君臣的相會增添了歡快的氣氛和更多樂趣。
燕射禮因需要一定的場所,且還有等級的劃分,所以其使用的范圍受到限制。但這種活動的形式畢竟能給宴飲帶來樂趣,所以古人又改以“投壺”活動,以使宴飲的氣氛更加活躍、歡快。
投壺,原為古代的一種游戲,由于投壺能助酒興,古人便將其用到宴飲上,遂成為流行一時的一種宴飲禮儀。在《禮記-投壺》中,就詳細地記載了“投壺禮”。
在宴飲進行中,主人拿出矢(亦作棘,形如箭,一端尖如刺),盛情邀請在座的各位賓朋:“某有枉矢(意指箭桿彎曲之箭)、哨壺(意指口歪之壺),請以樂賓。”客人則答謝:“子有旨酒(即美酒)、嘉肴(即佳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經再三邀請,見主人盛情難卻,賓客遂接過矢。賓客中較主人年長或位尊者接過矢後,可將矢放置在席上,取一支投一支;如是較主人年幼或位卑者,則需將矢抱在懷中,不能放在其他地方。
按照投壺禮的規定,投壺分輪進行,一般要進行3輪。每一輪發給每位賓客和主人各4支矢,每次只投1支矢。由于投壺禮可以在不同場所進行,場所的活動空間大小不一,故投壺所用的矢又有形制上的區別,活動空間越大,所投的矢也越大:室內投壺,矢長二尺;堂內投壺,矢長二尺八寸;庭院內投壺,矢長三尺六寸。矢越長,投擲的距離越遠。所投的壺,就是放置在宴席間的酒壺,壺口較小,壺頸較長。
投壺開始前,主賓先共同選定一位裁判——司射,由他負責確定壺擺放的位置,并監督投壺和計算每人投入壺中矢的數量,通常壺放置在宴席南側二矢半遠的地方。
投壺開始後,賓客和主人輪流將自己的一支矢投向壺口,司射則用“箅”(古代用于計數的一種籌碼)計算每人投中的數量。每投中一矢,司射就在投中者面前放置一笄。之後每人再執第2支矢,依次輪流投壺。直至4支矢全部投完,由司射根據每人所得笄的數量,確定投入壺中數量最多者為勝者。第一輪結束後,再向每人發4支矢,進行第二輪的投壺。待三輪投壺結束,以二勝或三勝者為最終的優勝者。其余的輸者則向優勝者祝賀,并受罰飲酒。
舉行投壺禮時,沒有長幼、尊卑的區分;投壺的先後,則按照席位的順序排列。不過,如有不按照順序搶先投壺者,即使投中,司射也不給筭,甚至還要罰酒。
由于投壺是一種十分有趣的游戲活動,既活躍了宴飲的氣氛,使賓客處于熱鬧、歡快的氛圍中,不至于拘謹;又能融洽賓主間的關系,增進友情,故深受人們的歡迎。漢代,投壺禮已普遍流行于社會各階層人士舉行的宴會上,且成為社會追求的一種雅興和時尚。“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這種宴飲時的娛樂活動,一直延續至唐代仍十分流行。
古人宴飲時,還有一種“行酒令”的游戲,也是用于為宴飲助興取樂、活躍宴席間的氣氛。
在行酒令前,賓主亦要共同推選一人為酒令官,由他制訂行酒令的游戲活動內容和規則,并主持活動。眾人對被推選的酒令官也有一定的要求,他必須先飲酒,以示受眾人之命,開始行酒令之職。眾人則須服從酒令官的決定,或依令做游戲,或依令賦詩作詞。違者或所做詩詞不佳者,即要受罰飲酒。
這種于酒席宴上舉行的游戲活動,自唐朝以後極為流行,尤其是深受文人雅士的喜愛,成為一種流行一時的文明、高雅的宴飲娛樂活動。在南宋詩人蔡寬夫的《蔡寬夫詩話》中就提到:“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樂。”
曹雪芹在《紅樓夢》第四十回《史太君兩宴大觀園,金鴛鴦三宣牙牌令》中寫道,賈母、劉姥姥、史湘云等眾人在大觀園宴飲時,賈母先笑道:“咱們先吃兩杯,今日也行個令,才有意思。”于是王熙鳳便推舉鴛鴦行酒令。鴛鴦半推半就,謝了坐,便坐下,也吃了一鐘(盅)酒,笑道:“酒令大如軍令,不論尊卑,唯我是主,違了我的話,是要受罰的。”隨後,她便用“骨牌副兒”(用二或三張骨牌上的色點配成一套,稱為一副)作韻,令每個人用詩詞歌賦、成語俗話與之和韻。
在宴飲時,因有行酒令的游戲,所以沒有高下尊卑之分,賓主之間亦無拘謹之感。大家可以談笑風生,氣氛活躍、融洽,極易增進情感,加深友情。
【責任編輯】王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