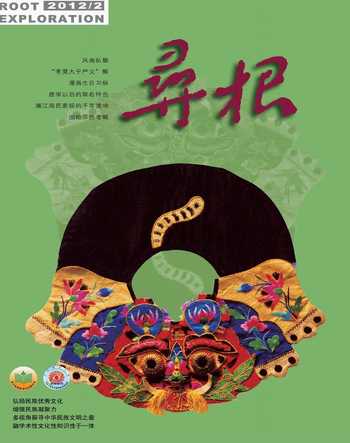浦江鄭氏家規的千年遺響
施賢明
一
浦江鄭氏自南宋初年同財共爨,明英宗天順三年(1459年)遭火災而瓦解,共經15世。李靜《義門家族的壽命與婚姻狀況分析》(《江淮論壇》2004年第5期,第96~99頁)據《義門鄭氏家譜》估算,鄭氏人口在元至大三年(1310年)、至正十年(1350)年、明建文二年(1400年)、宣德五年(1430年)依次是32人、92人、244人、355人,以此度之,天順三年鄭氏人口至少在400人以上。
義門鄭氏的同居生活雖然早已結束,但它留給人們的記憶與遐想卻不會煙消云散。時至今日,鄭氏宗祠仍然靜靜地矗立在浙江省浦江縣東部鄭宅古鎮。宗祠古色古香、滄桑凝重,正門高懸“鄭氏宗祠”匾;旁門坐北向南,檐上懸明太祖敕封的“江南第一家”匾,門前兩旁“耕”“讀”“忠信孝弟”“禮義廉恥”十個大字斑駁陸離,支撐門廳的四柱之上分別題有“三朝旌表恩榮第,九世同居孝義家”與“文章空冀北,孝義冠江南”,仿佛在向人們訴說著輝煌的往事。
俗語有云:國有國法,家有家規。龐大的鄭氏家族就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家規。
宋濂《旌義編引》載:“(鄭氏)持守之規,《前錄》五十八則,六世孫龍灣稅課提領大和所建,《后錄》七十則、《續錄》九十二則,七世孫青府君欽、江浙行省都事鉉所補,皆已勒石鋟版。”“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濤復以為三規閱世頗久,其中當有隨時變通者,乃帥三弟泳、澳、,白于二兄濂、源,同加損益而合于一。其聞諸父之訓,曾行而未登載者,因增入之,總為一百六十八則。”
家規《前錄》《后錄》以及《續錄》撰于元順帝時期,三者文本只見于永樂刻十卷本《麟溪集》。需要明確的是,宋濂所言《后錄》及《續錄》條數有誤。十卷本所收鄭欽《后錄》現存62條,第23條之后殘佚一頁,注云“以下缺七條”,而鄭欽《鄭氏義門續規序》亦稱:“演而繹之,成《續規》,亦六十余條。”(《義門鄭氏奕葉文集》卷一)鄭欽所撰當為69條;另外,該本所收鄭鉉所著家規為93條。
自《鄭氏規范》損益而合于一之后,大行于時。今所見《學海類編》本《鄭氏規范》一卷(《叢書集成初編》本據以排印)、胡鳳丹輯編《金華叢書》本《旌義編》二卷以及民國重刻本等,所收家規無一例外均是168條這一最終定本。
費孝通在《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中寫道:“家的規模大小是由兩股對立的力量的平衡而取決的,一股要結合在一起的力量,另一股要分散的力量。”(商務印書館,2001年,第42頁)鄭氏家長孜孜以求的便是強化聚居的向心力并削弱可能導致分裂的因素,家規的宗旨即在于此。
心理上的認同是義門聚居的基礎。一方面,敬仰與追慕祖宗是凝聚后人的有效力量,祭祀則在禮儀與心理上強化這種認同。《前錄》首五則均是言祠堂與祭祀之事,鄭欽則繼續在細節上予以強調,包括“當用黲淡衣服”等;另外,鄭大和僅言宗子“當嚴扃,所有祭器服不許他用”。《后錄》中則有三條規定宗子“上奉祖考,下一宗族”的職責。鄭欽意欲重塑宗子這一先祖與后世族人之間的精神媒介,體現了鄭氏家長敬宗收族的深度考慮。另一方面,家人唯有孝弟,才能共同營造認同感,和睦共處。《前錄》規定:“朔望,家長率眾參謁祠堂,畢出,坐堂中,男女分立堂下。擊鼓一通,令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凡為子者,必孝其親;為妻者,必敬其夫;為兄者,必愛其弟;為弟者,必恭其兄。”在祠堂中供奉的祖先觀照下反復申飭孝弟之道,鄭大和可謂用心良苦。《續錄》在聽訓接受的基礎上,通過令人羞愧的懲罰措施不斷強化對先祖事跡和家規的記誦,極大增強認知與心理上的認同感:“子弟已冠而習學者,每月十日一輪,挑背其已記之書及《譜圖》、家范之類。初次不通,去帽一日;再次不通則倍之;三次不通則分髻如未冠時,通則復之。”所謂《譜圖》,當指吳萊后至元元年(1335年)所著《鄭氏譜圖》,為鄭氏歷代人物小傳。
義門聚居依賴于財富,明初時鄭氏家族良田面積底線是8620畝,甚至可能數倍直至十倍于此(毛策:《孝義傳家—浦江鄭氏家族研究》,浙江大學出版社,第228~229頁)。如此雄厚的家資無疑是鄭氏得以綿延15世最堅實的物質保障。那么,鄭氏是如何積累財富的呢?鄭大和僅言通掌門戶有增拓田業之任;鄭欽則首先為儒士不屑道的積累財富正名,“增拓產業,彼則出于不得已,吾則欲為子孫悠久之計”,進而明言,“家長當令子孫以理生財,補助公堂之費”;而《續錄》詳列義門近二十種職務的職責,不僅農業生產由專人職掌,副業亦復如是(“牧藝之事,當以一人專總其綱”),而且嚴格規定增拓產業的程序:“增拓產業,長上必須與掌門戶者詳其物價等,然后行之;或掌門戶者他出,必伺其歸,方可交易。然又預使子弟親去檢視肥瘠及見在文憑無差,切不可魯莽,以為子孫之害。”“掌門戶者置他人產業,即時書于產業簿中,不許過于次日。”這種變化正是逐漸壯大的鄭氏對財富的依賴與訴求日益強烈的反映,也體現出至正末年鄭氏家族組織業已定型,對家族資產的營運也日漸規范。
不過,對私有財產的訴求卻是不容小覷的導致分裂的力量,這一點相信鄭大和早已洞若觀火。《前錄》規定:“子孫倘有私置田業、私積貨泉,事跡顯然彰著,眾得言之家長。家長率眾告于祠堂,擊鼓聲罪而榜于壁,更邀其所與親朋,告語之所私,即便拘納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論。”鄭大和通過對私置產業的嚴懲來保障義門財富的單一傳承,確保絕對的經濟均勻性,減少分裂傾向。
二
孝義家風是累世同居的基礎與必備條件。孝義行之于家,家庭才能和睦;推之于鄉鄰,既是義門的自覺追求,也在客觀上促成儒士對義門的揄揚與支持,進而得到文官集團背后的皇朝的褒揚與優待,這股力量正是義門累世同居最堅實的外部保障。
鄭氏的先祖即有樂善好施的美名。靖康歲儉,同居一世祖鄭綺之祖鄭淮賣田一千多畝以賑濟災民,以致家道中落。元末至正年間,鄭氏同居業已6世,頗具規模,自覺擔負起賑濟鄉鄰的職責。《前錄》明確規定:“每歲秋成,谷價廉平之際,糴三百石別為儲蓄。遇時艱食,依元價糶給鄉鄰之困乏者。”作為地方有能力的大族,鄭氏此舉相當于建立了一處小型的常平倉,平價出糶,既可以平抑市場物價,也可解災民燃眉之急。《前錄》又規定建義宅一區、義冢一所,使鄉鄰無所歸者生有所居、歿有所葬。與《前錄》僅有三則言及對鄉鄰的周濟與賑濟不同,《后錄》中竟有十余條家規詳述扶困救急之事,內容涵蓋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方方面面,這是已成規模的鄭氏在道義上的自我修持,也是其立身之基。鄭欽首先強調:“宗人實共一藝所生,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理勢然也。”宗人“其果(裹)無衾與絮者”,當量力資助;缺食者,“月給谷六斗”;“不能婚嫁者助之”;“營義方一區,以教宗族之子弟,免其束”;甚至宗人無后,則“擇親近者為繼立之”。至于鄰族里黨,除了不過問宗嗣之事,余亦有詳細規定,“每歲量力以錢五百貫文用以拯(里黨)患難之無告者”;里黨有缺食者,產子“不問男女,給助粥谷二十五升”等。
《后錄》第19條有云:“展藥市一區,收貯藥材。鄰族疾病,其證章章可驗,如瘧痢癰癤之類,施藥與之,更須診察寒熱虛實,不可慢易。此外不可妄與,恐致誤人。”以如此謹慎的態度救死扶傷,鄭氏真可謂積善之家!
三
鄭氏以孝持家,義舉推及宗人鄉鄰,成為士人心目中理想社會圖景的映射。于是,士人不吝筆墨,對義門氣象的書寫濃墨重彩,鄭大和裒輯而成《麟溪集》,嗣后時時補益并屢次重刻,這證明人們關于鄭氏的記憶并沒有隨著同居大家庭的崩潰而消逝。社會對儒家倫理、孝義家風的呼喚,鄭氏后裔對先祖德業的自豪與追慕,這兩股力量使得鄭氏成為一種典范的象征與想象:一種道德的象征,一種治家的典范,一幅和諧社會圖景的想象與憧憬。
記憶不曾淡去,想象也會與日俱增。民國年間,西學東漸,被一些浸淫于“四書五經”中的儒生視若洪水猛獸,斥之為“自新學橫流,異端競進;自由平等,荒謬絕倫”(民國刻本《麟溪集》卷首黃志琨《序》),便再度祭出義門,重刻《麟溪集》,試圖借此歸化人心、降服“異端邪說”,終究只能事與愿違。
那么,時至今日,義門鄭氏的意義何在?鄭氏家規的千年遺響究竟是和諧的樂音,還是遲暮腐朽的喪鐘?
鄭氏扶困救急是仁義之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孝義—義門的核心價值永遠不會過時,它依然是當下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訴求的。
不過,鄭氏家規并非全然可取。譬如,鄭大和之父德璋主家政時,“每晨興,擊鐘集家眾,展謁先祠,聚揖有序堂上,申‘毋聽婦言之戒”,大和則將此寫入家規。此外,鄭氏家長對莊婦、媵也有頗多鄙棄之語,以地主士族的優越感俯視婦人與勞動者,無疑是家規中的糟粕。
正如前文所述,一般而言,五世同堂是不分裂的極限。換言之,即便以剔除糟粕的鄭氏家規為指導,試圖在當下復制一個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仍然是癡人說夢。這種特殊的家庭組織形式很大程度上憑借的是唯心道德的維系,鄭氏家規的文本處處折射出義門倫理的艱難。
鄭氏家長對“家業之成,難如升天”(《后錄》)有清醒的認識,于是不斷強化義門的心理認同,并且嚴格保障絕對的經濟均勻性,盡可能減少分裂傾向。除此之外,在細節上補充《前錄》的《后錄》,滿目盡是禁忌;《續錄》則嚴格限制諸婦、子女與姻親往來,而且規定媵女不得妄出中門,加之前文所言對人、莊婦的限制,體現出鄭氏家長在相對封閉的時空中實踐這種特殊家族組織形式的努力。細節的規定與禁忌愈多,活動的空間愈封閉,愈呈現出義門倫理的不合時宜與艱難。我們似乎看到,那個精致而又承載著儒家倫理與士人理想的標本在被賞玩,眾人嘖嘖稱贊,但構建標本的鄭氏家長與族人卻不得不小心翼翼、戰戰兢兢。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