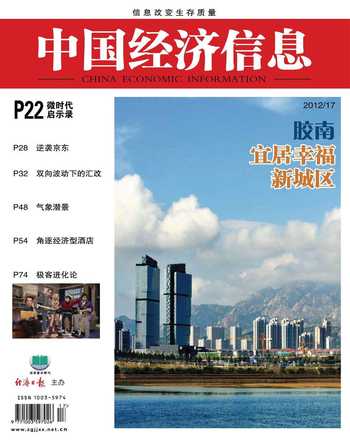沒有希望的失業
布拉德福德?德隆
勞動力市場將面臨結構性市場參與失靈,沒有簡單容易的藥方可以把這個問題治愈。
從商業周期的角度講,不管眼下全球經濟多么困難,這只是看待世界的一個視角而已。
從全球壽命預期、世界總財富、技術整體水平、新興國家增長前景和全球收入分配看,形勢一片大好。不過從其他領域看來,全球經濟則相當糟糕,比如全球變暖、國內收入失衡及其對各國社會穩定的影響等角度。
即便從商業周期角度看,如今的情況也比過去好得多。想想1929年開始的大蕭條給市場經濟造成了多大的沖擊,由于當時受到長期失業的重壓,市場經濟根本無法自力更生走向復蘇。
盡管我們今天還沒有走到這般田地,卻也不能說大蕭條跟我們一點關系都沒有,因為有種狀況的可能性正越來越大,即長期失業將在未來兩年對復蘇造成類似大蕭條的影響。
在1933年冬天的低谷時期,大蕭條簡直稱得上是集體性精神紊亂。到處都是游手好閑的工人,因為沒有企業雇用他們;企業不雇用工人是因為它們看不到產品的銷路;而產品沒有銷路是因為工人沒錢消費。
當時,大量失業已經轉變為長期失業,并造成兩個后果:第一,經濟失調的負擔并不是被公平地分擔的。由于消費價格比工資下跌得更快,大蕭條時期保住就業者的福利有所上升。丟掉工作并一直處于失業狀態的人承擔了絕大部分惡果。
第二,讓失業者重新回到市場經濟十分困難,即使是運轉平穩的市場經濟。有多少老板會舍棄職場新鮮人,而選擇已失業多年的人呢?經濟剛剛經歷了大量失業時期,這一簡單事實使得之前理所當然就能達到的增長和就業水平變得艱難。
貶值的匯率、溫和的政府預算赤字以及時間,看起來皆非良藥。高度集中的工會化勞動力市場(比如澳大利亞)與分散的自由放任勞動力市場(比如美國),在長期失業面前一樣束手無策。法西斯主義(比如意大利)同樣解決不了問題,除非伴隨迅速的軍力擴張(比如德國)。
最后,在美國,是“二戰”的逼近以及伴隨而生的軍工產品需求,促使私營部門雇主開始以可接受的工資水平雇用長期失業者。然而直至今日,經濟學家仍無法清楚地解釋,為什么在1933年到全面戰爭動員開始前的近十年時間里,私營部門無法找到雇用長期失業者之道。各地勞動力市場和國家制度各不相同,持續性失業的程度表明,精確描述某個方面重大失靈的理論只能是部分成立。
最初,大蕭條時期的長期失業者急切而努力地尋找其他工作。但是,在找工作半年而未果后,他們變得心灰意冷、心煩意亂。失業一年后,典型的失業者仍會尋找新工作,但已不再十分上心,也不抱有多大希望。而在失業兩年后,失業者會認為對于任何一個職位,自己都是最后才被考慮的人選,他會喪失希望,并從現實的角度考慮,離開勞動力市場。
這就是大蕭條時期長期失業的模式,也是西歐20世紀80年代末長期失業的模式。而在一兩年后,這也將成為北大西洋地區長期失業的模式。
四年來,筆者一直強調,我們的商業周期問題需要更積極的擴張性貨幣及財政政策,只有采取這樣的政策,我們最大的問題才能較快地解決。這一點目前仍然成立。
在未來兩年中,除非當前趨勢被突然地、出乎意料地打斷,否則這主張可能就不那么適用了。
從目前看來,發生概率較大的情況是,今后兩年,北大西洋主要勞動力市場失靈將不再指向需求面市場失靈——這類失靈是可以通過更積極的政策刺激經濟活動以及就業來輕松解決的。勞動力市場將面臨結構性市場參與失靈,沒有簡單容易的藥方可以把這個問題治愈。
作者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國民經濟研究局副研究員、美國財政部前部長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