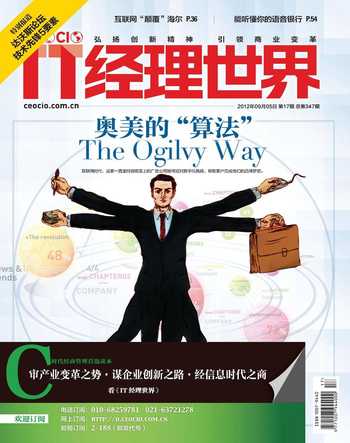曙光:“技術宅”變身
孫泠

下午2點,位于中關村軟件園的曙光大廈頂層露臺上熱氣蒸騰,曙光CEO歷軍和COO王正福在攝影師的指揮下擺出各種造型。頂層通往辦公層的電梯里貼著曙光新浪官微的大幅廣告——“親~曙光有官微了喲!聽取客戶意見更方便!”
這樣的場景在一般IT公司稀松平常,但對曙光這家貼滿“高性能計算”、“863”、“國家戰略”等標簽的“技術宅”型公司卻有著特殊的涵義。用句套話來說,這是轉變的一小步,卻是曙光的一大步。
王正福來了
香港人王正福在中國大陸的IT之旅開始于1987年,25年后的2011年4月,他從AMD 公司全球副總裁兼大中華區總經理的職位離開。聽到這個消息歷軍心里一動,因為江湖傳聞王正福很有運營經驗同時又是個很講義氣的人,“我跟他并不熟”,雖然內心覺得希望不大,但歷軍還是決定努力一把。
第一次碰面約在酒店的咖啡廳。歷軍上來就直抒胸臆——“中國IT界缺乏一個紅色巨人”,如果王正福“不嫌寒酸”,可以來曙光換換環境。王沒吭聲。幾天后他們又在那家酒店見面,深思熟慮后的王正福對歷軍表示:在外企干了一輩子,錢,足夠了。自己這個歲數,希望能找到家有思路、有抱負的公司,一直做到老。
2011年6月,王正福正式加入曙光出任集團COO一職,搬進了位于圓明園東門的曙光小院兒,歷軍交代的唯一任務是“半年內什么都不用干”,就是了解情況、了解曙光。
出身于中科院計算所的曙光公司問世之初就帶著濃濃的技術味道。上世紀70年代,美國研制的計算機已經達到了每秒2.5億次的運算速度,而中國直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研制的計算機,每秒僅能運算1000萬次。這種性能高、速度快的計算機被稱為高性能計算機HPC,發動機設計、模具設計、生物新藥設計、新材料的研制、風洞試驗仿真、石油勘探與開采等應用都離不開它。
在李國杰院士的帶領下,1993年5月,“曙光1號”問世,同時,我國高性能計算的產業化道路也從此啟程。當時,剛從清華大學應用電子技術專業畢業的歷軍還是毛頭小伙子,正在北京無線電儀器廠應用技術部工作。1995年,歷軍調入中科院計算所,被任命為曙光產品與研發中心總經理。
在國家“863”計劃的持續支持下,計算所先后研制成功了曙光1000A、曙光2000-I、曙光2000-II和曙光3000機群結構超級服務器,建立了“曙光”這一國產高性能計算機品牌。業務的快速發展,讓中科院計算所辦公區不堪重負,于是曙光從計算所搬到了位于清華大學附近的水磨西街小院兒。
2003~2004年,曙光4000-L型、曙光4000-A型高性能計算機研制成功,使中國成為除了美國、日本外第三個能夠制造和應用十萬億次商品化高性能計算機的國家,并在2004年6月進入全球高性能計算機TOP10行列,我國成為繼美國之后第二個可以獨立研發、制造超百萬億次計算機的國家。
從2000年開始,曙光踏上了快速發展之路,除了高性能計算和服務器,如存儲、安全、云計算產品同樣取得了很好的市場份額。根據2011年IDC公布的數據,曙光存儲市場占有率達到了全球第8,國產并列第二;曙光的城市云業務在包頭、無錫、成都、南京4座城市開通運營;2012年第一季度,曙光的服務器銷售額在國內市場排名第四,國產品牌排名第一。2011年,曙光的高性能計算機銷售額同比增長62%,達1.03億美元,成為進入全球HPC銷售額十強的唯一一家中國公司。
歷軍有些歉意地對剛入職的王正福表示:目前只有衛生間旁邊的一間辦公室還空著,曙光在中關村軟件園的大廈還在裝修……王正福對此并不介意,比氣味更讓他敏感的是周圍很多雙眼睛在看著自己。曙光從來沒有從外企引入過職業經理人,大家都在觀察——王正福講話會不會夾英文?PPT做成什么樣子?他到底能呆多久……歸根到底,外企的“貴氣”與曙光的“地氣”究竟能不能合拍?
水清,水混
曙光以技術見長,管理團隊也基本都是“技術宅男”出身,缺乏企業運營經驗簡直是注定的。“曙光的管理經驗都是自己摸索,一點點從實踐中來的。比如采購應該怎么做,當初是趕緊去書店買幾本書,看看別的企業怎么做,然后一邊試一邊改。”歷軍說,面對快速發展的曙光,他每天陷入生產、送貨、質量、銷售等方方面面的問題中,疲于奔命卻四處漏風,解決問題總是“按下葫蘆起來瓢”。
最讓歷軍光火的是,做大的同時,“混日子”的思想開始在企業內部蔓延。“一直到今天,依然不斷有人問我,怎么看待‘水至清則無魚這句話。”這是個曖昧的問題,希望公司是一盆混水從而混水摸魚的愿望卻異常清晰。歷軍認為自己需要定下心來,從企業文化和流程再造兩方面“想想曙光未來幾年的大事兒”。
于是,今年初歷軍把運營的柴米油鹽事都交給了王正福,自己在辦公室關上門琢磨“重要但又不那么緊急的事兒”。在外企25年的王正福的管理方式細致又規矩,他把自己每天的日程表在企業內網上公開,曙光所有員工想找他可以直接預約,公開透明。和過去“上司拍肩膀,下屬拍胸脯”的項目管理方式不同,王正福對于每個項目都親自找負責人談話,了解各個環節;每月出差去各地辦事處,是潛力市場就留下幫助辦事處解決具體問題,比如在廣州辦事處王正福就足足呆了兩個星期。“曙光現在年收入20億元,我不敢說能把曙光做成什么樣,爭取帶企業上一個臺階,收入做到50億元。”王正福說。
歷軍認為,王正福為曙光帶來的并不是策略和業務上的創新,而是規范的企業運營方式。“什么事兒我不說不行,我一說就算定了,有意見的也不敢說了。”歷軍對事無巨細都來請示、不推不動的做事風格也很無奈。王正福啟發手下的年輕人自己獨立自主地考慮并解決問題,“項目交給你了,就要你來動腦筋把它完成”,遇到進展緩慢的他會開玩笑——“你們怎么能跑得比我還慢?”
理順流程的同時,企業運營過程中的暗藏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比如,曙光有些產品成本明顯比競爭對手同類型的高,細查下去發現原來在采購環節沒有形成集中采購,供應商的價格壓不下來。年底盤點,雖然采購數量不比對手少,但整體成本高出競爭對手一大截。
再比如裝服務器的機柜,過去總是從曙光的深圳基地運到天津總部,拆開配置好再安裝上,最后發往全國各地。“后來發現有很大一部分是發回廣州的。一個機柜5000元,深圳-天津-廣州的運費就要1000元。這是什么?就是運營不夠精細化嘛!”
倆人分工明確,配合默契。王正福在現有的流程下,查漏補缺,杜絕“機柜南北往返”的現象,完成年度銷售目標;歷軍則專注優化流程與企業文化建設,讓曙光運營的效率更高。如今,王正福遇到昔日在外企的朋友常常被挑大拇指——“福總,夠膽!你做了我們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將技術拉下神壇
2012年3月,曙光從圓明園東路的偏僻的小院搬入中關村軟件園建筑面積25000平方米的曙光大廈。員工們說:原來鄰居是花江狗肉,現在鄰居是跨國公司。與身邊的這些鄰居相比,曙光的客戶以高校和政府機構為主,業務也集中在高性能計算和服務器上。
云計算和高性能計算是曙光的立足之本,也是“豪門盛宴”——幾乎所有國際級大廠商都參與到這一競爭中來,要在其中求得發展,除了追求更加精湛的工藝技術、更加精確的計算技術、更加精彩的方案設計外,曙光還必須將這兩樣都“拉下神壇”。
曙光公司成立十年的時候,歷軍曾感嘆“曙光十年時間就做了一件事,在高性能計算機產業里建立自己的地位。”無論是進入全球超級計算機排行榜TOP500前10名,還是在中國TOP100中占據30%的份額,曙光都肩負著“國家戰略”的重擔。“很多人都不理解,為什么我們要參與軍備競賽一樣的高性能技術競爭。但是我想既然要做就要做出水平,要在這一過程中爭取獲得超越自己的經歷。”歷軍說。
產業和技術一定是互相支撐或者依托的,離開產業談技術沒有意義,離開技術談產業沒有根基。與國內大多互聯網公司集中在應用層面的“微創新”不同,曙光走的始終是硬碰硬的基礎研究產業化道路。近20年的研發積累,曙光高性能計算產品雖然不被大眾看到,但已經深刻地影響到大眾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氣象、石油勘探、生物制藥測序、神五、神六、神七載人飛船從發射到回收的全過程,甚至北京奧運動漫渲染等領域,都有曙光高性能計算的身影。
曙光推出的100萬億次曙光5000系列。“100萬億次”的概念就是一秒鐘執行100萬億條浮點計算指令,一個天文數字的方程組可以在瞬間處理完畢。
這頭“神獸”最終安家在上海超算中心,提供超級計算的公共服務。“比如上海大眾汽車開發新車型,到設計開始到產品下線要撞88輛車。有了超級計算機進行模擬,可以大大縮短開發周期,只在實物測驗的時候撞一輛就可以了。”大眾在德國有自己的計算中心,但很難在中國再建一個,上海超算中心幫它解決了這個問題。“在當前的云計算環境下,首先有了實際應用,云計算才能夠真正覆蓋更多使用者,才能最終立足。”歷軍說。
今年曙光專門成立了云計算子公司,加快在國內二、三線城市的云計算中心的建設,未來計劃在國內建立超過30個云計算中心,完成云計算戰略布局,深化“服務提供商”的角色,用歷軍的話就是“要多掙服務的錢”。同時,今年新增的金融、能源和互聯網三個行業,讓商務云、行業云成為城市云的補充和延伸。“曙光給自己的定位不是最便宜的,但希望是最好的。”王正福說,
解決方案所有廠商都有,曙光的解決方案能夠給用戶提供帶有多年技術積累的行業價值。“曙光200多個技術支持工程師,50多個在各行業領域的首席工程師,他們通常不是學計算機的,而是學石油物探、氣象、化學、金融的。在每個行業領域的里面,這些又懂計算機又懂行業的專家是曙光最寶貴的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