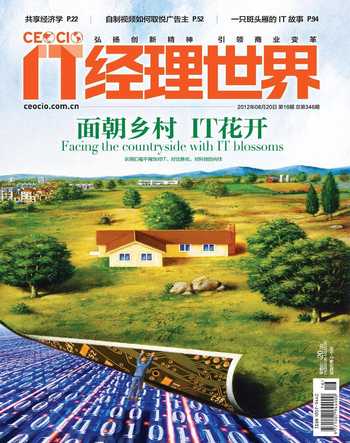歐洲城市的尷尬
托馬斯·史班達

幾十年來,當沙特爾這座中世紀的法國城市需要為一個市政建設項目籌資時,當地官員只需要走進坐落在市政廳和附近13世紀的輝煌大教堂群中的任何一間銀行即可。
而今年,他們必須將目光投向更遠的地方——甚至“遠”到中國北京。由于無法籌集資金以維持基建項目的正常運轉,沙特爾市長最近已向中國北京求援,希望通過商談獲得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的項目貸款。
這絕非個案。隨著奧朗德總統著手處置一堆棘手的由歐債危機引發的經濟貨幣問題,銀行被迫收緊償付能力規定,法國人面臨一項新挑戰:很多地方政府的市政建設項目都斷了糧。
這將給經濟發展帶來非常不利的影響。因為在歐洲,絕大部分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包括道路、下水管道和醫院等)都是由政府主導的,而歷年發生的新基建項目70%是在法國。由于歐洲各國的地方政府現在都在為資金籌措而費盡心思,市政資金的缺口在可預見的未來都難以很快填補。
巴黎近郊的索鎮領導人兼法國市長協會財政委員會主席菲利普·勞倫稱,如果這個洞不被及時填上,那么高度倚賴市政項目訂單而維持生計的建筑公司、維修商等連接緊密的產業生態圈都將受到重創,進而加大當地經濟壓力。
更不利的是,歐洲缺乏依靠發行債券來為市政建設項目融資的環境文化,這使目前市政資金鏈條斷裂的危局找到解決方案而少了一個可選項。在美國,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來融資是稀疏平常的事情,加上投資收益有稅務減免、而且有益于社會福祉,所以市場普遍視之為一種比較安全的投資方式。——但是在歐洲,市政項目沒有發債融資的大量先例,就拿英國來說,地方政權發放債券的行為自20世紀80年代起便不受鼓勵,唯一的例外是在2004到2006年間,倫敦交通當局為籌集鐵路建設資金而破例發放債券,當時出現了供不應求的局面。
現在再來討論發行債券的可行性也許為時已晚。因為,市場各方普遍擔心歐洲政府無力償還債務而由此加大投資風險,就連國債利率在近期都一度瘋漲,更遑論地方政府發行的債券呢?有行無市的局面難以避免。
當然,要責備銀行為遵循緊縮的償付能力規定而導致大量削減市政基建的放貸,似乎也勉為其難。要知道,在西班牙,由于地方政府在償還貸款方面的無能為力已經迫使該國政府預撥了350億歐元的信用額度作為壞賬沖抵。去年12月,馬德里政府不得不為巴倫西亞地區的政府基建投資無力償還而出手解救。
如今,歐洲的大部分銀行面對呆賬和壞賬已經停手作債權打包-證券化處理,而只能無奈地看著它們高高掛起、懸而不決。在債期匹配上,銀行也將執行更嚴格的合規政策。“我們現在已經無法像過去那樣,去市場上獲得短期融資、再去發放長期貸款;”法國興業銀行總裁兼法國銀行聯合會董事長菲德烈·烏戴爾說,“雖然這在過去是銀行業司空見慣的作法。”
銀行并非完全排斥地方政府作為借貸方。法國農業信貸集團的區域零售銀行總秘書長菲利普·布拉薩克就公開聲稱道,只要地方政府將其現金留在銀行(作為儲戶),他們就可能再次成為被追逐的銀行客戶。只不過,這一點暫時還難以付諸實現——根據目前的法國政府規定,地方政府必須將現金貯存在法國財政部、而不是銀行。也許,任何僵局的背后都脫不了結構性連環問題的干系。
在歐債危機中也盛行著關于“緊縮還是增長”的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似乎眼下的市政資金斷鏈也為其中的爭議作了一個注腳。一些批評人士指出,現在該是地方政府與國家政府一起勒緊腰帶節省開支的時候了。過去由于過松的貨幣供給,很多歐洲的地方政府在基建項目上花費無度——譬如,法國就建有3萬多條環形交叉公路,數量是德國的四倍之多,“但事實上,許多環形交叉公路都建造在鮮有密集交通狀況出現的鄉村次級公路上。”一位批評人士說。
而在另一邊,包括保羅·克魯格曼在內的一些具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則反對“緊縮論”的解決之道。他們認為,歐洲的緊縮政策勢必阻礙經濟活動,從而帶來適得其反的市場和社會效應。保羅·克魯格曼在其專欄中寫道,應設法通過經濟刺激政策而不是通過縮減開支來試圖償還債務。
我不是經濟學家,因此無法判斷到底是“刺激政策”還是“緊縮政策”最后能解決我們面臨的根本問題——那就是:歐洲其實沒有足夠的生產力來為歐洲人現有的生活方式買單。當然,很多歐洲人不愿意承認這個事實,所以他們選出來的政客都是那些承諾將徹底改變“不受歡迎政策”的人,比如延后退休年齡等政策······而這些,會真的解決根本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