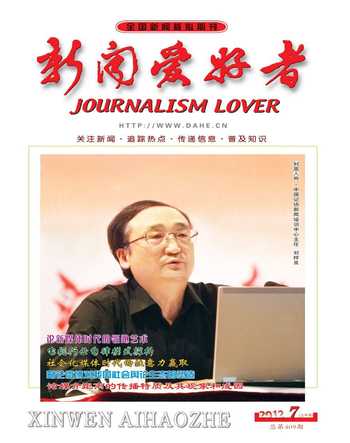電視時評欄目《映象版》的框架解讀
盧慎勇
【摘要】本文從框架理論的視角,梳理了河南電視臺大型原創時評欄目《映象版》的誕生及其架構,對其如何主動融入“建設中原經濟區”及承載的“話語意義”、“再現方式”等進行了闡釋與解析。《映象版》作為一個媒體符號呈現出的圖景和對各種事實的篩選與述評,為構建當下河南這一區域的社會現實提供了一個“框架”,這種“程序性”架構方式使欄目擁有了獨特的話語范式,賦予了新聞事實歷史意義與價值,擔負起了一種歷史使命:統一認識,凝聚人心,調動受眾的注意力“共建”中原經濟區。
【關鍵詞】框架;符號;程序;意義
2011年10月7日,隨著新華社《國務院關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設中原經濟區的指導意見》正式對外發布,標志著建設中原經濟區的大幕正式拉開,中原崛起、河南發展駛上了一個快車道。作為主流媒體,河南電視臺早在構建中原經濟區規劃過程中,就發揮了其大眾傳播議程設置功能的作用,展現了“傳媒的調查功效(報道)”、“詮釋功效(解釋)”和“交往功效”(編導),吸引了公眾對“中原經濟區”的關注、討論與熱議,為“中原經濟區”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營造了良好的社會輿論氛圍,承擔了傳媒的社會、歷史責任。那么在建設中原經濟區的過程中,河南電視臺又應該如何應對,才能為事關一億多中原人民福祉的大業更好地發揮出主流媒體的作用?尤其是作為河南媒介符號的主要代表——視聽媒介,如何利用自身視聽形象的傳媒優勢來闡釋“中原經濟區”的意義、價值與實現路徑,從而展現河南的新形象?這是中原經濟區在納入國家主體功能區之后,河南電視人就開始探索的一個大課題。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更是傳媒的主動作為、主動選擇。在河南省廣電局黨組的支持下,一個由河南電視臺新聞中心精心打造的電視新聞節目——大型原創時評欄目《映象版》(以下簡稱《映象版》)應運而生,并漸漸走進了公眾的視線。
美國社會學教授蓋伊·塔奇曼(Gaye Tuchman)在其代表作《做新聞》(Making News)中把新聞看做一種“框架”(Frame),說它是了解世界的一個窗口。他認為“窗口展示的視野取決于窗口的大小、窗格的多少、窗玻璃的明暗以及窗戶的朝向”,視野還取決于視點的位置。而加拿大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nian,另譯為高夫曼)在其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經驗組織論》中認為“框架”是約束著我們主觀參與的事件的“組織原則”。本文就從考察《映象版》如何主動融入“建設中原經濟區”入手,圍繞其承載的“話語意義”及“再現方式”,對河南電視臺這個原創新聞節目的“組織原則”,即《映象版》這個窗口的內涵、視野及視點的位置等進行闡釋與解析。
時空坐標上的意義解析
蓋伊·塔奇曼在定義新聞的“框架”時認為新聞從根本上說具有一種機構屬性。它有三層意義:第一是一種向消費者發布信息的機構方式;第二是合法機構的聯盟;第三是由以組織方式而進行工作的專業人員來采制和傳播。即“新聞必然是新聞工作者通過機構程序并遵循機構規范而生產的產品”。解析《映象版》的“框架”,首先應該還原它問世時的時空坐標。
《映象版》的策劃、設計肇始于河南電視臺衛星頻道、新聞頻道2011年8月6日22:05并機播出的《轉變領導方式推進中原經濟區建設新十八談映象版·用人篇——以求實之魂 樹用人新風》,定型于2011年9月4日播出的《轉變領導方式推進中原經濟區建設新十八談映象版·發展篇——崛起之路更寬廣》,成熟于2012年2月15日22:05播出的《建設中原經濟區走好“三化”協調科學發展路——“十八談”映象版·洛陽篇》。追蹤欄目策劃、設計的時空坐標與路徑,便會發現它不僅僅是河南廣電傳媒充分調動“機構程序”、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對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提出的“新聞宣傳要努力破‘四難:正面報道難、典型宣傳難、輿論監督難、新聞創新難”命題的積極回應,更是對其中的“新聞創新難”的再一次“機構反應”和深層次上的探索與實踐。以下即是“機構反應”的例證:
從2012年2月7日《建設中原經濟區走好“三化”協調科學發展路——“十八談”映象版·鄭州篇》開始,除了河南電視臺衛星頻道、新聞頻道并機播出外,河南廣電傳媒集團旗下的河南人民電臺、河南手機電視、移動電視、大象網、河南廣播網、新浪網河南頻道、《東方今報》以及各省轄市電臺、電視臺要么同步轉播《映象版》,要么全文轉載。這種“機構屬性”帶來的時空傳播與當下建設中原經濟區相關的政治、經濟、社會背景有機地結合在了一起。廣電傳媒在構建中原經濟區“話語場景”(建設中原經濟區當事方的描述、解釋性評論和視覺編輯)中發揮了“社會鏡子”的作用,同時作為社會的“瞭望者”,也可以算是對“前路”的一種探尋。節目播出后隨之產生的反響互動見證了這一效果的呈現。
中原經濟區的戰略規劃從醞釀到提出,再到成功晉升為國之方略,離不開新聞工作者的職業關懷,因為媒體關注的議題往往能成為新聞受眾認為最重要的議題。關于議程設置的大量研究早已證明了“媒體對議題關注度的權重會影響受眾對同樣議題關注度的傾向性”,因為“新聞把單純的事件轉化成公眾討論的事件”。新聞生產是一種社會行為,它之所以成為社會行為的基礎是因為材料選取于日常生活之中,然后“把我們大家做的事情呈獻給我們大家看”,“在記錄社會現實的同時也是社會現實的一種產品”。所以《映象版》的誕生為定義和構建當下河南這一區域的社會現實提供了一個“框架”。作為新聞傳播組織機構的參與者,其制作者河南電視臺新聞中心的編導們就被賦予了典型的社會行為,正是在這一層面意義上他們擔負起了一種歷史使命,凝聚人心,調動河南受眾的注意力來探尋或者接近真理的道路。
獨特的架構與理念傳播的平臺
“新聞構建中的位置及其與消息源的關系決定架構方式”,而架構方式又影響著媒體的視野和受眾的解讀。《映象版》從問世的那天起就構建了一個原創的節目形態,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架構方式。追蹤它呈現的形態與運行軌跡,可以解析為以下幾個環節:1.特邀中央電視臺著名節目主持人張紹剛擔當主持人;2.邀請直接參與河南經濟社會發展決策與建設的省直單位與省政府組成部門的一把手以及各省轄市的書記與市長做客演播室接受主持人訪談;3.邀請國家層面的各個行業的權威專家、學者現場評說與解析;4.邀請龍永圖擔任首席評論員;5.邀請著名評論家、上海文匯報高級編輯、原評論部主任潘益大先生為特約評論員;6.新聞短片描述新聞事件;7.網友熱議;8.百姓心聲以及現場觀眾互動;9.實施衛星頻道和新聞頻道并機“周播”機制。2011年8月30日出版的《東方今報》總結《映象版》的獨特性時這樣定位:把報紙時評搬上了電視熒屏,這是全國獨創;電視專門開辦大型時評欄目,也是全國獨創;河南電視臺利用全國資源來辦《映象版》,理念非常超前,這也應該是全國獨創。這一系列架構不僅使河南省直系統以及各地有了一個為建設中原經濟區出謀劃策的平臺,更重要的是通過這種獨特的架構方式傳播了河南社會各界與各地建設中原經濟區的理念和現實路徑的選擇。
從已經播出的節目看,這種架構方式還使得消息來源不但是“一手”的也是無距離的,更是權威高端的,這樣就直接決定了欄目的視野和影響力。比如《映象版·發展篇——崛起之路更寬廣》邀請河南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張維寧,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李平研究員走進演播室,圍繞河南建設中原經濟區,持續探索走不以犧牲農業和糧食、生態和環境為代價,以新型城鎮化為引領的“三化”協調科學發展之路的路徑選擇展開探討。《映象版·工業篇——新型工業化主導譜新篇》中河南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廳長楊盛道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工業經濟研究所前所長呂政就河南如何以新型工業化為主導,為“三化”協調科學發展作出貢獻,以及河南在走好新型工業化的道路中,面臨的困難和破解之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解讀。《映象版·農業篇——新型農業現代化強基固本》中河南省農業廳廳長朱孟洲和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趙長保圍繞河南省如何做好糧食穩產高產、如何推進新型農業現代化等問題探討發展思路和途徑。
綜觀往期《映象版》呈現的圖景以及對各種事實的篩選與述評,這種“程序性”架構方式使欄目擁有了獨特的話語范式,也組成了欄目自己的詮釋框架。因此它通過其承載的一期期獨一無二的“框架”和詮釋體系,賦予了新聞事實歷史意義與價值,也擁有了“定義現實的權力”。誠然,評估《映象版》在河南經濟社會方面的影響力也許當下還為時尚早,但這一創新欄目對河南電視傳媒在構建社會輿論方面的作用已經明顯上升。同時欄目搭建的平臺不是簡單地將電視簡化為單純的傳播技術,而是開創了一個全新的討論公共議題的表達模式;再者欄目采用的新聞短片多以回顧新聞產生的事實為基礎,加上嘉賓的述評和特約評論員的點評,將受眾帶向了參與未來的“框架”。
媒介符號的文化表征
《映象版》的宣傳語是“實現科學發展的新思路、轉變發展方式的新實踐、破解發展難題的新探索、促進中原崛起的新動力”。它顯現的意蘊特質與法國著名新聞傳播學者雷米·里埃菲爾的《傳媒是什么》一書的副標題“新實踐·新特質·新影響”不謀而合。這種傳媒特質的普適性,為《映象版》節目提供了一個可供參考的理論坐標。因此雖然電視不是唯一構建輿論的元素,但《映象版》這個欄目置身于正在生成的歷史之中,它構建的現實以及對擴展認知中原經濟區的能力和引發的輿論滾雪球效應無疑承擔了一種符號編碼功能。
美國人類學家克林福德·吉爾茲(Clifford Geertz)在《文化的解釋》一書第一編里指出“文化概念本質上是一個符號學的概念”。恩斯特·卡西爾在《人論》中指出“人是符號的動物”,在他看來人類社會的所有文化形式都是“符號形式”,而符號的基本功能在于表征(representation),各種不同的符號承載了文化的不同含義。分析《映象版》傳播引發的熱議和它討論的一個個話題,如果從文化視角審視,便會發現,對于生活在各種符號里的受眾來說,作為一個傳媒文化產品,《映象版》每一期都在進行著不同的文化意義編碼,媒介符號文化表征的意義也由此塑造著、傳播著積極而又正面的各類形象(包括欄目構建出的各級政府形象,新型城鎮化、新型工業化、新型農業現代化的圖景,以及中原城市生態群像),《映象版》在某種程度上已成為建設中原經濟區的一個“符號”。
新聞傳播學研究中把“真實”分為三個層面:客觀真實、媒介真實和主觀真實。那么與此對應,一個區域的形象是否也可以表述為三個層面?即區域的實體形象、區域的虛擬形象和公眾的認知形象。其中區域的虛擬形象就是由承載文化內涵的各種媒介符號構建的,而某一區域的虛擬形象對公眾的認知形象的建構將起到決定性的作用。[1]《映象版》不論是“省直篇”還是“城市篇”,都彰顯出各自特定的文化價值理念(一種精神潛流、精神特質),每一期都以富有特色的文字、聲音、圖像等視聽符號幫助受眾認知接收的各種信息,并以此形成日后行動參考的“情景架構”。“傳媒是構筑思想的工具”。比如建設中原經濟區中如何做到“三化”協調科學發展、新型工業化如何發揮主導作用、各個城市怎樣發揮自己的特色和構建自己在中原經濟區中的定位等一系列的價值判斷和情感導向。對這些多樣性現實的本體認知都將通過符號化的“影像”來呈現,并且將會在很長時間內影響著人們的行動。
結 語
新聞工作者的時空組織是在他們的活動中發揮作用的。我們相信若干年后,《映象版》本身將成為一種歷史的贈與,因為在它實施與傳播的過程中,它表征的文化價值不僅僅定義和再定義、構建和再構建了它的社會意義,同樣它也將定義和再定義、構建和再構建它隸屬的機構的現存程序——制度化和組織化的原則和程序,而這樣的原則和程序又將被用來作為未來行動的資源。
參考文獻:
[1]張愛鳳.媒介變遷與中國國家形象的嬗變[J].新華文摘,2012(3).
(作者為河南電視臺新聞頻道副總監,主任記者)
編校:趙 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