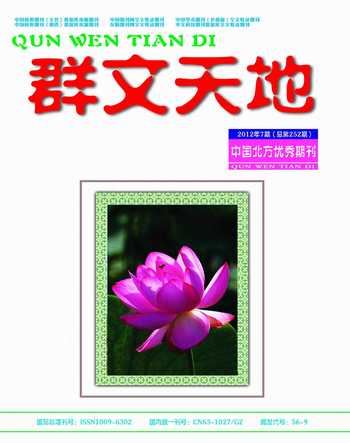淺析柏拉圖思想對雪萊詩歌創作影響
摘要:懷特海曾說,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的一連串注腳。從詩歌方面看,柏拉圖的本體論和關于藝術創作的“摹仿說”“靈感說”等文藝思想對后世西方的詩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詩人雪萊深受其思想影響,被柏拉圖放逐的詩人竟成了其精神遺產的真正繼承人。文章將從雪萊的詩歌創作理論和實踐中尋覓柏拉圖思想的余光。
關鍵詞:本體論;靈感說;繼承;發展
雅斯貝爾斯提出了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柏拉圖無疑是西方文明“軸心時代”最偉大的思想者之一。懷特海曾說,兩千五百年的西方哲學史不過是柏拉圖的一連串注腳。可見柏拉圖思想對于后世西方思想影響巨大。柏拉圖曾在《理想國》中驅逐詩人,而這恰恰開創了西方詩學“為詩辯護”之路。
亞里士多德成為文學史上第一個為詩辯護的人,他的詩辯雖然得出了與柏拉圖相反的結論而認為詩有存在的合法性,但亞氏的論爭并沒有否定柏拉圖詩思的基本框架與理性主義原則而是給它更大的彈性,從而強化了這一框架和原則濫觴于亞里士多德,經過黑格爾一直發展到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雪萊。
(一)雪萊與古希臘的關系
雪萊與古希臘關系深厚,他在伊頓公學讀書時,就以古希臘語成績優異而聞名。他深諳柏拉圖主義哲學,熟讀亞里士多德、盧克萊修等先賢著作,曾經親自翻譯過包括《會飲篇》在內的部分柏拉圖作品,并自費印刷數冊在朋友圈子內散發。
(二)對柏拉圖本體論的繼承
柏拉圖提出“理式”論,認為自然是理式的影子,并著有著名的有關洞喻的故事,出現在《理想國》第七卷(514A~520E)中。他指出,我們都是被囚禁的徒人,我們眼前見到的,都不是事物的真實,不能看到陽光(理性)和真實的事物(信念),只能看到投影(猜測或想象),并以此為真。在雪萊的大量詩中,秉承了這一思想。如《含羞草》中 “我們這一生 既然充滿了謬誤、愚昧、紛爭, 無所謂真實,一切都是表象, 當我們只是夢影在游蕩”,在《阿特拉斯的女巫》中,”對于愛、美和欣喜,沒有死亡和變易。”雪萊認為,他眼中的世界,也只是某種表象,是虛幻的影子而已,永恒性存在在理式中,而對現實生活則持有一種否定的態度。從某種角度可以說,雪萊的這些詩歌是柏拉圖的理式論的抒情詩翻版。這一思想突出地體現在《愛的哲學》詩中,“天宇的輕風永遠融有 一種甜蜜的感情; 世上哪有什么孤零零? 萬物由于自然律 都必融匯于一種精神。” 從雪萊的詩中,我們不僅看出了來自柏拉圖的理式論,更看到了雪萊對于柏拉圖理式論的變化和發展。在雪萊的思想中,世界上存在一種“一”的精神,主宰一切,產生一切,他指出:“一個詩人渾然忘我于永恒、無限、太一之中”而非柏拉圖眼中那個“桌子有桌子的理式,貓有貓的理式”的概念。
此外,雪萊在《為詩辯護》中反復重申,詩歌的神圣在于它“撕去這世界的陳腐的面目,面露赤裸的、酣睡的美——這種美是世間種種形相的精神,”“詩是生活惟妙惟肖的表象,表現了它的永恒真實。”可見,雪萊不僅僅是贊同柏拉圖認為的藝術模仿是的表象世界而已,而是對詩歌的現實功能加以肯定。相比較柏拉圖,雪萊更重視詩歌,認為其有很大的社會作用,不同于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驅逐詩人。
(三)對柏拉圖靈感說的繼承和改造
柏拉圖眼中,靈感來自于神的憑附,表現為迷狂,《斐德若篇》中,提到了幾種迷狂,“其中詩歌的迷狂由天神繆斯姊妹們主宰,這種迷狂是由詩神憑附而來。它憑附到一個溫柔貞潔的心靈,感發它,引它到興高采烈神飛色舞的境界,流露于各種詩歌。”
在詩的創作發生論上,雪萊繼承了柏拉圖的“靈感”說。作為雪萊的詩論深受柏拉圖影響的典型例證,《為詩辯護》中有一段話每每被后代的研究者所引用。雪萊說:“一條鎖鏈通過許多人的心靈傳遞下來,系在那些偉大的心靈上,它的神圣鐵環從未完全脫節的,而是那些偉大的心靈,如同磁石,流出不可見的磁力,同時連接著、振奮著、支持著所有的生命。”其實,這段話之所以值得重視,不僅因為它源自《伊安篇》,是對柏拉圖的靈感論所作的一種改造,更因為它是雪萊縱論詩歌發展史時所持的基本的詩歌共用觀。認為“詩 的 靈感之來 ,仿佛是一種更神圣的本質滲透于我們的本質中 ;但它的步伐卻像拂過海面的微風,風平浪靜了,它便無影。”
不同于柏拉圖的“靈感說”單指頌詩的創作,雪萊將這種靈感用來解釋自己的詩歌創作,而不單單是“神的代言人”。這方面,雪萊對于柏拉圖“靈感”說有了自己的改造。
1.靈感來源更為寬泛
柏拉圖的“靈感”是來自神,而沒有詩人自身的創造性,而在浪漫主義詩人雪萊這里,他認為“詩是不受心靈的主動能力支配的,詩的誕生及重現與人的意識或意志也沒有必然的關系。”但是,“我們往往感到思想和感情不可捉摸地襲來,有時與地或人有關 , 有時只與我們自己的心情有關,并且往往不能預見 ”,說明靈感的來源不僅僅是神,而也有“地與人”,“心情”有關,是不能預見的。
2.靈感創造的詩不僅僅是神的頌歌
柏拉圖在《理想國》里面,是驅逐詩人的,而僅僅保留了一部分英雄和神靈的頌詩。雪萊則不然,他認為,詩人所有的創作,皆來自靈感,在他的筆下,更是有大量反映現實生活,歌頌美麗愛情等等不同體裁的詩歌。
在雪萊的筆下,詩歌具有很大的藝術張力和魅力,“詩歌的無限擴張,乃是詩人作為創作主體的自我擴張的表現形式之一,然而,把詩歌與人類的其他創作活動混為一談,顯然無助于確立一種有價值的文學理論。正如當代美國學者R 韋勒克所指出:“詩歌在哲學、道德和藝術的籠統綜合物中全然喪失其特性。可以歸結為三者或其他兩者之一的東西是不能認真地僅僅歸之于詩歌的。”
身處十九世紀的雪萊在繼承靈感說的同時,也發展了靈感說,使得靈感說帶有了時代的痕跡。
(四)其他方面
除了上述兩個方面,雪萊詩歌中還明顯透出了柏拉圖式愛情的理想主義色彩。柏拉圖思想對于雪萊等詩人影響重大,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為“柏拉圖的著作比亞里士多德的具有更多真正偉大的藝術思想”,
正如當代美國學者MH艾布姆斯所指出,人們可以從雪萊的詩論中分辨出兩個思維層面,其一是柏拉圖主義的,其二是英國經驗主義的,他似乎把這兩者交替地應用于所討論的每個主要問題上了。
的確,柏拉圖在西方思想史上有著他人無法超越的地位,一代又一代的西方學者生活在其“影響的焦慮”下,其文藝思想對西方詩學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更是決定性的,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他奠定了西方詩學的基礎。
參考文獻:
[1]劉明月.柏拉圖文藝思想對后世西方詩學的影響[J].青年作家.2011.5
[2]余虹.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M].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
[3]穆小莉.雪萊愛情詩中的柏拉圖思想和悲觀意識[J]. 西安教育學院學報.2003.3
[4]牟娜娜. 雪萊詩歌創作和愛情觀中的理想主義[J].作家作品新論.
[5]江楓譯.雪萊抒情詩選[M].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7.
[6]楊冬.雪萊.《為詩辯護》及其柏拉圖主義[J].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1,3.
[7]R 韋勒克.近代文學批評史,第二卷,英文版,1955.
[8]艾布拉姆斯.鏡與燈[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
(作者簡介:盧姍(1993.04-),江西人,現為中南大學文學院2009級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