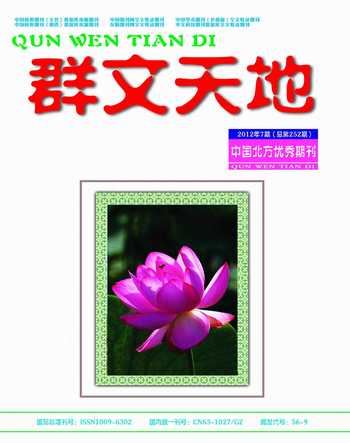中國音樂美學的主體間性探究
摘要:中國傳統文化在處理人與對象的關系時具有“主體間性”,這種“主體間性”使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得以表現出來。自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音樂美學發展開始由客體中心轉向了主客共建的模式,使主體在音樂認識中的意義逐漸凸現出來,出現了主客間性的新思路;至二十世紀后期,逐漸發展成為主體間性,解決了主客間性帶來的客觀性危機,并由此發展出來中國音樂美學中的“和”(本質論)、“傳神”(表現論)、“韻味”(審美論)等核心范疇,因此,主體間性成為了中國音樂美學具有鮮明特色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音樂美學;主體間性
一、前言
音樂美學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誕生于西方十九世紀中期,追溯其學科內容的歷程來源,歷史較為久遠,始于迄今2000多年前的古希臘。中國的音樂美學是基于中國傳統音樂發展而來,中國傳統音樂具有自身鮮明的特色,但在以往對于傳統音樂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對于音樂形態描述的層面上,近些年來,研究者們開始將研究的深度拓展開來,深入到了文化層面,從而追求對音樂更深一層的理解。當前,文化層面的研究維度主要是通過音樂與地區民俗、宗教、經濟方式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關聯考察,還沒有達到整體性系統性的高層次理論。在這些研究中,研究者往往在利用“主體間性”的特質處理人與對象的關系,從而使音樂的境界提升至中國文化中所謂的“天人合一”、“物我交融”的精神境界。簡而言之,“主體間性”影響了在中國文化土壤中孕育成長起來的中國音樂美學,并使之獲得了鮮明的特色。
說了這么多“主體間性”,讓我們來看一下“主體間性”究竟是什么。“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是二十世紀西方哲學的重要概念,它的提出是為了解決西方認識論中由于主體性的加強而帶來的客體性危機。主客關系是一直貫穿于西方認識論發展的重要理論,在十七世紀以前,一直處于客體性為中心的階段,此時,認識被理解為主體對客體本身屬性的真實反映。直到十七世紀笛卡爾的出現,使主體性的地位開始逐步上升,隨著人們對于認識論了解的不斷深入,于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出,主體在認識中的作用和意義逐漸凸現出來。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發現觀察者和研究者在對對象進行描述時,不可避免地介入其中,這一發現帶來了認識論的客觀性危機,因為知識是不依賴于認識者而獨立存在的,而知識的提供是依賴于人的認識活動,認識活動的主觀性與知識的客觀性產生了矛盾,使認識不再能夠充當構筑知識大廈的磚石。之后,“主體間性”的出現緩和了這一矛盾,認識的過程不再只是對事物本身的原樣呈現,而是事物通過人的意識得以建筑自身,知識的客觀性不是存在于事物的本身,而在于知識主體之間。知識的存在不是只接受知識客體本身的檢驗,而是在享用知識的主體之間被約定的。
二、音樂美學的主體性與客體性
音樂美學史上有主體性和客體性兩大傳統,他們從表面上看是互相對立的,但從深層次上體現著共同的認識論模式。從本體論的角度出發,產生了主體性研究和客體性研究,這種研究放置于音樂美學上,有兩個傾向,一種客體性研究,即是把音樂的本體歸結為世界、宇宙、自然本身或音樂形式本身,排除于人的因素,是存在于人之外的某種實體。另一種是主體性研究,即把音樂首先看城市人的心靈和情感的表現,看成是人的自我的外化。這是兩種不同的觀念和階段。但他們有著相同的認識論模式,他們都重視音樂文本在音樂活動中的獨立性和決定性地位,重視音樂文本本身的客觀性和絕對性。
我們對于音樂作品的研究,在客體性的階段當然也要研究主體,在研究作品本身的同時,還要研究作品背后的一些因素,諸如作者生平,時代背景之類。一個音樂作品的創作,這些因素都客觀地表現在作品之中。同樣,作品一經創作出來,就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客觀的存在,我們對于作品的研究,是研究客觀存在的作品,與研究者無關,研究者只需如實將作品中的東西拿出來給大家看就行。而在主體性階段的研究,并非單純的類似于浪漫主義音樂是表現激情的主觀體驗,而是同客觀性階段一樣,將作品當做一個獨立的、客觀存在的實體來對待。浪漫主義雖然認為情感表現是音樂的本質,但情感一旦表現在作品中,它就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并且獨立于欣賞者之外,不依存于欣賞者的存在。情感是客觀的存在于作品中,我們在研究時是需要將其客觀地分析出來就可以了。從認識論的角度上來看,音樂作品是一個純粹的課題和對象,它獨立與我們之外而存在,我們只需要用同樣的認識論方法去對待它,將作品打開來,使作品內含的意義呈現在我們面前。從這方面來看,音樂美學的主體性和客體性是一致的,它們有著共同的文本中心的傳統。
三、音樂美學的維度轉換
二十世紀以來,我國對于音樂的理解維度發生了變化,在這里我們稱之為維度轉換。這種轉換表現在兩個階段,首先是在主客間性中解讀音樂的美,然后是在主體間性中尋找音樂美學的基石。
1、在主客間性中解讀音樂的美
二十世紀的哲學,經歷了一個以主客間性為基礎來解讀音樂等藝術和社會現象的階段,于此同時,音樂美學也在同樣發生著轉變。主客間性是指對對象的認識不是僅僅著眼于客體,也不是僅僅著眼于主體,甚至也不是即著眼于客體,又著眼于主題,而是傾向于在主體與客體的互相對待和關聯中解釋自己的對象。
從主客間性的角度研究音樂美學最為突出的成績是心理學音樂美學,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格式塔美學。格式塔理論中最重要的范疇是“完形”、“同構”。格式塔作為心理學派,以非純客體的方式研究事物的形式,或者事物形式中的數學關系。此外,波蘭美學家英格爾登的著作《音樂作品及其同一性問題》中,從現象學的角度對音樂作品的存在方式進行了深入的考察。她從音樂作品存在哪里開始發文,在一一排除了音樂作品就是樂譜、就是音響、就是干瘦的虛擬結論之后,向我們指出,音樂作品不是一個無知的存在,而是人的意識與文本之間的一種關系性存在;它不是一個純粹的課題,而是在人的意識作用下的意向性客體,即存在于由人的意識和客體本身所形成的意向性關系中的客體。他不是單純存在于人的意識之中,也不是單純存在于音響與符號之中,而是在兩者的互相對待之中。
2、在主體間性中尋找音樂美學的基石
從主客間性到主體間性,標志著認識論的一次重要突破,也是人文科學包括美學方法論的一次重要突破。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我們在學術研究中所提供的結論必須是能夠被認定的客觀性的知識。知識與意見的區分,就在于其是主觀性的還是客觀性的。在音樂美學當中,我們經常講趣味無爭辯,但是美卻有其客觀性,對一首樂曲的客觀評價卻有其客觀性。我們無法對一個作品進行任意的評價,所有的評價都建立在作品本身的客觀性基礎之上。也就是說,音樂美學要想成為一門學科,就必須有客觀性來支撐。縱觀整個音樂美學的發展史,我們不難發現,整個研究的歷史進程是由客體中心向主體中心轉移,到主客間性時主體的地位和功能已經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主體的作用變得越來越重要,而客體正在慢慢地隱退。這就使學術的客觀性受到威脅,從而使知識的信念發生動搖。因為按照主客間性的觀念,我們的一切知識都是經過我們的理解產生的,是由我們的理解賦予客體的。我們無法證明我們的評價和理解是正確的,甚至也不能退回到客體性階段。因為主體在人的認識活動中的作用是客觀存在的,即使在客體性階段,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也是包含著主體性,只是當時人沒有認識到而已。當我們認識到這一點時,我們就只能對客觀性進行重新審視,進而發現,我們認識的客觀性并非單純來自事物的客體性,同時還來自主體之間的一種約定和共識。
在藝術的認知過程中所存在的客觀性并不是一種自然純粹的客觀性,而是我們主體間的客觀性,我們人群中的客觀性,或者說是社會的客觀性。事實上,音樂總是同音樂的享用主體連接在一起,一旦離開它的享用主體,音樂的意義就會發生變化。因此,不同的主體間性會賦予同一作品以不同的意義。正因為如此,二十世紀以來,文化人來學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在音樂學忠,產生了音樂人類學。文化人類學已經告訴我們,音樂總是存在于文化之中,離開了孕育他的文化母體,音樂就無法得到深刻的體會和認知,音樂的意義也就無法得到深刻的昭示。音樂的價值和意義是歷史的,存在于其自身的文化環境中的,當我們將音樂脫離它所存在的文化環境或者一直到另外一個文化環境中,音樂的雞雞就有可能被埋沒或扭曲。或者即使這樣的音樂是有意義的,也是另外一種意義。因此,我們在研究音樂的時候,僅僅研究音樂的形態是不夠的。音樂本身的形態雖然看似是最客觀可靠的,然而孤立于歷史之外的,甚至孤立與整首音樂之外的一個滑音、一個波音、乃至一個和弦都是空洞的存在,只有將他們放在特定的音樂情境中和文化母體中,其意義才能彰顯出來。
其實,從主客間性到主體間性,在理論上是一個必然的選擇,也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主客間性中對于主體的重視,本身就包含了對它進行具體化的內在張力,使主體獲得民族性、社會性和具體文化特征,這正是主體間性理論所包含的內容。
四、存在于人與音樂關系中的主體間性
中國文化傾向于將萬物視為主體,因此它看什么都力求觸及它的靈魂,它的內在精神,而不是僅僅滿足于僵死、呆板的形跡。因此,我們在挖掘音樂時,要將音樂背后的底蘊發掘出來,使其獲得靈魂,顯其精神。我們在看樂譜時,不能陷入教條化和客體化的泥淖中,將譜子看死,而要看到譜子背后的生命。
我們對待音樂的態度決定了主體間性在人與音樂作品的關系。對于中國音樂美學而言,我們始終將音樂看成有靈魂的主體;看成有內涵的作品,看成可以不斷生長的生命體。它能夠引起人的心靈的強烈共鳴,并成為我們修身養性的重要功課和抒發情懷的知心朋友。音樂作品的存在,不僅僅屬于作者本人,更屬于所有演奏和欣賞它的人。
五、總結
美是客觀的,但這種客觀性不在于它的物質性,而在于它的社會性。主體間性的出現,樸素的解決了審美判斷和審美經驗中主體性與客觀性之間的矛盾問題。中國的音樂美學在主體間性的理論道路上做了大量的工作,顯示出旺盛的活力和迷人的前景,然而,我們在實踐上開拓理論研究卻顯得不足,也并未對主體間性在音樂美學上做出應有的理論回應。當前最值得我們關注的是,音樂美學如何從抽象的共性理論轉為具體的與文化情境想接通的層面。
參考文獻:
[1]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古代樂論選集[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1.
[2]楊春時.從客體性到主體性到主體間性——西方美學體系的歷史演變[J].煙臺大學學報 2004(4).
[3]何乾三編.西方哲學家、文學家、音樂家論音樂[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83.
[4]于潤陽.現代西方音樂哲學導論[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
(作者簡介:冷雪巖(1969-),女,貴州貴陽人,甘肅省藝術學校教師,主要從事音樂教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