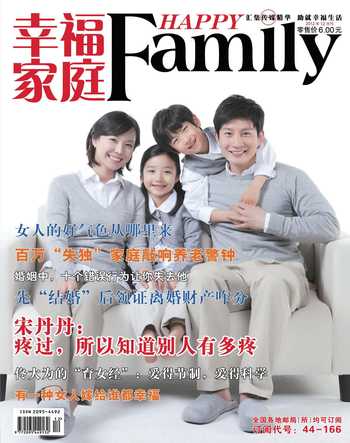希望與勇氣:兩個媽媽的“換肝救子”
付曉英
手術之后
9月18日,肝臟移植手術后第四天,兩個寶寶——團團和哲哲離開重癥監護室,分別跟著自己的媽媽尹春林和羅丹住進802和803病房。
手術挺順利,但是離開監護室以后,團團和哲哲都有點發燒,雖然是手術后的正常反應,醫生和媽媽們還是擔心感染和并發癥。病房每天都要經過臭氧消毒,不能隨意進出,并且要時刻戴口罩。寶寶出重癥監護室那天,在病房里記錄寶寶病情和用藥的白板上,醫生分別寫下了尹春林和羅丹最常說的話——“他既然來都來了,就不給自己留遺憾”以及“費那么大勁把他生下來,我一定要把他弄好”,作為對兩個人的鼓勵。
而尹春林和羅丹看上去依然非常虛弱,面色蒼白,聲音微弱,因為刀口疼痛,走路一直弓著身子。“直起腰來抻得傷口更疼。”尹春林說。但是兩個人精神狀態都還不錯,夸羅丹長得好看的時候,她很高興地笑,手一揮,說:“對,我很美!”經過走廊的護士看見羅丹,叫她一聲“蘿卜頭媽”,羅丹笑著點點頭:“因為我長得比較矮小嘛,叫我什么的都有,隨便叫,不介意。”
與羅丹住過同一間病房的高大姐在北京市福利院工作,今年5月份,因為在醫院看護福利院里患膽道閉鎖癥的孩子而跟羅丹結識,她跑去病房,想探望羅丹,又因為看到病房門口“限制探視”的牌子而最終沒敢進去。在走廊里遇到羅丹的時候,說了沒幾句,高大姐自己就哭了。“羅丹真夠堅強的,才23歲,這么小,自己帶著孩子,挺不容易的,我跟她一起的時候就一直勸她別著急慢慢等,她一直說‘我不能放棄,為了孩子我也不能放棄。真棒!”反倒是羅丹拍拍高大姐,很平靜地安慰她一切都好了,沒問題。
有好心人到醫院送水果,羅丹分一半出來,弓著腰走去尹春林的病房,看到尹春林的丈夫羅開志在走廊窗戶旁邊,就一邊走一邊埋怨他不過去幫忙提水果,笑著大叫“我是病人啊”。
尹春林一直在隔壁病房照看著兒子團團。“寶貝有點帶嬌了,只肯跟媽媽,一走開就哭。”羅開志說。而尹春林的媽媽宋玉瓊說起女兒就止不住地掉眼淚。“我女兒下病床第一句話就說‘我們下來出去走走吧,給別的膽道閉鎖寶寶的媽媽們看看,讓她們像我們這么堅強,也給自己的寶寶捐肝,給寶寶活下來的希望。當時我就哭了,又不敢給她看到,又可憐她又擔心她,看到寶寶活蹦亂跳又為她驕傲。手術后第三天我就扶著她出來在走廊里走,給那些害怕的媽媽看看,我們勇敢不勇敢。她沒有別的選擇,一直堅持給寶寶換肝,很多人說,花那么多錢,怕換不好,她都說‘我不管那么多,哪怕是只過一天正常人的生活,也要給寶寶換肝。”宋玉瓊哭著說。
“換肝救子”
羅丹是湖北人,跟丈夫劉祥在天津打工,尹春林是云南人,嫁到了重慶;羅丹是個小個子,尹春林則身材高挑;兩人都愛說愛笑,也都是膽道閉鎖寶寶的媽媽,這成為她們之間的交集。
羅丹的丈夫劉祥說,哲哲剛滿月不久,就發現他的眼睛一直不褪黃,去醫院檢查后確診為膽道閉鎖,之后一直接受各種治療。哲哲兩個月的時候,在天津一家醫院做了葛西手術。武警總醫院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醫師李威介紹說,患膽道閉鎖的孩子3個月以內做葛西手術效果還不錯,3個月之后基本上沒有效果。做了手術的寶寶有1/3可以撐到成年,還有1/3可以堅持到五六歲左右,那時候再換肝效果會好一些,另外的1/3就是效果不好、在1歲之內還得換肝。“我們寶寶太小了,當時想能不做移植就不移植,等他長大一點有了抵抗力再說,結果葛西手術做完之后就感染了。寶寶5個多月的時候,肝就徹底壞了,只能移植。”劉祥兩只手攤開,放在一起,比畫著說,“你沒看到寶寶肝的樣子,那么小的孩子肝臟就腫到有這么大,都是黑色的,已經完全壞掉了。”
團團的狀況也差不多。“50多天的時候我們發現他有病,去重慶、云南、上海都看過,兩個多月的時候在重慶做了葛西手術,希望可以延長他的生命。剛做完的時候恢復還可以,后來又反反復復發燒,我們也想等寶寶大一點再做,可是他已經開始發低燒了,醫生也建議在寶寶產生腹水之前做,手術后的恢復也好一些。”羅開志告訴記者。
今年5月份,羅丹就帶著哲哲住進了武警總醫院等待合適的肝源,而在尹春林之前,有過另一個母親曾經也想與羅丹互換肝臟,但是因為多種原因最終未能實現。至于與尹春林的相識,羅丹告訴記者:“我一個多月前跟尹春林在網上聊天認識的,都是因為孩子的病癥,從網上搜索相關的資料,看到了膽道閉鎖QQ群,就加進去了。群里的人都是孩子的母親,互相交流病情,也互相安慰。我們都被這個病困擾,等不到別人的肝源,又都想救孩子,聊過之后,發現我跟團團都是B型血,尹春林跟哲哲都是O型血,覺得挺合適的,就突然產生了交換的想法。我們做決定很快,也沒有多少猶豫,決定了就開始準備。”
對于做出換肝決定的過程,兩個人都沒覺得有那么艱難,說起來輕描淡寫,也都愿意用“緣分”來解釋。“那么多QQ群,一個群里也有500人,我們倆碰上了,只能說是緣分。”羅丹說。
雖然羅丹最先提出換肝,但是尹春林在羅丹提出換肝想法時就立即答應了。“羅丹的遭遇跟我的差不多,一個人帶孩子,心里也會憋屈,在網上也一直聊這些。我雖然是O型血,可以給團團換,但是同血型成功率更高,換給哲哲的話也還能再救一個孩子。后來哲哲拖不起了,我們寶貝各方面也不錯,能做就做了,還可以互相鼓勵。”羅丹比較樂觀,她說:“我也想過手術風險,但是不敢想,怕也沒辦法,怕也要上啊。”她笑著,像是要給自己信心和安慰。“但是都過去了,這么多人幫忙,問題也解決了,都挺順利的。”而尹春林則說自己不想那么多:“我知道有一定的風險,但是不能因為有風險就看著寶寶受病痛折磨,我愿意給他換,我從小就挺倔的,不管最后結果如何都不后悔,因為我努力爭取了,而且現在我們都有兩個孩子了。假如一個真出事了,不是還有一個嗎?”
倫理爭議
8月25日,22歲的尹春林也帶著寶寶來到北京。第二天,尹春林也住進了醫院。9月14日,所有的手續準備妥當,4臺手術同時進行。參與主刀的武警總醫院肝移植科主任醫師陳新國介紹說,手術從供體開始,兩個母親同時進去,4臺手術累積進行了48個小時。
而在手術之前,作為國內第一例互換肝移植,這在武警總醫院倫理委員會討論上有過不少倫理爭議。
“互相交換是目前國內親體肝移植的挑戰,2007年衛生部出臺了《人體器官移植條例》,按國家規定,親體肝移植只能限制在直系親屬或者三代以內的旁系親屬,或者夫妻之間,或者有幫扶關系的,比如養父母養子女這種情況,交換不在涵蓋范圍之內。”李威介紹說,“交換器官移植在國外很多國家都存在,比如韓國、英國、美國,國外既然都可以做了,國內為什么不能嘗試一下呢?而且,雖然肝移植交換是國內第一例,但是在2006年《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出臺前,武漢同濟醫院就已經做過腎移植交換。2007年底,類似的親體腎移植交換被廣州一家醫院的倫理委員會以8比1的投票否決,手術沒做成。后來這兩對夫妻去了海南一家醫院,倫理會通過了,手術也很成功,當時也有很大的倫理爭議,但是他們確實不涉及器官買賣,都是自愿交換救人,最后也得到了衛生部的默許,爭議慢慢平息了。我們在做這個手術之前,也咨詢過很多專家的意見,他們有人認為交換也是幫扶關系的一種延伸,而手術的主要負責人沈中陽教授則認為這實際上就是親體,因為兩個媽媽都是為了救自己的孩子,原本是要捐獻自己的肝臟給孩子,但是由于種種原因,互相交換了一下,而且關鍵是不存在買賣關系,他們兩家人都付出了,孩子也都得救了,他們是平等的也是公平的。”
李威介紹說,倫理委員會專家討論時也提到了一些其他問題。“專家一是擔心器官買賣,因為中國現在的器官買賣還是很猖獗的,很多時候會以各種手段進行器官交易,比如說假夫妻、臨時的養子女養父母等等,怎么去判斷呢?這方面的倫理要求非常嚴格,包括母子關系、夫妻關系等,很多方面都做了證明。二是擔心其中的平等性問題,他們兩家是相對平等的,但能不能絕對平等呢?比如說,兩個小孩子恢復得好不好,兩個大人的肝臟質量如何等等,這可能會產生糾紛;再比如,一個人做完了手術,成功了,另一個突然不想捐獻了怎么辦,這些都是要考慮的問題,所以,我們最后決定4臺手術同時進行,在人員安排和時間上盡量一致,盡量避免人為原因造成的不公平。兩個孩子的同一個手術步驟是同一個醫生來做的,只是先后順序不同,比如,把肝臟移植到寶寶體內是最重要的步驟,還有門靜脈、肝靜脈等很重要的血管的吻合,這些都是沈中陽教授親自做的。像我做的是動脈吻合和膽道吻合,這樣的話,兩個孩子雖然在時間上一前一后,但至少是同一個醫生來做,技術水平是一樣的。但是,因為肝臟大小不同,所以進行肝臟游離的時間也不同,手術也很難實現完全同步。”李威說。
對于爭議,陳新國說:“雖然這不能作為常規的操作方式,在中國規定的倫理方面也會有些偏差和爭議,但他們都沒有等待的機會,也沒有其他的辦法了,而且確實不存在器官買賣的問題,材料也符合倫理方面的要求,而且法律往往是相對比較滯后的,目前雖然并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數字,但是成人肝源等待比例都在1比100以上,孩子的就更高了。我們也希望在日后活體肝移植方面做一些探索。”
(摘自《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