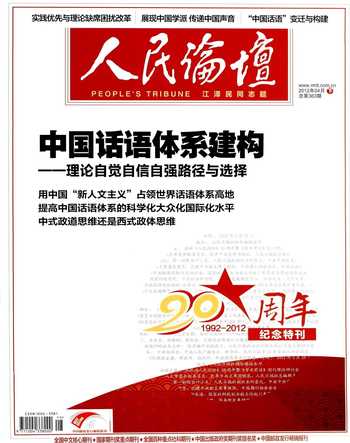學術評價體系建設的國際借鑒
蘇長和
一個國家的知識,往往不在于其產出的量,而在于其是否成“體系”,唯有成體系成建制的知識,才能推廣和擴散;零星散亂、支離破碎的知識,即使量再多,不成體系,那么也很容易被別的知識體系所擊潰、吸納或收編
我國的發展迫切需要有一個客觀友善的國內外輿論環境,好的輿論氛圍的形成,離不開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指引。社會科學在國家意識形態體系建設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些文明連貫的大國,莫不重視自身社會科學話語體系和評價體系的構建。當前,我國意識形態安全受到較大的壓力,與西方知識話語體系的大規模進入是有很大關系的。另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構建的一個重要環節,是構建中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后者確立并能挺立,對聚攏民心,樹立信心,為我國發展道路爭取有利的國內外輿論環境,意義極為重要。
構建中國特色社會科學評價體系,需要把握好政治與學術的關系
有人認為,學術研究應該“去政治”。這種看法對社會科學而言,不一定對。社會科學既有“學術”的屬性,也有“宣傳”的屬性。在現代國家,社會科學很大程度上承擔著國家價值和意識形態體系建構的角色,對大國來講,沒有獨立的與國家價值體系自洽并為國家價值體系論證的社會科學體系,該國的意識形態基礎必定很脆弱。
實際上,真正好的評價體系,是大道無形,不現政治,但是政治和價值的共識卻以隱蔽和無形的方式無處不在,嵌入在評價體系中。諾貝爾經濟學獎講不講政治?當然講!它講的主要是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政治。但它們在評選中不會把它的那套意識形態標準一條條直白地列出來,評價者個個心知肚明,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高度自覺”。
在大部分西方國家,學者與科研機構存在某種程度上的雇傭關系。科研機構在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價值體系上存在高度的共識和自覺,在雇什么人不雇什么人上心里清楚,這個隱蔽的價值門檻等于潛在地將異見學者擋在門外,反過來說,如果你要獲得一個教職,你必須進入其價值體系,按照其話語體系說話。
當然,社會科學研究講政治,絕不是泛政治化。科學合理的評價體系,一定要尊重學術研究的規律,尊重學者的個性創作。社會科學成果,最終是要由歷史來評價,由實踐來評價,由人民來評價。
科學合理的社會科學評價體系,還要兼顧好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既有利于個人活力的激發,也有利于集體團結攻關
我國特色的評價體系中至今仍有集體一等功或二等功之類的獎項,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榮譽制度內容之一。個人和集體是不可分開的,都應該重視,過去重視集體,忽視個人,現在重視個體,忽視集體,都是走極端。前段時間,圍繞屠呦呦獲獎在國內就有個人榮譽與集體榮譽的爭論。其實,筆者已經注意到,現今越來越多的人只愿意做容易使個人獲得功名的研究,但是對有利于國家但卻不容易使自己很快獲得功名的研究,例如基礎數據采集整理,或者非集體攻關則不可有突破的研究,不太重視。在目前的社會科學評價體系中,鮮有對那些默默無聞從事基礎數據材料采集工作的集體給予重視的。我覺得,越是在“各做各”碎片化研究盛行的今天,越應該有鼓勵集體科研和為國家重大利益進行集體攻關研究的評價導向。
科學合理的社會科學評價體系,還要辯證地處理量與質的關系
任何一項制度,都是針對99%的普通人的,1%的天才根本就不需要評價體系,也能做出天才成果。因此,在99%的普通人中間,以量衡量仍然不失評判的標準之一。世界上各個大學,教師職位晉升沒有不參考量的,尤其在很難有客觀標準的社會科學領域。當然,取量并不是鼓勵跑量。關鍵是,一國要有自己各個專業領域一流的標桿性雜志或出版機構,在這些得到專業學者認可的雜志或出版社發表的論著,量多自然是衡量學術成果的重要依據。
科學合理的社會科學評價體系,需要正確對待“中”與“外”的關系
鑒于社會科學的價值功能,我們不能將社會科學的評價體系拱手讓給西方,這與我國的金融體系不能過多倚重西方的評級體系,道理其實是一樣的。但同時,我們必須立足于自己刊物和出版社的質量建設,例如,對那些收取版面費的刊物,主管機構應該加強監管。
在刊物的選擇上,有人主張像《求是》等黨的理論刊物,不是學術雜志,不應該納入到評價指標中。這也是比較極端的看法,不可取。美國有本老牌的《外交事務》雜志,其文章也不“學術”,但其發表的文章經常具有風向標意義,《外交事務》某種意義上是美國的“黨報”,西方學者也樂于榮于在上面發文章。因此,《求是》、《人民日報》等理論版刊登的文章,更理應納入我們社會科學的評價指標中。
從長遠角度看,好的評價體系,一定要學會與國家語言戰略結合起來,鼓勵外國學者(目前主要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用中文寫學術文章,將這些研究成果納入評價范疇。另外,評價體系必須將中國特色與世界眼光結合起來,使自身的研究成果既能夠立足本土,也能夠被域外學生所接受。美國通過留學生培養以及當地教育部門合作等方式,將其教材體系大規模推廣到發展中國家,為其帶來巨大的話語聚合資源。本人接觸到的許多發展中國家學生,這些國家由于缺乏獨立的知識體系,其高等教育尤其是社會科學專業的教材,西方特色的教材占據顯要位置。以本人從事的國際政治研究為例,美國特色的政治學和國際政治學教材,基本是為其霸權及美式自由民主辯護的,設想其他國家一代或兩代的大學生是在閱讀這些教材下成長起來的,其思維不變都難。這是今天全球青年教育面臨的一大問題。我們通過自身評價體系建設,如能形成一整套有中國特色又有世界眼光的教科書系列,將中國人對和平發展、互利共贏、公平正義的理解化進教科書中,告訴給其他國家,則功莫大也!惟有各國在這類問題上形成共識,人類新的歷史才能展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科學合理的社會科學評價體系,必須要有利于中國特色社會科學知識話語“體系”的構建。一個國家的知識,往往不在于其產出的量,而在于其是否成“體系”,唯有成體系成建制的知識,才能推廣和擴散;零星散亂、支離破碎的知識,即使量再多,不成體系,那么也很容易被別的知識體系所擊潰、吸納或收編。社會科學應該包容個性化很強的研究,鼓勵自由探索,但是,作為引導、指導乃至確立主導的社會科學評價體系,一定要有至少一半的權重,致力于鼓勵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創新成果。因此,對那些有利于自身理論體系構建的(例如學科體系、教材體系、概念體系、方法論、元知識研究等)研究,應給予更高的評價權重。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外交學系教授)
責編/劉建美編/石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