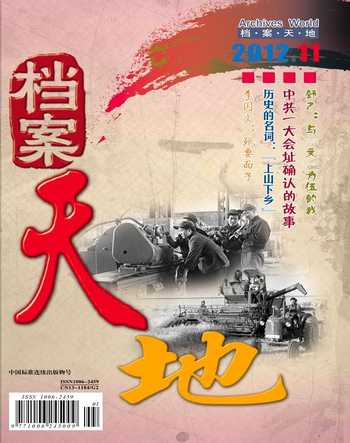荒煤,迷人的心田
林非
名家檔案:
荒煤(1913-1996年),生于上海市。當(dāng)代著名作家、文藝?yán)碚摷摇㈦娪八囆g(shù)家。
(一)接觸荒煤先生
已經(jīng)是將近20年前的往事了,最初見到荒煤的印象,至今飄蕩在腦海中。
當(dāng)時(shí),聽好多同事議論說,原來的文化部副部長陳荒煤同志到文學(xué)研究所來工作了。這大名鼎鼎的作家,我早就讀過他幾十年前撰寫的小說,也早就知道他曾領(lǐng)導(dǎo)過全國的電影工作,而且還因?yàn)殡娪啊读旨忆佔(zhàn)印泛汀对绱憾隆繁怀妨寺殻拔母铩遍_始時(shí),又被投進(jìn)監(jiān)獄,真是嘗盡了人世的磨難。
后來,荒煤先生出現(xiàn)了,他始終是輕輕地說著話,沒有抑揚(yáng)頓挫的聲調(diào),就像悄悄流淌的小溪那樣,覺得他的話里蘊(yùn)藏著無窮的味道,因?yàn)樗磸?fù)闡述著要恪守文學(xué)藝術(shù)的規(guī)律辦事,否則就會產(chǎn)生巨大的災(zāi)難,這種說法深深地吸引著我。我瞧見他翕動的嘴唇在微微地顫抖,兩條眉毛中間豎起的皺紋也在不住地起伏著,從眼眶里還射出一道“悲天憫人”的亮光。我深深地感到他這番話語的分量,而且,也強(qiáng)烈地覺得,有一股親切的力量鼓舞和激勵自己應(yīng)該努力去治學(xué)。
話說從沙汀和荒煤這兩位著名的前輩作家調(diào)來文學(xué)研究所主持工作之后,他們一心撲在公務(wù)中間,不知疲倦地規(guī)劃著許多研究的任務(wù),諄諄地囑咐大家要開創(chuàng)文學(xué)研究的新局面,許多同事都齊心協(xié)力和摩拳擦掌地想大干一番事業(yè),好彌補(bǔ)過去荒廢了的光陰。當(dāng)時(shí),真是充滿了一片百廢待興和欣欣向榮的氣氛。我也被調(diào)到了新成立的魯迅研究室,正夜以繼日地趕寫著計(jì)劃中的研究項(xiàng)目,覺得幾十年都沒有像這樣興奮和歡樂過。
大概是過了將近一年之后,他有一回在走廊碰到我,約我去他的辦公室談話。當(dāng)我靜靜地坐在他對面,默默地看著他時(shí),他也默默地望著我。從窗外刮進(jìn)來一陣溫馨的微風(fēng),吹動了他桌上的紙片,他這才像是從夢中驚醒過來,低聲細(xì)語地問我:“為了明年的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jì)念,你們考慮過沒有還該做一些什么工作?”
“除了已經(jīng)上報(bào)的三部學(xué)術(shù)章著之外,還發(fā)動大家多寫一些論文,針對當(dāng)前存在的問題發(fā)表意見,著眼于提高魯迅研究的學(xué)術(shù)水準(zhǔn),這樣來發(fā)揮魯迅研究室的作用,大家都有信心去完成。”我也像他這樣慢條斯理地說著。
“你們沒有想到過其他的工作嗎?”他默默地望著我,然后就和藹地笑了。
我無法回答他突然的詢問,搖了搖頭說:“還沒有。”
“應(yīng)該趕寫一部言簡意賅的《魯迅傳》,讓更多的人準(zhǔn)確地了解魯迅,這既是最有意義的紀(jì)念,也是撥亂反正的重要工作啊!”
這個主意實(shí)在太好了,我在好多年前就想到過撰寫《魯迅傳》的事情,還認(rèn)認(rèn)真真地鉆研過羅曼·羅蘭的《貝多芬傳》,揮舞著紅筆,在自己的這本書上圈圈點(diǎn)點(diǎn),想從里面學(xué)到一點(diǎn)兒寫作的竅門,怎么這一回制訂研究計(jì)劃時(shí)卻忘記了呢?并不是忘記了,卻感到這是一樁相當(dāng)艱巨的攻堅(jiān)戰(zhàn),得放在以后再考慮去進(jìn)行,于是,有點(diǎn)兒猶豫地說道:“怕不容易寫好。”
荒煤拉開辦公室的抽屜,拿出幾本書來,默默地瞧著我說:“我找來了你寫的文章,認(rèn)真地看了看,覺得你應(yīng)該能寫好它,時(shí)間很緊了,回去研究一下,幾個同志合作撰寫也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就決定下來。”
除開荒煤之外,從來還沒有哪一位領(lǐng)導(dǎo)在閱讀我的文章后,再布置和指點(diǎn)我去從事研究工作。我的心激動得跳蕩起來,多么想冒出一句感謝的話兒。
(二)荒煤先生的心胸
從1981年夏天開始,紀(jì)念魯迅誕辰100周年的準(zhǔn)備工作,就一天天地緊張起來。荒煤是這個紀(jì)念委員會的秘書長,工作的頭緒相當(dāng)紛繁,首先是籌劃有上萬人參加的紀(jì)念大會,全國的著名作家都會前來北京,聆聽當(dāng)時(shí)的總書記胡耀邦講演,真是事關(guān)重大呀。對于我參加的學(xué)術(shù)組這一攤事務(wù),他也經(jīng)常來過問和指導(dǎo),想開好一個有全國上百位著名學(xué)者參加的研討會,也實(shí)在是一件談何容易的事情。就在人們紛紛前來報(bào)到,會議即將開幕的前夕,他終于勞累得病倒了,我前往首都醫(yī)院向他匯報(bào)工作時(shí),瞧見有幾位電影界和文學(xué)界的朋友們正圍坐在床邊,傾聽他說話。
他跟我握了握手,依舊滔滔不絕地繼續(xù)往下說去,發(fā)表著對電影《傷逝》和話劇《阿Q正傳》的看法。我瞧著他消瘦的面頰和額頭上深深的皺紋,瞧著他異常憔悴的臉色,驚訝于他躺在病房里,怎么還能這樣不顧一切地工作?面對著這位充滿了獻(xiàn)身精神的“殉道者”,我心里翻騰著一種痛苦而又崇敬的感情,暗暗地發(fā)誓,畢生都要努力地工作,才不會辜負(fù)他的言傳身教。
當(dāng)我正想得出神時(shí),荒煤輕輕地招呼我走到他床前,詢問著賓館里對于食宿方面的生活安排,是不是都作得很妥善?囑咐我務(wù)必轉(zhuǎn)告全體工作人員,一定要尊敬和團(tuán)結(jié)所有的作家與學(xué)者,說是只有分外地尊重和發(fā)揮知識的作用,國家才會有前進(jìn)的希望。從這件細(xì)小的工作中,我也強(qiáng)烈地領(lǐng)會到了,他寬厚和廣博的胸懷。
不久以后,荒煤又奉命回到國家文化部去工作了,回憶著往昔幾年令人神往的歲月,真感到悵然若失。我跟他并無更多的交往,還由于在我們之間年齡和地位的懸殊,幾乎從來沒有過私人之間的談心,然而,他燃燒和發(fā)光的生命,他出自內(nèi)心地關(guān)切著所有人們的情懷,始終使我感到無比的親切。我常常想去看望他,卻又知道他的工作十分忙碌,因?yàn)椋P(guān)心著整個中國的文學(xué)事業(yè),要閱讀數(shù)不清的作品,然后,給這些作家們詳盡地提出自己的意見來,怎么能平白無故地去打擾他呢?
有一回,我下了決心前往他家里,準(zhǔn)備坐一會兒就走。在那間朝向馬路的屋子里,坐著好幾位年輕的作者,正說得十分熱鬧,有個年輕人氣憤地詛咒著,人人憎恨的貪官污吏,說是希望他們“早死”。
“應(yīng)該大家共同來努力,有效地采取道德裁判,有效地進(jìn)行法律的懲處,僅僅是停留在煩惱和憤懣中間,那就遠(yuǎn)遠(yuǎn)地不夠了。“荒煤依舊是輕輕地訴說著自己的看法。
我真想提出許許多多的問題向荒煤先生請教,正好在不久之后,自己的一本“游記選”將要出版,于是,又拿起一疊剪報(bào)去找他了。荒煤仔細(xì)地翻閱著剪報(bào),搖著頭笑道:“我是個從來不寫游記的俗人,能發(fā)表什么意見呢?”
“你不管發(fā)表什么意見,都會對我有啟發(fā)的。”我誠心誠意地笑了起來。
他瞧著我笑得好歡暢,也嘿嘿地笑了,說:“這不是逼上梁山嗎?”
沒有過幾天,在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后,荒煤突然找到我家里來了,氣喘吁吁地坐在椅子上,舉起手來輕輕拍打我兒子的肩膀,高高興興地跟肖鳳說道:“孩子長得這么英俊,真是青出于藍(lán)啊!”接著,又關(guān)心地詢問她正在撰寫什么傳記作品。閑談了一番之后,他才從書包里拿出一疊剪報(bào)來,將夾在里面的“序言”遞給了我。
在匆匆告別時(shí),他還回過頭來打量著這間狹小的屋子,眺望著書柜頂上堆積如山的典籍,皺著眉頭像是自言自語地說道:“書太多了,太擁擠了!”
我瞧著他憂郁的眼光,在他凝重的張望中,一股激流撞擊著我的胸膛,深深地感覺到,他總是關(guān)懷別人的一切。我一直送他上了車才回到家里,趕緊翻開他的序言閱讀起來。他對于“游記”的能夠開闊視野、溝通心靈和提高境界,闡述得是那么的精辟。這篇序言在《光明日報(bào)》上發(fā)表之后,我聽到好多朋友說起,讀完之后,受到很多的啟發(fā)。
如果永遠(yuǎn)能夠聽他說話,永遠(yuǎn)能夠閱讀他的文章,永遠(yuǎn)能夠受到他的啟迪,這是多么的幸福啊!那次,在山東東營考察。清晨,當(dāng)?shù)氐氖形瘯洈v扶著荒煤乘上了輪船,大家直往黃河入海的地方駛?cè)ァ4系紫率倾殂榱魈实牟擁斏嫌志砥痍囮嚨目耧L(fēng),我瞧著荒煤直挺挺地站立在欄桿旁邊,揮著手臂跟人們說話,眼睛里閃爍著歡樂的光芒,多么的神采奕奕,再也瞧不見絲毫憂郁的神色了,我深信,他肯定會跟人們在一起迎接21世紀(jì)的來臨。
哪里知道災(zāi)禍這么迅捷地降臨。雖說是“人生七十古來稀”,何況還遠(yuǎn)遠(yuǎn)地超越了這個期限,本來可以昂起頭顱,用最虔誠的敬禮為他送行,卻總是抑制不住眼眶里的淚水,抑制不住悲哀和痛苦的呻吟,因?yàn)椋麑?shí)在太善良和高尚了,實(shí)在舍不得他離去;不過他雖說是離開了大家,卻永遠(yuǎn)在我們心里矗立起一座高大的紀(jì)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