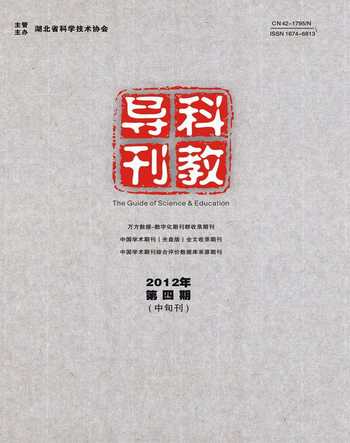“副詞+名詞”結構的認知研究
曾幫珍 李瑛
0 引言
關于“副詞+名詞”(如:很女人)的結構,已經有不少的學者對其進行研究。邢福義認為該結構的使用與句式結構和文化背景有關,并且討論了該結構可用不可用的問題。桂詩春則認為該結構的使用僅僅是一種語用策略,不符合漢語習慣的用法,甚至認為這類用法不能納入喬姆斯基的語言能力/語言運用模式,都認為是不規范的用法。
1 轉喻
認知語言學認為:轉喻不僅僅是語言現象,而是人們一般的思維和行為方式。我們的思維和行為所依賴的概念系統都具有轉喻的性質。Lakoff &Johnson(1980)認為隱喻與轉喻不僅僅是必要的修辭手段。更是人類的重要思維方式,它們普遍存在于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影響著我們的思想和行為。我們賴于思維和行動的一般概念系統,概念轉喻是在同一個理想化認知模型中用一個范疇去激活另一個范疇的認知過程。
2 副詞+名詞結構的認知分析
2.1 “副詞+名詞”結構的搭配原則
副名搭配會受到一些原則的制約,例如,“很青蛙”、“很板凳”等幾乎是不會出現。下面我們就對名詞的凸顯度、具體性、范疇層次性等因素對副名搭配產生的影響進行討論。
2.1.1 凸顯度
特征凸顯度高的名詞在進入副名結構搭配中優先于特征凸顯度低的名詞。副名結構中名詞具有的重要特征就是有較高的特征凸顯度。副名結構是概念轉喻的一種方式,涉及的范疇轉指范疇相關屬性,例如,to bus to school 涉及“工具到動作”(INSTRUMENT FOR ACTION)的概念轉喻,to go to school這個習慣性行為不如這個行為的方式by bus顯著,因此行為的方式可轉指行為本身。在日常生活中,同是名詞, “很牛”、“很狼”的使用頻率為什么會相對比“很魚”、“很青蛙”更高呢,原因在于名詞特征的凸顯度不同。因為“牛”、“狼”的特征比“魚”、“青蛙”的特征更明顯,所以“很”和這些名詞搭配時使用頻率就會比較高。
2.1.2 具體性
抽象名詞(如“很古代”“很風度”)表示人或物的指稱意義相對最弱。表示性質的內涵意義相對最強。它不指向具體個體,而是指向一個類或集合,如張伯江、方梅(1996)指出“抽象名詞不是典型的名詞,帶有明顯的性質意義。”如:“他很哲理的想著”。哲理有意味深長,發人深省的內涵,雖然不能用具體的言語表達,但是人們心理都是能理解的,有了這樣的內涵,副詞與名詞的結合就更自然,語義內容也更充實。
具體名詞(“很鄉村”、“很淑女”)表示可見可觸摸的具體實體,具有較強的空間意義,進入副名結構的能力較抽象名詞弱。如果是與人們日常關系密切的具體名詞,就更容易進入副詞+名詞結構。如:“你的作品太泡沫”。“泡沫”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事物,在這樣的表達中,人們就很自然的會產生相關的聯想。
專有名詞 “很雷鋒”所指的是唯一的個體,具有最豐富的內涵。專有名詞一般是通過 “提高知名度”來獲得類似于抽象名詞的特征。如說到雷鋒,人們就會想起助人為樂的品質;在專有名詞的特征只有在被人所熟知后,進入副詞+名詞的結構就很容易了。
2.1.3 范疇層次性
副名結構涉及名詞范疇層次的選擇問題。范疇具有層次性,一般基本層次范疇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使用最多的,也最被人們所熟悉。能與副詞搭配的名詞經常是基本層次范疇的名詞, 例如, 我們會說“很男人”、“很女人”,但幾乎不說“很人”。這是因為男人、女人等是基本層次范疇的名詞,且具有具體的范疇屬性特征。
2.2 “副詞+名詞”結構的認知理據
從語用角度“副詞+名詞”結構這樣的表達可取語用效果來滿足交際需求,但是在語法層面上就造成了違規現象, 這種違規的言語的怎樣被人們所接受并廣泛使用的呢?
認知語言學認為“副詞+名詞”結構的認知理解是借助于概念轉喻(conceptual metonymy)來實現的。(沈家煊,1999)轉喻概念(如部分代替整體)更是我們進行思維、活動和談話的方式之一。轉喻思維能力是人們在認識客觀世界時與現實世界互動而逐步形成的潛在意識和認知能力。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思想也需要更新,觀念也要變化。語言作為一種思想和表達方式,就需要我們依賴于已有的知識和概念來認識和表達新思想、新概念。根據具體語境,可以在日常交際中通過轉喻,來表達無數的新概念、新思想以滿足交際的需要。副名結構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比如,“很男人”、“特貴族”、“非常家庭”中“男人”、“貴族”、“家庭”就是轉喻用法,是通過具體事物映射出這些具體事物的典型特征。所以,副名結構的認知理解是概念轉喻的結果。
3 結語
“副詞+名詞”結構這種看似不符合語法規則的表達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反映了認知系統和語言系統不斷創新的過程,同時豐富了語言表達,有待我們進一步研究和探索。
參考文獻
[1]Lakoff, G & M. Johnson.1980. Metaphor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Lakoff, G.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3]懂成如.轉喻的認知闡釋.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4(3).
[4]桂詩春.從“這個地方很郊區”談起.語言文字應用,1995(3):24-28.
[5]沈家煊.轉指和轉喻.當代語言學,1997(1).
[6]胡學文.現代漢語“程度副詞+名詞”結構的認知理據、句法操作及限制條件.山東教學,2005(2).
[7]邢福義.關于副詞修飾名詞[J].中國語文,1962(5).
[8]張伯江,方梅.漢語功能語法研究.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