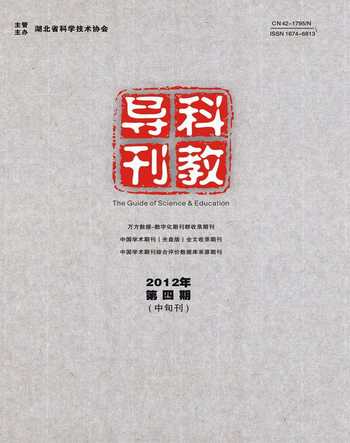文王之“德”內涵再探
楊洪娥
西周“文武之政”被視為后世政治制度的楷模。周文王作為開關明君,地位十分重要。傳統論述中,文王之“德”最為閃耀,一直是周人遵奉的政治規范。對此,文獻資料記載頗多,如《詩經·維天之命》:“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詩經·清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鄭箋》釋“秉文之德”為“執行文王之德”。①《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等。
文王之“德”的內涵,以往多從“德”字本義解釋,為道德修養、道德政治教化。劉寶楠《論語正義》:“文德謂文治之德,所以別征伐為武事也。”②楊伯峻《論語譯注》將“文德”釋為“仁義禮樂的政教”。③這種觀點強調文王以德行服人心、得天下。還有觀點認為,“德”包含了武力征伐在內的政治方略。④本文認為以上兩種觀點都有待完善。
1 由“德”之本義看
甲骨文學者認為,“德”早在殷代就已經出現。⑤并試圖從甲骨文中追查“德”字含義。在春秋時,德字使用廣泛。例如:
天為剛德,猶不于時,況在人乎。《左傳·文公五年》
夷德無厭。《左傳·文公四年》
狄,豺狼之得也。《國語·周語中》
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國語·魯語下》
“夷德”、“豺狼之德”等,顯然并非專指好的行事方式。加以修飾來表達好壞,如“明德”、“懿德”、“兇德”、“昏德”等。在使用范圍上,從“天為剛德”、“豺狼之德”、“祖識地德”等知,“德”可用于人及天地萬物。文王之“德”指“明德”、“懿德”,即指個人品德修養卓越。
首先,“明德”即修養品德,使個人有所“得”。在周人看來,文王因“得天命”而得天下,天命之得又源于其“德”。古人提倡“明德”,先秦文獻多有記載,如“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荀子·勸學》)、“德也者,得于身人”(《禮記·鄉飲酒義》)。許慎《說文解字》中有“惪”字,不少學者認為這就是后來的“德”字。⑥《說文》解釋:“惪,外德于人,內得于己也。從直從心。”劉熙《釋名》云:“德,得也,得事宜也。”孔穎達《尚書正義》亦云:“德者,得也,自得于心。”⑦毛詩正義云:“德者,得也,自得于身,人行之總名。”⑧由此可見,“德”有“得”之意,于自身有所得。
其次,“德”還包含了“施惠于人”。《左傳》有記載“德以施惠”。“施惠于人”是文王具體的行為方式,其結果是“得天命”。《尚書·無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穿著平民的衣服,從事耕種的勞役。從早到晚忙得無暇吃飯,施惠于民,以求萬民和諧。
2 由周公“德治”思想看
早在帝王盤庚時,就提出“施實德于民”。到周代,文王之德排首位。《毛詩序》記《皇矣》主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⑨周公提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推行“德治”主張。他認為,皇天輔佐謹奉道德以保有其民的人,要永固統治,為政者必須“明德”、“保民”、“勤政”、“尚賢”、“慎罰”。
周公“德治”思想是繼承文王思想而來,最初在文王行為和思想中已有所體現。古文獻資料對文王恪守自身修養、勤政愛民、禮賢下士都有記載,如《國語·楚語上》轉引《周書》之語“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唯政是恭。”《史記·周本紀》也記載“(文王)……篤仁,敬老,慈少。禮賢下士,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文王以“不暇食”的勤政精神保民愛民,得到了四方擁戴。當時有諸多謀臣輔士,如太顛、閎夭、散宜生等人,都為極大地輔助了文王的傾商事業。這是文王的為政方式,也是他以“德”行政的體現。
3 從文王的政治功績來看
文王傾盡一生精力為翦商做好準備。從“小邦周”發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西土大國,并非單純靠個人德行感化、道德政治教化,也經歷了大量攻伐戰爭。周人文治上擴大同盟力量、武功上征伐擴張。文王的文治武功,彰顯出其政治謀略之“德”。
文治上,首先聯絡周邊方國、建立方國聯盟。周初實力弱小,文王修德積善、禮賢下士,吸引方國和輔士歸附;解決虞芮之爭,成功地爭取到更多歸附者。《詩·大雅·緜》:“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其次,與商通婚,祭奠商先王。《詩經·大明》記載文王娶莘國女。《周易》中也記載商君嫁女于西周。近年在陜西岐山周原發現的甲骨文,有文王祭祀商先王的記載。這些行為是商周實力消長和矛盾對立的體現。自身實力尚弱,文王表面尊奉商,實為自身壯大爭取時間。
武功上,《史記·周本紀》記載了文王一連串軍事行動:“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自岐下而徙都豐。”文王伐邘,戰略意義重大。李學勤先生說:“是周商勢力對比轉換的標志……文王伐此地,實即直叩天邑商的門戶。因此,武王伐商,中途已無任何阻礙,可以長驅而至商郊。”⑩文王遷都豐邑后,成為足以對抗殷商的西土大國,完全奠定了翦商基礎。
現在學術界有些觀點質疑《史記》記載的可靠性;以文王不恪守君臣之道,質疑文王是否為紂臣。通過本文論述,這個問題應該得以解決了。文王接納叛紂之國,出自其政治謀略的考慮;商紂暴虐,事紂是傾商的策略,與恪守君臣之道并不矛盾。
“德”本身側重個人道德修養;同時,“德”又是政治的根本保障。因此,本文認為文王之“德”,最初不僅包含道德修養、道德的政治教化,也包含“明德慎罰”、“勤政保民”等行政思想,還包括武力征伐商紂的政治謀略。到周公時商紂已滅,“德”之內涵也隨之發生了變化,剩下了前兩方面內容。周公進一步將之系統化,并發揚光大,對后世影響深遠。
注釋
①毛詩正義.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583.
②諸子集成本·論語正義.上海書店,1986:352.
③楊伯峻.論語譯注.中華書局,1980:172-173.
④姚小鷗,鄭麗娟.《大雅·皇矣》與“文王之德”考辨.中州學刊,2007(2).
⑤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290.
⑥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23.
⑦尚書正義·泰誓.“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疏.
⑧毛詩正義·關雎.“關雎,后妃之德也”疏.
⑨毛詩正義.阮刻十三經注疏本.中華書局,1980:519.
⑩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科學出版社,195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