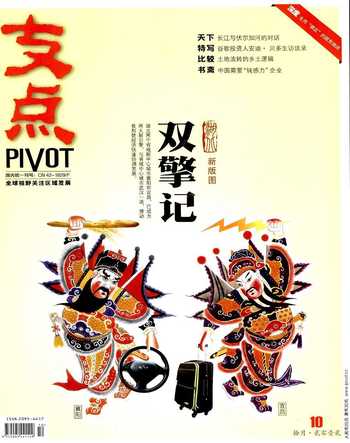黔中灣塘村:生存“禁區”的脫貧挑戰
楊萍 劉真真


編者按
灣塘村,是位于貴州省安順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縣(下稱紫云縣)宗地鄉東南部的一座苗寨,距紫云縣城45公里。
在這個2300多人的村寨里,98%以上是苗族,15個村民聚居點散落在重重山坳間。這里的人們世世代代生活在山窩窩里。
這里被看作人類生存的禁區。實施“坡改梯”以前,80%以上的山地不能用牛耕種。加上不通公路,不通電,缺煤,柴草是唯一的燃料,生存條件極為惡劣
8月中旬,《支點》雜志社同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組成的聯合調研隊,來到這個偏遠的村寨駐扎走訪,探尋大山深處的貧困與希冀。
“丟塊石頭都打不到一個破瓦罐”
灣塘村所在的紫云縣,地處黔中山區麻山腹地,是國家級貧困縣。惡劣的自然條件,是其貧困的重要原因。
這里是喀斯特地貌典型區,縱橫交錯的山脈間,裸露的巖石如被神斧劈過一般,呈現出光滑平整的切面。山上土薄根淺,水土流失嚴重,植被極易遭到破壞。部分土壤貧瘠,是滇桂黔石漠化最嚴重的地區之一。山地面積大,地勢崎嶇,交通不便,雖然很多縣都通了公路,卻是晴通雨阻。
這里曾與世隔絕。若干年前,當第一批到訪的調研干部翻山越嶺踏足村寨時,都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條件太差了!嚴重缺水,沒有耕地,人們只在山坡上種點玉米果腹。親戚之間相互通婚,生出的孩子大多智力有問題。
“丟塊石頭都打不到一個破瓦罐”,當地人用這句話來形容苗寨人曾經的貧困。
當地政府認為,像這樣不適合人居的地方應當移民。近年來,政府對貧困地區實施“生態移民”,2011年安順市移民人數達2000人,移民大多集中在紫云、普定、關禮、鎮寧等重點貧困縣。
現在,紫云縣好幾個鄉鎮的村民,都是從深山移民出來的。盡管如此,貧困依然困擾著這里的人們。
紫云縣被列為限制性開發縣,缺乏工業支撐,財政收入主要依靠農業。由于交通不便,基礎設施落后,加上農民知識水平不高,使得該縣至今是貧困面最廣、貧困程度最深的地區。
如今,大部分的青壯年去了城里打工,現在的灣塘村,是一個由留守小孩、老人和婦女組成的村寨。老人們依然習慣穿著上個世紀的藍布衫、黑褲子,踩著崎嶇的山路,到山坡上收掰玉米。
鄉鎮是這里唯一的交易中心。每個星期,附近村寨的人,或者騎摩托車,或者幾個人擠一輛三輪車,陸續到鄉里去趕集。村民們把自己養的豬、釀的酒、編的籮筐拿去賣,再順便添置一些生活用品。而這二十分鐘的車程,基本上算是灣塘村留守村民可到達的最遠距離,也是他們與市場經濟最近的接觸。
改造不起的吊腳樓
韋十妹是灣塘村竹林組村民,今年48歲。她穿著不合時季沾滿污漬的紅色秋衣,記者到訪時,她正在自家屋后彎腰曬蘿卜種子。
苗寨的房屋大多依山而建,韋十妹家的吊腳樓建在一個石頭坡上,因年久失修,竹編的圍墻已日漸稀疏,很難再遮擋風雨。陽光透過墻上大大小小的窟窿,給昏暗的屋子帶來些許亮光。
家里,沒有洗衣機、電冰箱,沒有熱水器,甚至連自來水管都沒有。唯一跟現代化沾邊的是電視和一臺粉碎機。在寨子里,每家都用粉碎機打苞谷來喂豬。
屋子另一側,鐵皮水桶、落滿灰塵的電飯煲,暖瓶等,散落一地。最里面的一張床上,被子已洗得看不出顏色。
韋十妹給記者搬來個小板凳,大家圍著火塘聊起來。剛坐下,襲來一股豬糞味兒,隨即傳來了豬慵懶的叫聲。原來,在屋子的另一邊,地面是用木板搭建的,透過木板縫隙,下面的豬圈清晰可見。
由于沒有自來水,每天早起,韋十妹先去附近的井里挑水,然后打豬草喂豬。早飯是從來不吃的,生病了也從不去醫院。
“錢太少了,總是不夠用。”她喃喃地說著。
這個吊腳樓實在太舊了,下雨天總是漏雨,為了攢錢建新房,韋十妹和丈夫以及他最小的兒子,都去了城里打工。
在灣塘村,對大多數村民來說,建新房是頭等大事。
隨著政府扶貧資金的陸續投入,這幾年寨子里通了電,還修了3.2公里的公路,方便了村民到鄉上去趕集。條件好一些的人家,積極響應舊房改造的號召,蓋起了兩層小樓,用上了自來水,但破舊的吊腳樓、每天去挑水的人們仍然隨處可見。
為鼓勵舊房改造,政府制定了資金補貼措施。據2011年政策標準,按照貧困程度的高低,農民建房分別能拿到2萬元、1.5萬元、1萬元、5500元的建房補貼。
按理說,最貧困的農民應當拿到最高數額2萬元的補貼,然而,記者在調研時發現,補貼金的發放并未完全達到政府的初衷。當地一家重度貧困戶,去年只拿到最低標準5500元的補貼。
原因在于,當地一家舊房改造約需5萬元,能夠自己拿出3萬元的農戶方能獲得政府給予的2萬元補貼。實際上,由于重度貧困戶根本拿不出3萬元錢,而能夠申請2萬元補貼的往往是較為富裕的農戶,因此,重度貧困戶根本無法獲得最高額補貼,只能拿到最低級別(5500元)的補貼。
于是,這個看似合理的補貼政策造成了眼前的悖景:村里條件相對較好的家庭,住進了鋼筋混凝土的新房;但村里出不起補貼“配套”的家庭,如韋十妹一家,仍不得不住在破舊的吊腳樓里,建新房一直是他們當前最迫切的愿望。
漂泊的青春
最早出去打工的村民,是在城郊的蔬菜種植基地干活。此后,村里人外出打工,大都是做這一類的工作,韋十妹和他的丈夫同樣如此,起早貪黑割菜拔草。雖然出外打工能帶來一些收入的增加,但城市并不屬于他們。
楊華祥今年25歲。從15歲到25歲,他人生中最年輕的時光都是在外打工中度過的。十年里,楊華祥已輾轉奔波于廣東、浙江、北京、天津、武漢等十幾個地方。“如果聽到同鄉說哪個地方工資高,我們就換到那里。”
由于缺少基本技能,教育水平低,多年來他只是在私人老板蔬菜種植基地里務工,從早上7點開始工作,到了中午,十來個人圍坐在一起扒口飯,一直忙到天黑。
“剛出去的時候每天十幾塊,現在好點了,一天能掙幾十塊錢。”楊華祥說。
此間,他結婚生子。老婆是同村大他一歲的韋吳妹。婚后不久,兩人就一起外出打工。每天種菜、拔草、收割,住十人間的通鋪,一年到頭,除了生病請假外,沒有一天休息。
現在,兩人的工資每個月加起來有2000多塊錢。兩口子開銷極少,最大的開銷花在孩子身上。
他們三歲的兒子,是在北京打工時降臨世間的。分娩那天,因沒錢去醫院,就臨時請一位年長的婦女來幫忙。在那個只有一襲布簾遮擋的十人間的通鋪上,一個小生命誕生了。楊華祥親手幫孩子剪了臍帶。
與城里女人不同,從懷孕、分娩到坐月子,韋吳妹都是自己照顧自己,生完孩子僅一個月,就開始上班了。“不干活就沒有收入,我們倆每個月賺2000多塊,給孩子買零食看病等都要花去1000多。”她說。
在外多年,楊華祥夫婦的圈子僅限于同鄉之間的交流,他們很少跟城里人講話,更沒想過要留在城里,在他們心里,唯一的想法是等賺夠錢后回到寨子里建房子。
今年,楊華祥帶著賺來的5萬元錢回到了家鄉,加上從親戚那借的3萬多元,又從銀行貸款3萬元,他們的新房終于動工了。
村里的合作社
在紫云縣的農村,年輕人幾乎全都外出務工,剩下年邁的老人在家務農。老年人體力有限,加上懂農業知識的人很少,大多采取廣種薄收的方式進行農業生產,一些農田不得不撂荒。
最常見的是,外出務工者將土地轉給親戚耕種,楊華祥家的地給了幺叔耕種,韋十妹家的給了弟弟耕種,耕種者每年會給點糧食作為報酬。
為了避免土地荒蕪,政府免費給農戶發放核桃苗或花椒苗,成活一株還有獎勵。此外,村里也會組織人員,幫長年在外打工的家庭種植經濟作物,種一株可得3毛錢勞務費。
這一措施卻收效甚微。村民羅賢榮家去年種了1000棵核桃樹,僅存活250棵。村主任楊正云說:“成活率低主要是缺少管理,政府給予產業引導,但具體管理還是要靠農戶自己。”
很多家庭只有老人和孩子,根本無力打理。比如花椒苗種下去,要經過四到五年才有收成,有的村民怕有風險不愿意種,更擔心種了賣不出去。
“有的村民為了拿到更多的勞務費,就會快種多種,甚至為了搶速度,把幾株苗直接種在一起,現在還沒有找到好的解決辦法。”楊正云說。
我們了解到,安順市扶貧辦對此項目會定期驗收,為了通過上級檢查驗收,在實施過程中難免會出現“搶進度,追數量”等現象,從而造成產業化效率低下,有限耕地也未能得到充分利用。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政府倡議外出打工或者不愿意管理土地的農戶,可以選擇將土地流轉給合作社或協會,之后再進行利益分配,即“合作社模式”。
當前,這一模式是紫云縣探索土地流轉的新嘗試,具體方式為:鼓勵農民將土地流轉給合作社(合作社的性質是有法人代表的企業),由合作社統一耕種,周邊的農民到合作社來打工。
在紫云縣,土地流轉規模最大的合作社是平壩縣天龍鎮鼎興種植農民專業合作社(以下稱鼎興合作社),該合作社理事長肖鼎介紹,他們在安順市幾個縣內共有2萬多畝蔬菜,在武漢、成都、重慶、昆明、江浙及兩廣一帶,有成熟的銷售渠道,每天銷售蔬菜20多萬斤。今年,該社在紫云縣以每畝500元的租金流轉了1000畝土地,共投資400多萬元,吸引了不少村民前來打工。
在紫云縣火花鄉,我們看到,上千畝流轉的土地已經種植了大蔥、辣椒、西紅柿等無公害蔬菜,一些地里還搭起了大棚。
由于資金匱乏家底薄,農戶抗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的能力普遍很弱,當地政府認為,相比傳統“散戶”生產模式,合作社模式一頭連企業,一頭接農戶,既實現了土地規模化生產,又降低了農戶風險,提高了家庭平均收入。
而對于鼎興合作社的合伙人王肖猛來說,其更青睞另一種模式:合作社不用租土地自己耕種,而是給農民下訂單,如此一來,就能將合作社自身的市場風險降到最低。
小額信貸創新
為了推廣合作社模式,便于更多的企業到紫云縣投資,安順市及紫云縣扶貧辦對當地金融部門推出了新措施——貸款貼息。
紫云縣扶貧辦主任張嚴介紹,2010年以來,當地扶貧資金全部投入產業扶貧,目前縣里已經有了核桃、油茶、冰脆李、蔬菜等項目。
為了吸引企業投資和鼓勵農民創業,紫云縣農業銀行和農村信用聯合社(以下稱農信社)等金融機構開展了小額信貸活動。凡是為了發展產業在農行和農信社貸款,縣扶貧辦將會對這兩家金融機構實施貸款貼息,其中,農戶貸款貼息5%,省級龍頭企業貸款貼息3‰
農信社辦公室主任肖剛明白,此舉是為了提高金融機構小額信貸的積極性。都說銀行“嫌貧愛富”,只愿意貸款給大企業,不愿意給小微企業和農戶貸款,最主要的原因是風險不可控,調查成本太高。然而,肖剛告訴我們:“農戶在農信社貸款,不需要任何抵押和擔保。”
不需要任何抵押和擔保,那風險如何控制呢?
原來肖剛所在的農信社共有171名員工,其中信貸員占了一半。他們將龐大的信貸員隊伍投放在農村,給每個村的農戶部建立了信用檔案,根據農戶資產,信用記錄,掌握的技能及款項用途等因素,進行評級授信,并實時臨控貸款使用情況。通過對農戶評級授信,既簡化了貸款手續,解決了農民貸款難的問題,又加大了資金運用力度,提高了信貸資金的安全系數。
羅協榮去年從農信社申請到3萬元貸款,湊夠了11萬元,在宗地鄉買了一塊地,合計100平方米左右,打算以后給兒子建房子用。5月30日申請當天,他就拿到了款項,年息8%,需要三年之內還清。貸款程序很簡單,標準只有一個,個人信用評級。他的信用評級為“優秀”。
今年,農信社再次提高了農戶授信限額,農戶信用貸款從原來的5萬元提高到10萬元,對信譽好,有經濟實力,從事特色產業和返鄉創業的農民,最高信用貸款可提高到50萬元,而不需要任何資產作抵押。
對于大部分涉農金融機構來說,農戶抗風險能力低是很棘手的問題,一旦遭遇天災人禍,金融機構便容易陷入不良貸款的泥沼。
村里的能人
農信社靈活簡便的貸款方式,很快吸引了大批農戶,但同時也增加了自身的資金壓力;另一方面,國有商業銀行網點的撤并和貸款上收,投向轉型,對縣域經濟發展信貸投入不足。因此,農信社有限資金亦難以滿足快速增長的市場需求。
無論怎樣,農村金融機構的信貸措施,還是令一大批農戶嘗到了甜頭,灣塘村的楊順就是受益人之一。
42歲的楊順,是個皮膚黝黑、話語不多的精壯漢子,被稱為村里的能人。
楊順今年首次嘗試種植煙葉,他向宗地鄉農信社貸款2萬元,種了20畝煙葉。煙苗需要自己購買,一畝煙苗要花費30元,可產200斤煙葉。
一個陽光明媚的午后,村里的女人們在烤煙房前面的空地上編煙葉,他們熟練地把巨大的煙葉編在竹竿上,然后送進烤煙房烘烤。楊順說,要裝滿一間烤煙房,10個人需要編一天,每人每天的工錢是70元左右。楊順每天給工人的工資加起來約有700元,外包一頓中餐。
一間烤房的煙葉,需要烤5—7天,烤好后賣給鄉里的煙葉站。烤煙葉是個技術活,對溫度、濕度都有嚴格要求,要想烤出上等的好煙葉可不容易。“烤得好,一斤能賣15—20元,烤得差,一斤頂多賣10元。”楊順說,他第一年嘗試,心里也沒底。
村主任楊正云告訴我們,楊順此前在外面當包工頭,每年的毛收入能達到20萬元。看他能干,村委會曾找到他,想讓他當村干部,他婉拒了。
問起為啥不想當干部,楊順嘿嘿一笑:“自己干自由一些。”
尷尬的免費培訓
不過,像楊順一樣敢于嘗試并帶頭致富的人不多,大多數村民仍然擺脫不了小生產者的習慣和心理,因循守舊、安于現狀的小農意識和“重農抑商”的觀念,讓絕大多數農民不懂市場經濟運作規律,市場意識淡薄,對新技術、新信息反應遲鈍,缺乏接納、消化和吸收能力。
為提高農戶科技水平,紫云縣實行了陽光工程培訓,免費為貧困農戶提供農業技術培訓,灣塘村每年都有一次玉米種植技術培訓,數次養殖技術培訓、科技培訓等,主要以室內授課為主,結果參加的人寥寥無幾。
“自己文化水平那么低,去了也聽不懂。”楊華祥從未參加過。十年在外的坎坷經歷,帶給他更多的是一種羞怯的自卑,殘缺的教育和閉塞的信息則讓其已對現狀漠然。在他眼里,“技術”距離自己太過遙遠。
對此,紫云縣副縣長晏正武說,“也許現有培訓方式還存在一定問題,我們正在嘗試將培訓放在田間。”
武漢大學發展經濟學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葉初升認為:“農民文化程度低,直接影響了農民接受新知識和各種信息的能力,制約農民思維水平和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
2006年底,紫云縣對農村農民知識水平調查結果顯示:文盲半文盲占45%,小學占35%,初中占15%,高中占3%,大專以上的占2%。總體上,該縣農民仍然是一個“知識貧困”群體。
斷層的教育
20歲的羅麗今年剛剛訂婚,已算是村里的晚婚女孩。灣塘村的女孩子,大多十六七歲就結婚。她初中畢業后,正好碰上鎮寧一家幼師學校來村內招生,半年學費1400元,她報名了。但不到五個月就從學校回來了。
“學校很多人都走了,感覺學不到什么東西,而且花錢太多。”盡管如此,羅麗仍然懷念那段時光。如今,在雙方家庭的催促下,羅麗已經在計劃著置辦酒席。
至于對未來的想法,她吐出三個字“不知道”。村里年輕的父母們也是如此,很少考慮孩子以后的教育問題。“不知道……以后再看吧。”楊華祥說。
灣塘村有兩個小學,每所學校的年入學人數不足20人。村主任楊正云介紹:“現在第一小學共有230余人,第二小學僅有70人。因生源太少,二小快要淘汰了。”
教育幾乎處于斷層,直到2007年,村里才考取了第二個高中生,16歲的楊光祥考上了宗地鄉高中,3年后,他成為了村內有史以來第一個本科生。
離鄉那天,他自己打包了行李,到信用社辦了助學貸款,從家里帶了500塊錢,獨自坐上了開往蘭州的火車。
據了解,楊光祥的大伯楊金華是灣塘村上一任村支書,曾帶領村民開山修路,在石山旮旯里“坡改梯”,深受村民愛戴,但不幸在一次偶然事故中傷亡。大伯對楊光祥影響至深,在填報志愿時,光祥選擇了教育技術學。
“只有教育可以改變人的思維,村民極度貧困,很大程度上是太缺教育了。”
這個在灣塘村生活了十幾年的大男孩,如今已經大學三年級了,他打算畢業后從事廣播電視行業。
“廣電行業傳播效應大,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盡可能地改善村民們的思維現狀。”他堅定地認為,自己只有走出去,才會給家鄉人帶來希望。
村民眼中的幸福
打工賺錢,貸款建房,打工還貸,最后安居村內。在灣塘村,無論是四五十歲的壯年,還是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們大多固守著這套一成不變的思維邏輯,家家戶戶驚人地相似。
村里現代化的房子是用高額的代價換來的。長年在外奔波,讓他們嘗盡艱辛,有的甚至犧牲了健康。
58歲的苗族老漢韋小年,因長期在沙場打工,患上了塵肺病。在外十載的楊華祥,雖然只有25歲,已經時常感到腰疼,吃不下飯。一年到頭,他們幾乎都在辛勞中度過。
他們很少回家,只有在親戚或鄰居家辦酒席的時候才回來看看。他們非常看重這種辦酒席的時刻,無論婚喪嫁娶,只要有一家操辦此事,周邊的鄉鄰都會來幫忙。
如果你不去幫忙,等自己家辦這種事,就沒人來幫你。楊華祥說。
禮金通常是幾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視關系親疏而定。村里的紅白喜事,成為苗寨人彼此情感紐帶的同時,也給每個家庭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
在經歷了多年的背井離鄉后,他們終有一天會永遠地回到用辛勞積蓄修建起來的家中。他們夢想著,等還完建房欠債后,就回來舒舒服服地住進新房,從此再不外出打工,只守著老婆孩子,種種地,養養豬,窮一點無所謂,最重要的是跟家人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