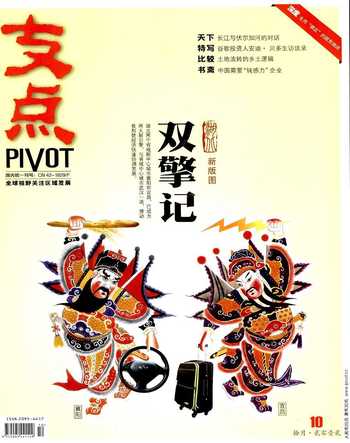中國商幫用人機制的演變
王俞現
中國商幫史上的用人機制演變經歷了三個階段:一個是以家族成員為主體的階段,以徽州鹽商為主;一個是用鄉不用親的階段,以山西票號商人為主;一個是開始用異鄉人的階段,以近代寧波商人為主。
明清徽商在揚州盛極一時,甚至有揚州實乃“徽商殖民地”的說法,這種地位是由鹽商成就的。以宗族和血緣為單位聚族而居是明代徽州的普遍現象,鹽商家族的視野是一個個被劃分了銷售區域的鹽業市場及一個個方格式的鹽場。
徽州商號如代理人、副手之類的高層伙計,一般由宗族子弟擔任,晉升、薪水等基本在內部人中間進行。約束性規定主要依靠默認的傳統習俗和宗族規矩,認同感和凝聚力主要通過祭祀先祖來維護,基本處于一個較為封閉的單元之內,尚缺少像晉商那樣需要縱橫捭闔走四方的豪氣及激勵的潛在需要。
中國沿北疆一線都活躍著晉商的身影。這些散落在各地的山西人,以張家口為東口、以殺虎口為西口,進而串起了山西人走東販西、走南闖北的一條貿易大動脈。商路上的一個個會館是山西商人丈量中國的標尺,這些會館以河南、湖北等中原地區為中心,四面輻射,生根發芽。支撐這條貿易線路的是以湖北為中轉的茶葉,這是繼絲綢、瓷器之后中國最大宗的對外貿易商品。
盡管茶路帶來的利潤可觀,但其中的艱辛也非常人所能體會。從張家口到庫倫,一年里最多走兩趟;到恰克圖,一年只能走一趟。這種長距離和全產業鏈的貿易所承載的使命,遠非一兩人所能騰挪應對。聘請非親屬的外人,成為一種迫在眉睫的選擇項。
在山西知名的票業內,自己人出任票號掌柜的寥寥無幾,絕大多數票號都用鄉不用親。陳其田曾在《山西票莊考略》中指出,“山西票莊自經理以下的職員,除了一二仆役外,清一色地雇傭山西人”。
在家族關系盛行的明清鄉土社會,這種不同尋常的規定突破了傳統的血緣局限,是中國傳統社會由親族社會轉向鄉族社會的體現,也是成就山西商人地位的標志性因素之一。
晚清,因為洋務事業的需要,跨區域用人才慢慢成為一種常態。作為中國首個股份制公司,輪船招商局一開始主要側重在傳統的船商中招商。稍后,一些靠買辦起家爾后轉型的江浙商人,因為事業的不斷拓展,開始自辦近代學校,培養多料人才。
當然,晚清也出現了一些跨省區整合資源而成立的票號,而現代金融業興起后,無論是成立大清銀行還是袁世凱在天津舉辦金融,創辦者首先想到的就是從山西票業挖人,職業人才的跨區域流動成為常態。
到了民國二三十年代,中國區域商人內部的分化加劇了這種常態。寧波人創辦的上海各馬路商界總聯合會,打破了以鄉緣為媒介的同鄉商人組織的界限,上海商人社團實現多元整合。華中師范大學教授馬敏說,商會的出現使紳商階層得以在合法形式下迅速團聚,并開始突破同鄉、同業的狹隘范圍,聯袂組合到一個區域性的商界共同體中。
地域商人的分崩離析,加劇了跨區域聘用人才的氛圍。江蘇無錫榮氏兄弟的崛起,同鄉的功勞顯赫,但也愈加兼顧了對外鄉人才的使用。當一個不局限于使用同鄉的人才氛圍形成時,江浙等地商人又超越晉商而延續了中國的商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