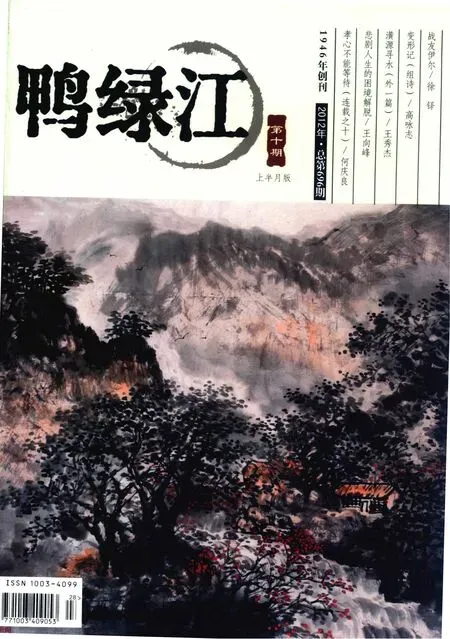變形記(組詩)
高詠志
火烈鳥
它的名字
讓我有一種
很不一般的感覺
究竟怎樣不一般
我說不大清楚
我還沒看過這種鳥
當然它也沒有
見過我
但這不妨礙我把它
寫進這首詩里
現在我并沒有
要見它的欲望
而在我看到它之前
我相信它跟
我想象的一模一樣
一只綠蘋果
記得有一本雜志
把一只綠蘋果
畫在了
全年的封皮上
而且
畫面上除了一只
綠蘋果
什么都沒有
它是將一只
完整的蘋果
分十二期吃完
每一次不多不少
咬下一口
吃掉這只蘋果
用了正好一年
到現在
那雜志里面
有些什么內容
我都不記得了
但那只被
一口一口
吃了十二個月的蘋果
還在我的記憶中
綠著
卡薩布蘭卡
一些外國地名讓我
感到奇怪
我奇怪它們
翻譯過來的
幾個漢字
什么關系都沒有
讀著卻很順
而且聽起來
還非常舒服
比如卡薩布蘭卡
卡薩布蘭卡
它的意思是
白色的房子
老實說我不喜歡
白色的房子
但這沒有影響我對
卡薩布蘭卡的感覺
好像白色的房子與
卡薩布蘭卡
它們根本就是兩碼事
關于花香
好多花香
我都聞不到
我這樣講不是說
我的鼻子有毛病
而是好多花
根本沒有什么香
一個畫家告訴我
花香是形而上的
這讓我想起了
皇帝的新衣
我不喜歡去嗅
太抽象的東西
我喜歡槐花
就是因為
它們有香而且
不用用力嗅
我就會感覺到它們
又細又軟的香氣
我知道花
主要是
用來看的
但與好看相比
還是好聞讓我
覺得舒服
干草垛
我喜歡干草
我知道草割下來
被陽光曬透
才會散發出
這樣清新的香
我夢見黃昏
我又躺在干草垛上
陽光照著
小風吹著
大雁飛著
我夢見我
再也沒有醒來
干成了一捆草
卑微、干凈、輕盈
彌漫著靈魂的氣息
兩只風箏
二十歲以前
我很少出門
就是出門
也用不了多長時間
就返回故鄉
那時候
我是故鄉的
一只風箏
二十歲以后
我很少回家
就是回家
也待不了多長時間
就回到城里
這時候
故鄉是我的
一只風箏
不論二十歲前
還是二十歲后
從沒改變的
是我和故鄉之間
那條無形的線
就是這條線
生生世世把我們
連在一起
石子之戀
我已經無法理解
當時
我怎么會那樣
迷戀石子
我尋覓它們
我夢見它們
我撫摸它們
恨不得把這些
擁有我體溫的石子
像紐扣一樣
戴在身上
現在這些石子
堆在倉庫的
角落里
它們沒了光澤
普通得不能再普通
我看著它們
有一種陌生感
好像當初迷戀它們的
是另外一個人
而那個人已被我拋得
比石子還遠
想起一些詞
我在蘇州看見過
一條很幽靜的巷子
名字叫柳巷
后來我又在太原
逛過一回街
那差不多是太原
最熱鬧的一條街
它也叫柳巷
我一直納悶
怎么會叫柳巷呢
我印象里花街柳巷
有紅燈區的意思
而且有一種
不干凈的病就是
用花柳
來稱呼的
但仔細一想
柳和花還都是
很美好的東西
其實我們每個時代
都會有好東西被弄壞
比如說小姐
多么尊貴的一個詞
現在卻被我們搞臟了
初戀
我要說的初戀
它不是初戀
它跟女人或者
第一次
都沒有關系
我要說的初戀
是一種酒
是貼在瓶子外面
寫得最大的
那兩個字
郁達夫逃亡到
蘇門答臘的時候
他開了一家酒廠
他釀的酒
就叫初戀
我沒有喝過這種酒
也猜不出它會是
什么味道
他釀的另一種酒
叫太白
記一次旅行
鄰座的女士
在讀一本雜志
我看見
她讀的那篇叫
《被雨淋濕的河》
是鬼子的小說
這是在開往S城的客車上
窗外的楊樹
一排排
朝后退去
不知什么時候
她睡著了
書落在腳下
她的頭滑向我的肩
我不知道她夢里
是不是頂著細雨
涉過了那條被淋濕的河
但我感到了被
一個陌生的女人靠著
那種特別的感覺
車上在播放電影
星仔那訓練有素的笑聲
讓我斷斷續續
抬起頭來
突然一陣顛簸
鄰座女士醒了
她把頭移回
我彎下身拾起書
遞給她
她沖我燦然一笑
很多年過去了
我還記得
那次旅行
鄰座女士的笑
她的牙非常白
她的笑容照亮我
一段無聊的旅程
現在我把它
寫進這首詩里
作為紀念
夜歌
深夜
一個人坐在房間里
獨享滿滿一屋子的黑
我感覺我像一塊糖
在慢慢融化
我明明知道
這一屋子的黑里面
其實什么都沒有
可我還是感到
說不出的充盈
我敬畏黑夜
它是夢的腹地
它告訴我
有時候只有閉上眼睛
才能看得更遠
從母親的子宮
到大地的子宮
是黑暗孕育和收留了
我們而所謂人生
不過是我們路過的一段光明
我喜歡的豹子
我喜歡豹子
單是它漂亮的斑紋
就足以令我著迷
那些很庸俗的圖案
煥發著神秘的光彩
讓我想起史蒂文斯說的
金錢是一種詩歌
其實
我對一頭豹子的了解
也僅僅止于皮毛
頂多再加上
它奔跑起來
那起伏的流線
但我想這些已經足夠
我喜歡的豹子
它不需要深奧的內心
就是有也不會
深于它的外表
我不想讓這些
捉摸不定的東西
影響一頭豹子的速度
變形記
我喜歡卡夫卡
主要是因為這三個字
排列起來
很對稱
就是換成外文也不會破壞
這種感覺
至于他的小說
雖然那么有名
我還是看不下去
讀著讀著
總會
感到一種窒息
每當這時候
我合上書
便瞧見他的名字
卡—夫—卡
一個男人
夾在兩個卡中間
我想時間久了
他肯定要害肺病
甚至會有點變形
但他居然變成
一只甲殼蟲
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偶然的桃花
我走進桃園
那些桃花
一下子全開了
它們像是等了我好久
就像心愛的女人
在我推開門的剎那
忽然亮出這么多
驚喜
寫到這里
我有點猶疑
或者這些
不過是我的幻覺
事實上
那些桃花常常在
我們想不到的時候
已經一朵朵開好
而且
它們也不會像女人
它們是桃花
所以才開得那么好
哲蚌寺
經堂里微弱的蠟燭
是我燃燒的手指
它的疼痛
連著我心底的
黑暗
冬眠的蜜
在掌心蘇醒……
我的軟弱長出蚌殼
在蚌殼里
我滴淚成珠
恍惚
一個美國人
名字我記不得了
他說
所謂的神
就是自我的
合理延伸
此刻
我對著一樹槐花發呆
我的神
他延伸到了樹上
我因此獲得了片刻
失去統治的自由
恍惚中
我不知道拿什么東西
來填充
神走后
在我身體里
留下的空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