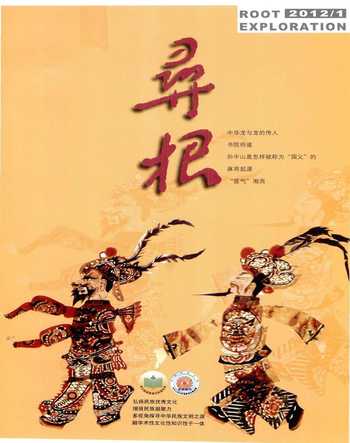書院師道
許剛
書院是古代極富“中國特色”的一種教育機構與制度,其教育宗旨、理念、旨趣、形式、方法等均有值得今日大學所宜思味、汲取者。
所謂師道,首先涉及“道”的問題。在儒家的傳統學者中,從唐朝韓愈以來,就有一種所謂“道統”的意識與執著,其《原道》等文章首揭“道統”之義,以抗衡佛道二教,并為后來宋儒所踵繼,而朱子更是將韓愈所謂的堯、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孟一脈相承之道標舉為“道統”。用今天的話來說,我想可以將其定義為儒家學者歷代所推崇、遵信并身體力行的仁義孝悌等學說與主張,“道統”就是歷代儒家學者所致力于儒家正統、正宗學說研究與恢弘的前仆后繼、薪火相傳,當然究竟誰在這歷史長河中算得上是“道統”中的一員乃至嫡傳,儒者自身也有見仁見智的不同意見,自承程朱一派上接孔孟道統的朱熹等宋儒把韓愈區別于此道統之外,即是最顯著的說明。
“道統”的概念和使用似乎離我們已經很久遠了,我在給學生上《儒家文化》專業選修課時,講到唐宋之際的“道統”,花了較多時間,學生似乎仍對此恍恍惚惚、不置可否。這也難怪,從小未嘗浸染于傳統文化典籍與氛圍中的80后、90后們,包括我這70后乃至往上的60后,對此“玄奧”的“道統”充滿疑問與困惑也是正常的,雖然現在有學者疾呼需要人文學者或傳統文化研究者重拾“道統”意識,但顯然不是短時間可以立竿見影的。
如此,我們不妨再來看“師道”,它是為人師者之道,也可謂為人師者的使命感與責任感,如果你認同了上述所說的儒家“道統”之道,那么我可以說,在中國古代為人師者的身上,同樣也含有這儒家“道統”之道的意味,它或許不必如學者那般斤斤計較,但在一些學者兼人師的身上,始終是那么強烈、濃厚地呈現并感染著授業者、聽講者。這一“師道”,也和唐代的韓愈有關,其《師說》開篇的“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擺在第一位的“傳道”,所傳即可謂“師道”,這遠非我們今天普通學校所說的“教書育人”中一般意義的道德教育。雖然道德教育自是這“師道”中極重要的一個內容,它更應該包括立志、修身、養性、涵詠等在內的對于學術文化、國家人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一種使命感與責任感,宋儒張載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或許最為近之吧!
明乎此,我們再來看中國古代書院教書育人中的“師道”,聯系當下國內中小學特別是“師道”流失已久的高校,應該說是可以有所感觸、有所體悟的。
宋儒朱子白鹿洞書院及其五教之目、為學之序、修身處世、接物之要的學規,所體現的儒家“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思想自不必說,就是晚清以降,傳統社會末期一些士大夫所創辦的書院,其中的“師道”意味亦可圈可點。比如世人仰望的史學大家陳寅恪先生,其祖父陳寶箴在光緒六年(1880年),任河南省河北道員,創致用精舍,“河北風趨為一變”(陳三立語)。光緒八年(1882年),陳寶箴擢浙江按察使,其離任前,即取所為《致用精舍記》《致用精舍學規》(《說學》諸篇匯刊之,“以稔后之君子及諸生之造于學者”,正可見其心思之所傾注,而謂:“河北山川輪郁,賢豪之所代鐘,殆將有瑰瑋卓犖之士,明體達用,出而經緯天地、彌綸萬變者乎?茍子曰:‘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細流,無以成江河。篤之,培之,擴之,充之,以俟君子。”
今欲有所申論者,為《致用精舍學規》中之第四條,全文如下:
一、成德成材,本屬一貫,后人歧而視之,遂致學術不古。肄業諸生,或文才可觀,而于孝弟本原上不能盡職,雖有一切聰明才辨,適足以成為小人而已。孔子謂:“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庭闈多闕,則異日之致君可知。故《大學》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其有內行肫篤而于經世大務荒穢不治,但取淺近語錄奉為師資,則亦不足以成大器。精舍之設,原欲合體用為一,為國家樹千百孝子忠臣、賢相良將,所以望諸生者厚矣。山長于考察課程外,咨訪諸生平日所以事親事長之道,如內行不敦,斯宮墻有玷,即不得士禮相待。諸生宜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這段文字,具論孝悌本原,宜加注意:首先,《致用精舍學規》凡十五條,論及誦習經史、旁覽天算、存錄日記、戒驕矜、免爭心、師弟情義、謁圣拜師等諸多方面,然而專門闡論道德、申明孝悌,唯此一條,足見寶箴之看重。其次,“山長于考察課程外,咨訪諸生平日所以事親事長之道,如內行不敦,斯宮墻有玷,即不得士禮相待”,此一方面;另一方面亦當注意,陳寶箴并非唯孝悌而不及其他,其先曰“于孝弟本原上不能盡職,雖有一切聰明才辨,適足以成為小人而已”,后則曰“其有內行肫篤而于經世大務荒穢不治,但取淺近語錄奉為師資,則亦不足以成大器”,足證其于道德、學問之“道”(孝道等倫理品行)與“學”(經史等學術才干)或說“德”與“才”并不偏廢一端,而是合乎傳統倡導的“道德學問,打成一片”,也就是陳寶箴所謂的“成德成材,本屬一貫”。故曰:“精舍之設,原欲合體用為一,為國家樹千百孝子忠臣、賢相良將,所以望諸生者厚矣。”“體用”亦即德、才,體之立而道生于身者為孝子忠臣,用之達而學濟于世者為賢相良將,以此寄望于后生者,豈止是孤懷卓識于近代保守與進步、頑固與激進之上,就是對比今日之培養教育,吾輩又得無愧乎?
陳寶箴在其與致用精舍諸生交勉之《說學》中云,無論“忠臣孝子”,抑或“無忝所生”,同樣屬于為學立志,“細細推勘、刻刻提撕,自然志氣奮發”。這是陳寶箴所屢屢提示后進以孝道倫理之真摯所在。一旦遇見才俊非議綱常,必平和曉諭;一旦獲見名士敢言異說,則從容辨析。故綜觀陳寶箴之所倡行,真可見其于孝道倫理價值諄諄教誨、循循啟誘,誠欲竭心盡力維系傳統道德,并以此造就人才、導引學子也。
這樣的書院、這樣的學規、這樣的教育、這樣的“師道”,似乎現在距離我們已經有些時日了,并且還在越來越遠,這是讓人痛心的!當然也不能說一無所有,畢竟每個時代都會讓人看到一些傳統文化得以傳承、綿延的身影和努力,業師張新民先生創辦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苦心經營,在我看來,又強烈地看到并感受到令人振奮的“師道”。《中國文化書院學規》第七條曰:“欲成就偉大之事業,必先成就偉大之學業。成就偉大之學業不能不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以發明真理為職志;成就偉大之事業亦必擔負起人類群體之責任,以服務于社會為光榮。非特要蔚成學風,起一代人文,更要聚為良習,興百年禮樂。此皆非取消而實為成全人之天才與個性也。故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無論于學業于事業,均為至要至大之關鍵焉。”這里面,跳躍著的不正是“師道”的使命、“傳道”的精神嗎?
我鐘情“中國特色”的書院師道,我且充滿溫情與敬意地踐行其中并注視、期待著它的授受與光大。
作者單位:華中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