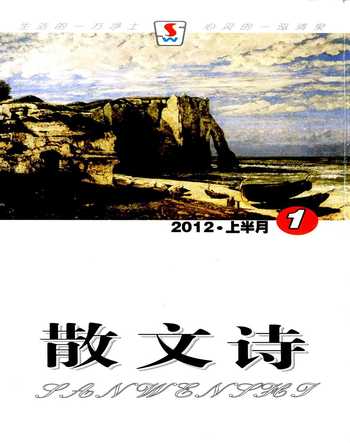禪思
2012-04-29 01:00:42龍彼德
散文詩 2012年1期
龍彼德
“禪思是打通‘古典與‘現(xiàn)代的奇妙出入口。”這是詩學(xué)家陳仲義的卓識,但他同時感嘆:“五四新詩運動在徹底破除舊詩詞格律枷鎖后,竟也把千百年來裊裊不息的禪思香火給掐滅了,翻開新詩編年史,專司于斯的詩人鳳毛麟角,1917年至1949年三十年間,大概只能找出廢名一人。”
《樹與柴火》可以說是廢名少有的散文詩,表面看似乎沒有什么特色,實質(zhì)上是一篇成功運用禪思的佳作。他從“柴火”談起。先是自己的孩子“揀柴”,繼而是自己小時候揀柴。揀柴的地點是樹林,由“柴火”便過渡到“樹”。樹有季節(jié)之分,春葉不如冬葉。“冬日的落葉。乃是生之跳舞。”從植物忽進入生命……思路跳躍,語意曲折,正是禪宗思維的主要特點。在落葉中,他突出了“松毛”(“松毛者,松葉之落地而枯黃者也。”)“大力者舉一擔(dān)松毛而肩之,龐大如兩只巨獸,……此時落日不是落日而是朝陽了。”由“松毛”到“朝陽”沒有過渡,非推理,非分析判斷,完全是一種直覺的激活,一種悟性的出現(xiàn)。當(dāng)然,這與前文“我仿佛一枚一枚的葉子都是一個一個的生命了”不無關(guān)系,但中間的文意已斷,正是作者提倡的“隔”。廢名認(rèn)為,隔與不隔乃是區(qū)分散文與詩的標(biāo)準(zhǔn)。
最后一段將人類的記憶比喻成“柴火”,所謂“春華秋實”“昨夜星辰,今朝露水”,只不過是“火之平生”而已。“終于又是虛空,因為火燒了則無有也。”這不就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諸受皆苦”和“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yīng)作如是觀”的佛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