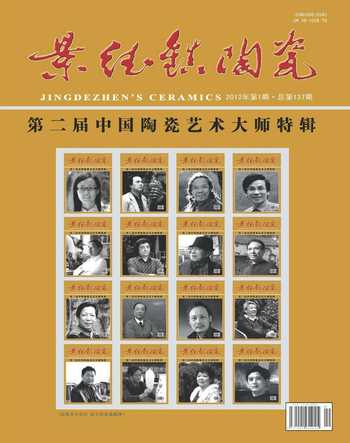淺論中國畫的筆墨節奏
楊冰 文靜
一、緒論
筆墨是中國畫的工具,也是中國畫用以造型的獨特藝術語言,是中國畫評判優劣的標準之一。因此,筆墨是外在、是形式、是體現、是升華。而節奏,從外而言是不同民族、不同時代、不同藝術家藝術形式的具體體現;從內而言是人類精神的律動。節奏是任何藝術形式共通的研究命題。對畫而言,節奏在筆墨中隱現流動,筆墨在節奏中“氣韻生動”。
二、節奏的形式美感
筆墨是兩個概念,但“蓋筆墨兩者,相依則為用,相離則俱毀。”故而聯系在一起論其節奏。筆墨節奏的形式美感來自一種形象性的表現,有著視覺上的效果。但這種美感同時也來自作者對韻律的把握。這種獨特的韻律使畫中自然體現出一種動人的效果。就美感而言,既來自于好的形式,又來自于形式背后的內容。好的形式誘人深入,賞心悅目:大大小小、疏疏密密、起起落落的筆墨對比形成的節奏;中國畫用筆特有的書法筆意形成的節奏,和筆墨所特有的濃淡干濕的變化形成的節奏……但這節奏不是內心的共鳴就只能作為一種人為的制作式的擺布,只為求得形式。而有內容的形式帶來視覺和精神上的雙重享受。畫面自有的韻律,是畫家恰到好處地運用技巧來表現自己的心境成為畫境,并在筆墨中產生共鳴,形成一種節奏。這節奏使得濃淡干濕經得起推敲,使得畫尤為生動。好的形式是前提手段不是目的根本,不可本末倒置。有句話可以驚醒我們,法國蘇弗爾說,藝術有兩條路:大路藝術憾人,小路藝術娛人。而可以憾人的是情,決不是怎樣具體的形式,只是在繪畫藝術中,情通過形式來表現,而情讓形式成為千古絕畫。就國畫而言,謝赫“六法”中的第一法為“氣韻生動”。就當下盛行的裝飾畫而言,其筆墨亦是追求趣味的,而不是一味地為了形式而形式。作為藝術性的繪畫不僅要能帶給人視覺上的享受,還要給人以精神的愉悅或思考。筆墨節奏的形式美感與畫面的內容是相得益彰的。歷來的優秀畫作,其筆墨必與思想在紙上共舞。為此,我想以以下例子來作進一步的說明:
1、《溪山行旅圖》
北宋范寬所作。北方山水畫派的四大鼎足之一。明董其昌見畫后嘆到“宋畫第一”;徐悲鴻稱“中國所有之寶,吾最傾倒者。”此畫歷經數代而魅力不減,魅力從何而來?畫面又何以動人?對于筆墨的表現力,郭若虛評價為“槍筆俱均,人屋皆質。”吳冠中曾寫過一篇文章《筆墨等于零》,其意思是說脫離了具體畫面,不具表現力的筆墨等于零。筆墨只有表現了“質”與“氣”,才有了意義與生命力,才達到“真”(“真”與純真、精神、本質等有著內在的聯系)。而“槍筆”是書法中由蹲而斜向上急出的一種用筆方法,富于力度,可以很好地表現山石的質地和作者的精神面貌。但這只完成了“質”。 對于“氣”,“ 氣”是指自然物的內在精神,是作者所感受到的。它在筆墨之間形成節奏。誠如荊浩所言“氣者,心隨筆運,取象不惑。”即是說:筆之所至,即心之所運,氣之所生;是說,畫家應用心來統帥用筆以達到認識與表象的合二為一。
韻律,是情之所生。僅就個人而言,它包括作者的性格修養、人生追求、個人經歷等。就性格而言,《圣朝名畫評》記“ 性溫厚,有大度,故時人目為范寬”,《畫聞見圖志》記:“以其性寬,故人呼為范寬也”。可見他的性格應當寬厚,畫如其人,反映到畫中,筆墨雄沉渾厚而無浮夸,營造的氣勢逼人而不是野景小趣,自是性格使然。就修養而言,山水始學李成、荊浩,米芾曾指出范寬師荊浩“山頂好作密林,山際作突兀大石”以及“氣勢雄杰、山巒正面折落,四面峻厚”這些即便在《溪》中也可看出一些端倪。就人生追求而言,范寬“好道”,即以老莊哲學為根本。道家崇尚自然,佛家關心生靈。基于這種追求他深入山川去“師物”“師諸心”,又因為關心生靈,畫面才讓人感覺貼切并富有生氣,是蓬勃向上的。因而筆墨節奏富有了生命的張力。就個人經歷而言,始學李、荊,后有所悟“于是舍其舊習,卜居于終南,太華巖隈林麓之間”。終南、太華二山皆為關峽名山,其山巒形勢之美和人文氛圍都給范寬的藝術境界提供了生活基礎。再加之,終南峰高路險幽暗如夜,太華奇險雄偉。這些都可以從《溪》和他的其它畫作中找到相似之處,這些感受都會被帶進畫面,通過畫面傳達給讀者,宋人說范寬“善與山水傳神”即來于此。人們在體味畫面的形式美感時,人們體味到的是形式帶來的“神”態。
如果說韻律是“氣”,多受感性的影響;那么內容就是“質”,多受理性的影響。繪畫需要激情,需要有想提筆的沖動,需要赤誠的熱愛,但繪畫依然是講道理的、是有很多道理可尋的。西方有人抨擊中國繪畫不科學,這是沒有支撐的觀點。中國人有著自己的寫生方式,只不過不是像西方那樣把人體比例等定的那樣精確,甚或用尺子測量用格子定位,我們則有著另一種的嚴謹方式:《溪》中反復的皴法不是無規律的或是經過嚴謹的測量的,它是作者觀察、感受總結出的表現方法。相對于西方數理光學的科學而言,中國人習慣目識心記,不盲目相信自己的眼睛,但這并不等同于不講究“形”,而是中國人更重“形神兼備、以形寫神”。總之,中國的繪畫有著自己民族的特色。包括著民族、時代和物象這樣客觀和理性的方面。就《溪山行旅圖》的時代而言,絹本、水墨,鐘情的是全景式的山水,尤重意境、筆墨和氣韻。筆墨的時代性體現為剛健蒼勁,筆墨節奏也同這一時期的畫一樣,都充溢著陽剛之氣,蘊含著人生命的律動。在《溪》中物象作為作者的觀察所得,它必然是作者感受到的,因而情在理之中,情與理共同組織畫面,構成畫面的思想。這思想不同于情,不是主觀主義全無章法的涂抹,不同于理,不是不帶任何情感的。在繪畫中,這思想觀念把感覺、情緒整個組合起來或構成藝術的出發點。
2、《墨葡萄圖》
明代徐渭,大寫意畫派的先驅。其畫風影響了朱耷、吳昌碩、齊白石等人。此畫被推為其代表作。從視覺效果上看,形象簡練、格局奇特;就筆墨節奏來看,痛快淋漓、奔放恣意。 就“情”而論:徐渭一生坎坷到晚年仍過得極不安定,曾撰寫過《四聲猿》抨擊時政,想要有所作為卻潦倒一生,性格豪放。繼承了梁楷的減筆畫和林良、沈周、文征明等寫意花卉的畫法而更為簡練,他在繪畫中追求作品的精神境界。這諸多因素致使他繪畫所持有的特質,也致使他形成自己的形式。徐渭與范寬不同,他的性格較之范寬更為奔放,加之他懷才不遇,內心郁結并受社會冷漠,這種感情一一寄予筆端來表現,自然其筆墨節奏必然肆意而富有動勢,是活動的、奔放的、舞蹈著的。枝葉、果實更像是大大小小的音符表達著作者的心聲,只有有著這樣的情才造就著這樣的形式美感。
“理”駕馭著情,正如前文所講,是把感覺和情緒組織起來的依據,是思想性的。“理”受時代、民族、環境等因素的影響。從徐渭所處的時代看,內部朝廷腐敗,奸黨專橫,外部倭寇屢侵,人民苦不堪言。所以其畫中常有郁憤不滿的情緒。民族的一面是與生俱來的,歷來文人士大夫不得志便寄情于書畫以自慰或旁敲側擊時政。就筆墨本身而言也是民族性的,畫并不是僅僅作為情感的宣泄,不是帶著情就涂抹一通。觀《墨》他也是有章法有理可講的,有枝有葉有筆有墨有意有境,我們不能不說,這種筆墨節奏比起傳統筆墨,因和情一起為舞、和內容更相符,而顯得這種筆墨節奏的形式美感有憾人的效果。
因而,是情與理的共同作用使得視覺上筆墨節奏的形式美感有著強大的魅力。3、《星月夜》
西方畫家凡·高代表作之一,之所以要對西畫進行分析是因為藝術是不分國界的,好的節奏可以感染不同膚色的人,藝術的發展更要在比較之中各取所長,西方的繪畫亦有其自己的筆墨節奏。
從單純的視覺效果上來說,其“筆墨”雖不像國畫中那樣注重用線也不追求“水墨淋漓”的筆墨情趣,但筆觸長長短短形成對比,富有動勢,從形式來看,松柏的筆觸最重并且長而柔動,天空的筆觸短而密集甚至排列成漩渦形,房屋和山坡則處理成有輕重對比的曲線。長、短、曲線的對比加之顏色上黃、藍對比,使得畫面更加鮮明。
從情感角度看,繪畫是凡·高自身的選擇,更是其發自內心的呼喊。就性格而言,他急躁、易怒、敏感、情緒波動大。就修養而言他自兒時就養成讀書學習的習慣,對文學和哲學及繪畫史都有深刻的了解。就個人經歷而言,十六歲時在畫廊賣畫,二十三歲任教師,二十四歲做店員,二十六歲傳教,二十七歲以畫畫為業,至此由其弟維持生活而畫作卻難以賣出,三十七歲死。但由于他在畫廊賣畫長達六年,因而對畫有一定鑒賞力;傳教士的經歷讓他了解人間疾苦,想要解救,不得,便自救而擇畫,再基于對自然有著深沉的熱愛,于是有了這樣充沛的感情和這樣充沛的畫面。文學讓他在畫作中尋找意義,是一些值得信賴和愛的事物,又因為性格敏感,才捕捉了那么多生活中別人察覺不到的美。正因為這樣《星月夜》是凡·高心中的筆下的。
從思想而言,凡·高自己曾說:“安排色彩可以創造詩歌,亦如音樂可以撫慰人心。”可見他的畫作不只是情是強烈的熱愛,也有著深沉的思考和美好的目的。而蔣勛的說法正好證實了這一點,他說:“這幅畫安慰了許多人,好像我們借著一個重病的人的苦難舒緩了我們自己內心的焦慮與不安。”從東西方畫家對于畫面感覺的契合可以看出,畫面透過形式其內容的東西是可以撫慰人心的。這賦予形式以崇高的內容,也是形式的意義。
總之,這些畫作在這里只是被作為代表而提出來做分析,但我們可以從以上例子中看出一些共通的地方,并以此類推。通過分析,我們大略可以認同:筆墨節奏的形式美感不僅來自形式也來自形式之外,其中包括個人、民族和時代的特質等方面。這些認知有助于我們從宏觀上把握一幅畫的筆墨節奏,相當于縱軸。但從哪入手,從何處出發?我們還需要一個可以把握的橫軸,固定一個點,用以切入。如果以傳達和寄予作為橫軸,情感則是我要提出的點。以下即通過分析筆墨節奏對情感的傳達和寄予,來深入探究筆墨節奏的表現方法方式,以期達到情文并茂的境界。
三、筆墨節奏對情感的傳達和寄予
關于筆墨。筆墨的功能有二,它可以用于再現人的情感的物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可以表現人自身的感情即傳達情感。筆墨表現情感是雙重的:一方面是通過對物象的再現而表現,另一方面筆墨本身也具有表情功能,二者又相互統一。無論如何,這種筆墨表現是筆墨運用才產生的。筆墨,落而成點,運而成線,潑而成面,用以成象。這里僅就線展開論述:線孕育著豐富的情感,如在《溪山行旅圖》中傳達出內涵的深度,在《星月夜》中是一種急切的熱愛,再如在梁楷的《太白行吟圖》中傳達出一種自由奔放的情感。當然這些表情功能和傳達的內容只有結合到具體畫面才有意義。
關于節奏。節奏的傳達是不言而喻的。貢布里希的研究證明“從單一的節奏直到豐富的節奏,各種節奏有各自獨特的聯想作用和心里效應”。只是節奏的形成在音樂中依靠音符,在畫面中依靠具體的物象如筆墨。
關于筆墨節奏。從筆墨和節奏的單獨分析中,可知筆墨對于情感的傳達依靠節奏。依舊拿線舉例:線要有抑揚頓挫、輕重緩急、長短曲直、強弱虛實,這些都形成節奏,構成畫面特有的韻律感,傳達著不同的聲音從而產生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使觀者得到審美的愉悅。節奏的傳達則要以筆墨或其他物象的形為依托,因而,筆墨、節奏需聯系在一起方構成傳達情感的條件。筆墨節奏的沉穩有力,或密而急則可傳達出震撼鮮明強烈的感覺如《星月夜》;或滿而徐則可傳達出一種氣勢如宏的感覺與《星月夜》迥異如《溪山行旅圖》。
關于傳達與寄予。傳達是寄予的目的和歸宿。傳達取決予寄予,但除與寄予有關還包括觀者的不同而有差異。舉一故事為例,劉備帶著關羽請諸葛亮出山,去前吩咐關羽不準說話,諸葛亮想知劉備心胸如何,便問關羽:“你在想什么?”關羽餓了想吃餅不敢言,于是畫了一個圈,諸葛亮以為其要一統天下便出山,這雖然是個詼諧的故事,卻讓我們知道聽者、觀者首先從自己出發,藝術便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
四、結束語
有藝術處有音樂,節奏是藝術“活”的動力,死水之死是死在不流不動,而泉水叮咚、大海濤濤,生生不息。萬物之變化,盡有其各自的節奏。節奏是任何藝術都逃脫不開的,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因而對于畫而言,筆墨節奏實為我們把握筆墨,把握繪畫的一條路徑,不可忽略。
參考文獻:
楊成寅,林文霞.中國書畫名家畫語圖解 潘天壽[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70-79
馬鴻增. 北方山水畫派[M].吉林美術出版社,2003:60-132
劉治貴. 閱讀凡·高[M].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53-76
(英)貢布里希.秩序感[M].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