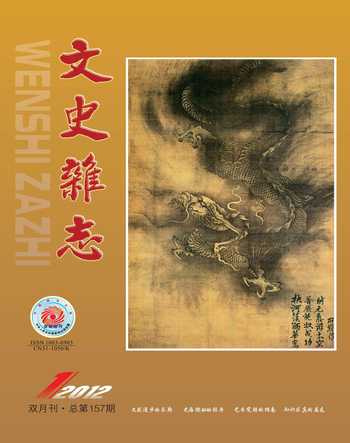對社會轉型中的彝族年節文化的思考
羅曲 秦艷
彝族年節文化和其他任何一種文化一樣,是一種適應的體系,涉及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心理等三種關系。在這三種關系的適應歷程中,彝族年從表現自然崇拜到祖先崇拜,到娛樂成份的增加,使彝族年節文化成為了一個復雜的“文化復合體”,并表現出相應的功能。當時針指向21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后的今天,彝區和其他地區一樣,處于社會轉型期,不僅使體制轉型、社會結構變化、社會文化變遷,而且文化信息處理電子化,出現了新型傳播媒體;同時,由于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而使必要勞動時間大為減少,閑暇時間大為增加,人們的生活觀念大為改變,使社會具有休閑經濟社會的性質。此外,彝區在發展當地的休閑旅游經濟方面,已經認識到利用民族文化資源的重要性,并在民族文化資源的開發利用上已經有所作為。在這樣的社會發展背景下,作為文化復合體的彝族年節文化,表現出新的適應功能。與之相應,地方政府在開發著彝族年節文化的新功能,使之在當今人們的休閑生活中發揮積極作用。
彝族年節文化的這種新作用,通過媒體傳播為廣大受眾所知曉;而部分受眾知曉了彝族年節文化的這種新功能,便前往彝區體驗享受之,這又從客觀上助推了彝族年節文化休閑旅游功能的進一步顯現。從四川彝區看,2009年以來的彝族年節,不再像過去那樣“傳統”,因而從2009年以來網絡上關于彝族年的報道,不再拘泥于傳統的、原生態的彝族民間年文化習俗,而是更多地出現了與彝族年文化相關的“繁衍品”,例如關于“彝族年文化”旅游業的報道便是明顯的例子。正是基于彝族民間對本民族文化的訴求以及外部希望了解彝族年文化的愿望,彝區以彝族年為基礎進行的彝族年旅游業遂迅速興起,并通過網絡進行傳播,使受眾在鼠標的點擊中受到影響。彝族年正是在這樣的一種文化語境下逐漸被更多的人知曉和了解,也逐漸產生了變異。在官方網站傳播中,已經強烈地感覺到彝族年在彝族地區已經慢慢開始形成“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吸引外地游客、拉動本地經濟創收,文化、經濟共同發展的模式。當然,將本民族節日文化以市場化的做法并不是彝族率先開創的,全國很多地區的少數民族都已將本民族節日文化市場經濟化了,像傣族的潑水節等即是例子。我國民族眾多,各民族的節日更是豐富多彩,“漢族節日500多個,少數民族的節日1200多個”。對于各個民族而言,本民族的節日都是具有紀念價值和娛樂功能的。因此,在節日之際,人們都希望從事一些慶賀活動,這也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傳承和發展。在這種傳承和發展中,人們近年開始嘗試將經濟元素加入節慶活動當中。如此一來,既慶祝了本民族的節日,又促進了地方經濟的發展。“全國節慶市場化的先河開始于1985年初,北京東城區文化局恢復中斷多年的地壇廟會,搭起當時全京城最大的一個群眾文化舞臺。廟會期間吸引了國內外游客70多萬人,盈利38萬元,利用節慶文化創造了可觀的財富”。
從網絡傳播的信息看,近年市場經濟下的網絡傳播,為當地彝族年文化的傳播提供了極受歡迎的渠道。政府充分地利用了這種宣傳渠道。在當地政府的操持下,現在彝族舉辦的彝族年慶祝活動,越來越多地呈現出將彝歷年打造成為具有民族特色的休閑文化品牌的趨勢。例如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州政府所在地西昌,在2009年彝歷年的時候舉行了“冬春陽光之旅”、“品我涼山,愛我家鄉”等一系列的旅游活動,通過網絡傳播加強宣傳力度,吸引來各地游客。
為促進涼山地區彝族年旅游節日文化的發展,當地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為貫徹州委、州政府提出的一邊加強外部促銷一邊擴大內部宣傳,實現將彝族年打造成涼山民族風情第二節的目標,相關部門2009年11月20日在西昌月城廣場正式啟動了“品我涼山,愛我家鄉”的涼山人游涼山活動,拉開了2009年彝歷年相關慶典活動,從而也拉開西昌“冬春陽光之旅”的序幕。從有關報道可知,其內容有祈福、慶豐收、殺年豬、砣砣肉宴……在11月20日-26日彝歷新年期間,西昌市精心準備了眾多極富民族特色的慶祝活動,以吸引游客前來作陽光之旅。除20日在西昌市火把廣場舉行彝族新年祈福儀式外,還有安哈民俗文化藝術節、普格縣螺髻山彝寨的“大涼山上品彝風,螺髻山下過彝年”活動、涼山州歌舞團經典節目薈萃《精彩歲月》、西昌風情美食節狂歡晚會等。彝歷新年期間,還舉辦了全國跆拳道精英賽、環邛海馬拉松賽、徒步登瀘山大賽、少數民族鄉鎮籃球賽、彝歷年彝族式射箭比賽等。
到了2010年,彝族年節在2009年的基礎上,其休閑旅游功能又有所增強。據四川省人民政府網站2010年11月23日采自涼山州政府門戶網站的資料:截至2010年11月22日下午4點30分的不完全統計,西昌市、鹽源縣、冕寧縣、普格縣、雷波縣四縣一市共接待游客7.4312萬人次,其中過夜游游客1.8736萬人次,一日游游客5.5576萬人次,實現旅游收入2092.6萬元,接待自駕車1970余輛,酒店入住率36.44%。由車牌照顯示,游客多數來至成渝等地。11月23日旅游情況為:第一,由西昌市委市政府主辦,邛海瀘山管理局、市總工會、市旅游和文化體育局承辦的“2010中國·西昌第三屆環湖半馬拉松大賽”在邛海瀘山景區隆重舉行。參加的運動員有成都、攀枝花、涼山各縣市等不同地區的體育愛好者100多名。第二,在這陽光明媚的出游日,大多數游客選擇到邛海瀘山景區。人們走進小漁村各美食節的餐飲點,家家人聲鼎沸,一只只載滿游客的游船從月色風情小鎮帶著興致盎然的游客來品嘗鮮美的特色燒烤,品嘗漁家風味餐飲。客人們高興地評價著如畫美景,邊揮著汗、吃著麻辣燒烤,那種滿足、興奮全寫在臉上。
隨著旅游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彝族聚居區的政府已經認識到,頗具民族特色的彝歷年是促進本地區旅游經濟發展的又一資源,而有效運用這一資源的宣傳平臺便是于“無形”當中現“有型”的網絡傳播。于是大家越來越重視網絡這一信息快速傳播的手段,將彝族年特色文化植入網絡報道之中,使廣大的受眾可以接觸到其信息源。在網絡傳播的時代,受眾群體享有極大的自主權;因而,政府宣傳是否到位,便成為一份特色文化考卷,考驗著當地政府對本民族文化的理解以及包裝的能力。
文化產業是一個朝陽產業,它從經濟的邊緣逐步走向經濟的中心。所以近年來文化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民族文化產業的發展也是這一發展上的關鍵鏈條。它將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轉化為一種文化資本,使其資本化運營,根據市場需求,投入民族文化資本、貨幣資本、人力資本、技術資本等,生產出適銷對路的文化產品來供應社會,以此獲得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很多地方政府大力支持以彝族年為基礎進行包裝的這種特色旅游品牌,由此而展開了一波又一波的網絡傳媒大戰。大家各自出招,宣傳當地年節文化,以吸引更多的游客到當地進行觀光,在促進當地文化繁榮的同時,也促進經濟的良性
循環發展。
從相關彝區政府官網上的報道來看,各彝區的彝族年旅游文化,以豐富多彩的彝民族傳統文化為依托,把彝族的人文風情、自然景觀合為一體,形成具有片區特色的完整旅游鏈,以吸引天下的游客。這種民族旅游項目是一種將民族民俗旅游化、民族節慶市場化、民族藝術商業化、民族文化品牌化等等結合起來,綜合發展經濟創收、文化繁榮的民族品牌文化項目。
在一片為民族年節文化旅游開發叫好聲的同時,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便是民族文化的開發與保護。很多相關網絡報道也流露出彝族年同樣面臨保護的問題。現代化社會環境中的彝族年,開始面臨選擇:首先是彝區開放后,面臨的其他民族的文化沖擊。在有些地方,彝族年只是一種象征文化符號。例如涼山甘洛縣,白彝地方的村民對于自己民族的彝族年只是象征性地簡單過一下,而對中國各民族的傳統春節卻過得非常隆重。散居彝族居住的地方,像貴州某些村落則已經不過彝族年了。針對這一情況,當地政府應當適度引導群眾,重新強化本民族的文化心理,讓其獨特的民族文化得以流傳。
對于民俗活動,政府不宜過度參與。若是政府過度干預民俗,反客為主的話,在經濟利益的誘導下,很容易導致偽民俗事項的產生,會排斥節日主體而扼殺民間社會積極性,使歷史悠久的彝族年最終成為無民間根基的官方旅游節。當然,彝族年文化旅游業本身的發展又離不開政府在政策上的指引,所以這就要求政府要將自己的職能行使權控制在一定范圍內,為彝族年這一民俗文化的繼承與發展提供一個寬容、和睦、友好、尊重的文化環境,使之可以在新的社會環境下健康、良性地傳承。
在包含著最核心的彝族傳統文化信仰根基的大樹下,無數新生的幼苗試圖以此為基礎或使自己發展,或尋找更廣闊的生存空間。人類社會在發展的同時,其傳統文化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變異,從而產生葆有民族傳統文化精神的新文化。所以,一種年節文化始終承載的是一種民族氣質與精神。就彝族傳統文化而言,它在流傳的過程中,雖然要經歷歷史長河的洗禮,因生活內容的豐富而使彝族年節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但其彝族年節這個特質是不會變化的。我們也不應該丟掉這樣的特質。所以,對于彝族年節文化來說,如果離開民族民間的空間和地理,由城市操辦,其“年味”也便失去了鄉土味,也難說得上民族特色。對此人們應當進行深入的思考。也就是說,如何讓彝族年這一獨具風格的民族文化的傳承在現代環境下保持自然發展的狀態,是一個應當重視的問題。所以,當地政府部門在“開發”熱浪中,必須重視對彝族年的自然生存和發展的文化土壤的保持;因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要成為世界的,必須是民族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