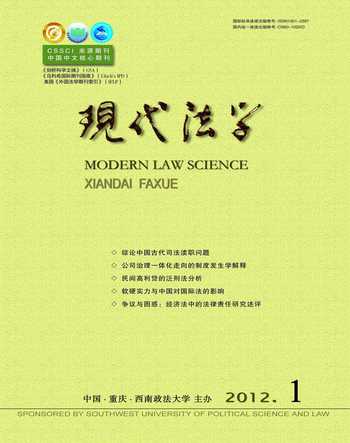軟硬實力與中國對國際法的影響
徐崇利
摘 要:晚近以來,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迅猛崛起,然而,中國對國際法的影響仍然有限,與中國實力的快速增強很不相稱。造成這種反常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軟硬實力大小的失衡及發揮的受限。要扭轉這種不利局面,絕非一日之功而能成就。雖然如此,在國際法律過程中,中國仍然可以根據軟硬實力作用的機理,通過利益和觀念兩大維度盡量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
關鍵詞:中國崛起;國際法;實力;軟實力;硬實力
中圖分類號:DF96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2.01.15
一、導論
國際法具有兩大維度:利益和觀念。[注:對于國際法之利益和觀念(價值觀)兩種維度的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參見:K. W. Abbott & D. Snidal. Value and Interests: International Legalization in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tion[J].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2002,31(2):141-178.]從利益之維度來看,國際法律過程是各國之間分配利益的過程,即國家作為利己的主體必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遵循的是“結果性邏輯”(工具理性),以結果是否于己有利作為行為的導向。國際法的這種理性選擇模式得到了現實主義和制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支持。從觀念之維度來看,國際法律過程是各國實現觀念的過程,遵循的是“適當性邏輯”(價值理性),即各國以適當與否作為自己是否行為的準則。國際法的這種理念選擇模式得到了理想主義和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支持。應該說,任何國際法律制度都兼有
利益和觀念兩大維度,利益和觀念構成國際法這塊硬幣的兩面。
目前,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缺乏權位凌駕于各國之上的世界政府,國際權力(實力)結構必然影響國際法。按照國際關系理論,各國的實力由硬實力和軟實力兩大部分構成。硬實力以一國的軍事、經濟和科技等物質力量為主要內容,而軟實力則表現為來自一國意識形態、文化觀念、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發展模式、國際形象和外交方針等方面的示范力、吸引力和說服力。從軟硬實力的內涵來看,與硬實力相對應的,主要是國際法的利益之維度,即硬實力直接影響的是各國間利益的分配;與軟實力相聯系的則主要是國際法的觀念之維度,即軟實力直接影響的是國際法律過程中的價值判斷。
如所周知,一國實力的大小決定該國對國際法的影響程度。在改革開放之前,基于當時東西方對立和南北矛盾的現實,中國作為一個“體系外國家”,對傳統的西方國際法提出了強烈的挑戰,扮演著一個革命者的角色。在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開始成為一個“體系內國家”,雖主張對現行的國際法律秩序進行改革,但因實力有待提高,難以大有作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作為一個大國迅猛崛起。然而,從現狀來看,中國對國際法的影響力仍然有限,與中國實力的快速提升很不相稱。在國際法律過程中,面對西方國家,當下中國經常不是處于主動作為,而是處于被動應對的狀態。此乃一個反常的現象,就其產生的原因以及相應的對策,可從軟硬實力對國際法的作用機理中得到解讀。
二、軟硬實力大小失衡與中國對國際法的影響
人們通常言及一國實力對國際法的影響,其實,該語境中的實力僅指硬實力,表達的也只是硬實力對國際法利益之維度的作用。顯然,這樣的習慣性理解是不全面的,忽略了各國軟實力對國際法中價值實現影響的另一面。按照理想主義和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僅有利益的考量,而舍棄觀念之維度,國際法就會出現“偏癱”。對于中國而言,有的外國學者指出,“晚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實踐和言論反映了一種持續的、也許是更強烈的對權力和利益之地位的認識。……盡管這些特點表明其廣泛地符合現實主義的教義,但是假如中國對國家之間的法律(和其他)關系的規范性視域消失了,那么將是異乎尋常的。現實表明并非如此。……北京部分擁戴‘亞洲價值觀和以文化相對主義的視角看待國際人權法也是一種很高的規范性語調。”[1]
此類觀點雖然認定中國對待國際法首先延續了追求硬實力和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作法,同時也沒有置國際法之觀念維度于不顧,但是并沒有進一步探討中國軟實力對國際法觀念之維度的具體作用問題。恰恰是在這方面,中國對國際法的影響力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一)總體狀況
無庸質疑,國際法需建立在各國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即國際法是各國相互合作的產物,而合作必得有剩余。然而,各國雖有共同利益(合作剩余),但仍存在著共同利益如何分配的問題。按照現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觀點,硬實力是決定各國之間利益分配的工具;亦即,一國硬實力越大,所獲的利益也越多[2]。
晚近以來,中國的硬實力大增,僅以總體經濟實力觀之,2009年,我國GDP總量達到了4.91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三,2010年上半年已超過日本,僅次于美國,名列世界第二。同時,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第五大資本輸出國。應該說,硬實力的增強使得中國通過利益之維度對國際法的影響程度有所增大。
然而,中國硬實力的飆升并不必然意味著軟實力的變化,硬實力的成長是軟實力提升的基礎,但硬實力本身并不會自動轉化為軟實力[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雖然在發展模式(如“北京共識”)、文化觀念和外交方針等方面的軟實力提升較快,但在世界范圍內并未取得主導性地位;毋庸諱言,中國在意識形態、政治社會制度以及國際形象等方面的軟實力還有待進一步提升或投射。2009年7月,45位中國頂級的國際問題專家通過投票選出未來十年中國與世界交往面臨的五大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加強中國軟實力建設和提升中國國家形象”[4]。
2011年10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顯,維護國家文化安全任務更加艱巨,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要求更加緊迫。”[注:2011年10月15日,在《關于<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的說明》中,李長春也指出:“從一定意義上說,誰占據了文化發展制高點,誰擁有了強大文化軟實力,誰就能夠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在這樣的形勢下,我們必須大力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力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斷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形成與我國國際地位相稱的文化軟實力,牢牢掌握思想文化領域國際斗爭主動權,切實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與西方國家相比,現時軟實力的不足使得中國難以從觀念的維度有效地影響國際法。諸如,西方國家標榜民主、自由等為普世的價值觀,敵視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社會制度。緣此,中國的人權事業雖已取得巨大的進步,但在國際人權法律領域,仍然成為西方國家責難和攻訐的對象;雖然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見證了中國發展模式和經濟制度的巨大成功,但是依西方的新自由主義觀,中國仍然算不上一個市場經濟國家,從而加劇了中國在國際經濟法律領域(如反傾銷、反補貼等)所受的各種不公平待遇;雖然中國擁有“和諧世界”等文化傳統以及長期致力于樹立和平外交的形象,但是西方國家仍然抱守大國崛起必然導致沖突乃至戰爭的舊思維,拒絕接受中國“和平發展”的理念,以至在“中國威脅論”等思潮的左右下,對中國開展的對外活動設置諸多法律障礙,如以國家安全為由限制中國企業的海外并購以及限制對中國的高技術產品轉讓,等等。
如所周知,傳統國際法是“西方文明”的產物,體現的是西方的價值觀,現代國際法的主體雖已擴及世界各國,弱小國家獲得了主權獨立,但是各國之間的文化差異并未因全球化而消弭。借此,西方國家作為文化帝國,仍然株守其所謂的“文明使命”,在國際法領域,實際上繼續復制“文明國家”與“非文明國家”的二元論[5]。
也就是說,現在西方國家的軟實力優勢猶存,國際法仍然浸透著歐洲中心主義,承續著文化上的偏見。時至當代,“國際法雖不再以純歐洲文化之語境來理解,但作為一種秩序化機制的國際法之理念仍然從主流文化中獲取范疇,并沒有脫離其繼續相當程度上控制話語權的文化之語境。像維多利亞時代一樣,當代國際法的辯術仍然得到主流文化觀念的支持。”[6]
這里所謂的“主流文化”指的就是西方文化。
從歷史上看,西方國家軟實力的提升與硬實力的增長基本上是同步發生的,軟硬實力經由利益和觀念兩大緯度“雙管齊下”,同時影響國際法,且其中軟實力的存續通常具有穩定性,哪怕硬實力絕對或相對衰退,西方國家軟實力對國際法觀念之維度的影響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仍可維持。與西方國家的經歷不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硬實力通過利益之維度對國際法的作用趨于加強,但軟實力經由觀念之維度對國際法的影響卻仍然有限。
(二)具體對策
盡管有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學者相信中國文化終將統治世界[注:例如,在2009年出版的《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衰弱》一書中,英國學者馬丁?雅克給出了這樣的邏輯:中國崛起指日可待,從而以一種迥異于西方文明模式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并必然導致西方文明的衰弱與終結,整個世界將不得不按中國的文化進行重組,最終會形成“中國文化霸權”的人類文明格局。雅氏反復指出:“中國最有可能實現霸權的領域還是文化。”“中國崛起為世界大國后,很可能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在文化等方面完全改寫世界秩序。”“認為中國對世界的影響主要體現在經濟方面,實在有些過時,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可能也會產生無比深遠的影響。中國未來給世界帶來的影響,將可與20世紀的美國媲美,甚至有可能超越美國。”(參見:馬丁?雅克.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衰弱[M].張莉,劉曲,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923,13.)又如,金舜權、戴維?菲德勒和蘇米特?甘他古利也撰文指出,實力固然重要,但國家間政治還涉及理念的競爭。隨著中國及印度作為大國崛起,東方理念有不斷輸出亞洲之外國家(如非洲)的趨勢,可能會最終取代西方主導的、延續數百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后威斯特伐利亞”之普世價值,形成新的“東方利亞體系”。(參見:S. W. Kim, D. P. Fidler & S. Ganguly. Eastphalia Rising? Asian Influence and the Fate of Human Security[J]. World Policy Journal,
2009,26(2):53-64.)],一些西方國際法學者也對中國價值觀傳播,從而在將來挑戰西方國際法文化的霸權主義憂心忡忡。例如,芝加哥大學的小波斯納在論及中國崛起與國際法之間的關系時指出,在中國,“現在還沒有贊美資本主義和拒絕民主的任何哲學,然而,當中國需要一種意識形態在美國的敵人中進行動員以爭取國際支持時,也許這樣的哲學就出來了。”[7]
然而,中國要在短期內徹底改變自己軟硬實力大小不平衡的狀況,實際上是難以做到的。在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在短短的30多年時間里硬實力得到如此快速的增長。然則,無論如何,軟實力的提升不可能速成,需要一個比較長的建設周期,此其一。其二,構成中國軟實力因素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民族文化以及外交方針等具有超強的穩定性,中國不可能通過改變這些因素去迎合西方國家的價值觀。在保持這些軟實力因素不變的前提下,要加大它們對其他國家的示范力、吸引力和說服力,即進行軟實力的對外投射,并非易事。面對軟硬實力大小不均衡將長期存在的現實,中國應通過利益和觀念兩大維度在國際法律過程中盡量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
1. 軟硬實力大小不平衡與中國對不同領域國際法律制度的選擇問題
國際法雖兼具利益和觀念兩大維度,但不同領域國際法律制度體現這兩大成分的比重卻存在差異,相應地,軟硬實力的影響情形也不盡相同。其可大別為三類:一類是側重于追求利益的國際法律制度,如國際經濟法等。此類國際法律制度側重于追求利益而不是實現觀念,故硬實力對其影響比較大,軟實力的影響則比較小。二是側重于實現觀念的國際法律制度,如國際人權法等。相反,就此類國際法律制度而言,軟實力的影響比較大,硬實力的影響則比較小。三是比較平衡地反映利益和觀念的國際法律制度,如國際環境法等。既然如此,對此類國際法律制度,軟硬實力的影響可能難分伯仲。
隨著中國硬實力的提升,中國在國家間利益分配過程中的信心和能力不斷得到加強。從整體上而言,一項國際法律制度越側重于利益之維度,對中國就越有利。鑒此,中國應更加積極主動地參加此類國際法律領域的活動,并充分發揮自己在硬實力上的比較優勢。例如,在WTO中,中國扮演的角色越來越積極,所發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時任中國常駐WTO大使孫振宇曾總結認為,從“入世”后的經歷來看,“中國已從略顯稚嫩的新成員一步步成為一個成熟的、負責任的重要成員,并成為WTO核心圈的一員。”[8]
又如,2011年,中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中所占的份額從原來的第六位上升到了第三位,中國在這兩大主要國際經濟組織中的決策權也得到了相應的提高。
相反,在中國軟實力對國際法觀念之維度的影響尚屬不足的情況下,一項國際法律制度越側重于觀念的實現,對中國就越不利。例如,在西方價值觀主控的國際人權法律領域,中國一直處于不斷受到西方國家打壓的困境。在觀念主導的這些國際法律領域,中國應特別注意自身軟實力的打造及發揮,以便最大限度地影響相關國際法律過程中的價值維度。另一方面,中國也要徹底揭露西方國家隱藏在其“華麗”價值觀背后骯臟的利益,盡量將對自己不利的觀念沖突轉化為對自己更為有利的利益對抗,進而引入自己的硬實力抗衡西方國家。例如,在西方國家打著維護人權之普世價值的旗號試圖干涉中國內部事務之時,中國不但要抨擊西方國家奢談人權的虛偽性,而且要揭示其行動背后不想告人的私利,從而名正言順地依靠硬實力維護自己的利益。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國際法律制度的利益或觀念維度具有隱蔽性。因自身軟實力不足而無法有效影響國際法之觀念維度,故在此類國際法律制度中,中國可能仍處于不利地位。
其中的一種情形是,一些國際法律制度表面觀之只重利益之維度,但實際上價值判斷起著很大的作用。例如,人們通常更多地以利益之爭看待知識產權的國際法律保護問題。實際上,就知識產權的保護,存在著私人利益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張力。然而,現行國際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建立在西方國家的“文明”標準之上的,在知識產權“私權論”、“人權論”等西方理念的主導下,私人利益在知識產權的國際法律保護中得到了張揚,公共利益則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壓制;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義輕利”等觀念恰恰具有矯正西方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此等偏頗的功效。但是,由于反映西方國家軟實力的法律文化帝國主義的擴張,使得國際知識產權法中這樣的中國文化元素難以得到有效的體現[9]。
可見,有關知識產權國際法律保護的議題,從利益維度觀察,一開始就是不利于中國的;而深究其隱含的觀念維度,同樣對中國不利。就這種對中國有雙重不利的議題,要格外警惕。一前車之鑒就是,當年發達國家通過“一攬子協議”將知識產權議題納入烏拉圭回合,形成了TRIPS協議,該協議現廣泛地被認為是WTO法律體制中對發展中國家最為不利之一部。
另一種情形是,一些國際法律制度從表面上看只反映了觀念之維度,但其背后實際上卻隱藏著重大的利益之爭。例如,對于勞工標準,人們可能首先視其為國際人權法的范疇,體現的是價值追求。然而,勞工標準的提高會削弱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貿活動中所具之勞動力成本低的比較優勢。因此,就該議題的提出,發達國家有著強烈的內在利益驅動。在中國軟實力尚難以匹敵西方國家的情形下,西方價值觀勝出從而導致勞工標準的過度提高,將會損及中國的經濟利益,這就是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堅決反對西方國家把勞工標準納入WTO多哈回合談判的原因。
2. 軟硬實力大小不平衡與中國對不同國際爭端解決方式的選擇問題
從動態的角度來看,軟硬實力通過利益和觀念之維度影響國際法,實際上影響的是國際法律過程,具體包括國際立法過程和國際爭端解決過程。在國際立法過程中,表現為哪個國家的硬實力越強,制定的國際法律規則就越能體現哪個國家的利益;以及哪個國家的軟實力越強,制定的國際法律規則就越能體現哪個國家的觀念。從表面上看,一旦國際法律規則得到創制,各國之間的利益和觀念分配關系似乎就被這些規則所固化,在國際爭端解決過程中,不再有軟硬實力作用的余地。然而,事實并非如此。
國際爭端有外交解決和司法解決之分,在外交解決方式中,繼續充滿著硬實力的較量。即便當事雙方以既定的國際法律規則為依據談判解決國際爭端,但因這些國際法律規則通常存在著不同程度的模糊性,如何適用和解釋,直接關系到當事雙方的利益,硬實力在其間的影響仍然無法排除。更何況通過外交方式解決國際爭端在法律上不具有“先例效力”,因此,有時不會受到既成國際法律規則的嚴格限制,此時,當事各方的硬實力便依然成為決定爭端解決結果的主要因素。晚近以來,隨著硬實力的不斷提升,在國際爭端的談判解決過程中,中國越來越有能力維護本國的應有利益不受損害,哪怕談判對手是世界上硬實力最強的美國,亦是如此。例如,近年來,美國國內一些議員屢屢施壓,試圖迫使人民幣快速升值,但是,迄今為止,這些施壓對中國均難奏效。
相反,在國際爭端的司法裁判解決過程中,由于裁判者是獨立的第三方,當事各方無法以硬實力對他們施壓。然而,因既成國際法律規則往往存有彈性,故國際裁判者的觀念可能會通過價值之維度影響這些規則的適用和解釋,這就為西方國家發揮軟實力優勢留下了空間。因此,與外交解決方式不同,對國際爭端司法解決起作用的因素更多的是軟實力。應當看到,現行的許多國際法律規則體現的是西方價值觀,而國際裁判者又大多來自西方國家或在西方接受法學教育,西方國家軟實力對他們的影響無疑要遠大于中國軟實力的作用。雖然有關國際條約都規定國際爭端的裁判者應保持司法獨立,即使這些裁判者也愿意如此踐行,但是他們的價值觀實際上無法達到中立。例如,研究表明,文化差異影響國際法院法官對國際法的解釋[10]。
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來自西方國家之法官占據多數的國際法院往往難以取得它們的信任[11]。
那些秉承西方價值觀的國際裁判者因為對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存在漠視、不解、誤讀乃至偏見等,都有可能導致他們做出對中國不利的裁決。
可見,從總體上看,對于國際爭端的解決,中國軟硬實力大小的不平衡可能會造成外交談判比之司法裁判更有利的結果。因此,在國際爭端解決實踐中,中國往往偏好外交談判而不是司法裁判,這并不單純是中國“忌訴”、“厭訴”之傳統文化使然,其本身就是中國的一種理性選擇。有的學者主張,從中國更大程度地融入國際法律體系的需要出發,對于國際爭端的解決,不應基于“實用主義”過于從外交便利考慮,而應更多地接受國際司法解決方式[12]。
我們認為,鑒于中國軟硬實力大小不平衡的狀況,中國不應輕言放棄外交解決方式而盲從國際司法解決。例如,當下在南海問題上,菲律賓之類的國家主張將之提交聯合國國際海洋法法庭裁決,中國應堅決予以反對。
然而,需要說明的是,由于軟實力主要是通過國際法的觀念之維度起作用,當一項國際法律制度側重于追求利益而不是實現觀念時,即使國際爭端的裁判者所持的觀念對中國不利,因這些觀念可用武之地很小,對中國接受此類國際法律領域爭端的司法裁判方式不會構成大礙。例如,WTO協定總體上側重于利益,體現觀念的成分比較小,因此,中國因軟實力不占優勢而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中處于不利地位的情形不會太嚴重。
相反,如果一項國際法律制度側重于觀念,那么,西方的價值觀就會獲得更大的機會通過裁判者輸入法律解釋和適用過程,以致對中國造成大不利的結果。例如,《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屬于國際人權法,中國一貫在原則上支持懲治嚴重侵犯基本人權的種族滅絕罪、戰爭罪、反人類罪和侵略罪,然而,國際刑事法院的法官們在具體解釋該規約條款時,所秉持的多是西方的理念,從而可能導致對該規約的濫用,對此中國不能不防,或許這已成為中國接受該規約的最大一個障礙。現在不斷有學者主張中國應加入《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從人權領域軟實力欠缺之根本考慮,中國應慎之又慎。
三、軟硬實力發揮受限與中國對國際法的影響
中國對國際法影響程度不足的原因除有軟硬實力的大小不均衡外,還源于中國軟硬實力發揮受限之層面。具體言之,西方國家不僅在軟硬實力的構成上對中國占有優勢,而且在軟硬實力發揮之行動上也容易比中國更為有效。
(一)硬實力的發揮與中國對國際法的影響
晚近中國的快速崛起帶來了硬實力的大增,這本該意味著中國通過利益之維度對國際法的影響力也會得到很大的提升。然而,事實上,此等態勢并未充分顯現出來,這與在多邊場合中國硬實力發揮受到限制密切相關。在全球化時代,國際法律過程越來越趨于多邊化,其間,一個國家的硬實力再強,如果僅僅是“單打獨斗”或“孤軍奮戰”,不是以“集團化”的方式行動,也難有勝算。
近代西方世界具有分裂性,主要表現為各個列強都通過瓜分殖民地來建立自己的勢力范圍,以及戰勝國將戰敗國排除在體系之外等。然而,二戰之后建立的國際法律體制以多邊性為基本特征之一,且西方國家將戰敗的德國和日本等統合在內,形成了一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強權聯盟,協同發揮硬實力[13]。
毫無疑義,傳統上,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團結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發揮集體的力量,爭取和維護共同的利益。但即便如此,發達國家集團的硬實力畢竟仍要大于發展中國家集團;而且發展中國家因數量多,在對外采取一致行動時,存在著“集體行動困境”等問題。因此,中國依托發展中國家集團發揮硬實力可能自始就難以在與發達國家集團的抗衡中占據優勢地位。
晚近以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就硬實力而言,如以經濟“總量”計,中國已越來越接近發達經濟體。然而,目前中國人均GDP只有約3 600美元,仍排在世界第100名左右,即從“人均”的意義來看,中國尚屬一個發展中國家。于是,到底是從總量上判定中國為富國,還是從人均上繼續視中國為窮國,已成為近來備受國際關注的一個如何定位中國的問題[14]。
當下中國仍然從人均的角度認同自己為發展中國家,而不愿從總量的角度考慮與發達國家為伍;換言之,中國不可能借助發達國家集團發揮自己的硬實力。
當然,隨著硬實力的快速提升,中國客觀上將越來越接近成為一個發達的大國。這就意味著,中國在總體上與其他一般發展中國家之利益的非相合性將會逐漸加大,相應地,中國依托發展中國家集團發揮硬實力的有效性可能會降低。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作為一個由發展中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快速轉型的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與一般發展中國家級差的出現和拉大,客觀上可能會給發達國家在多邊國際法律過程中實行孤立中國的策略以可乘之機。
例如,在WTO法律體制內,已經出現了依發展程度不同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分級”的傾向。在多哈回合中,就發展中國家“特殊與差別待遇”議題的談判,發達國家主張對發展中國家進行分類,區別對待,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應承擔更多的義務;而某些發展中國家亦認為,較先進的發展中國家不應與他們享有同等的“特殊與差別待遇”。這種“分級”會加速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利益分化,從而損害發展中國家集團內部的團結[15]。
對中國硬實力的運用而言,更是面臨著發展中國家集團利益分化帶來的威脅。在2008年7月進行的多哈回合談判中,中國積極推動和參與其中,并給予其他發展中國家以最大的支持,爭取創造一個“共贏”的結局。然而,最后就農產品補貼問題,美國采取分化策略,對比較貧窮的發展中國家做出了一些妥協,但是拒絕就印度、中國等發展中大國的正當關切做出應有的回應,從而導致談判無果而終。為此,一些認為可從美國的讓步中獲益的發展中國家,將談判失敗的責任歸咎于印度和中國的不合作[16]。
又如,在2009年12月舉行的哥本哈根氣候會議上,一些西方國家明確提出將發展中國家劃分為“先進的發展中國家”和“最脆弱的國家”,并將中國歸入前者,試圖通過操弄概念,把中國擠出發展中國家的陣營。不可否認的是,在這次大會上,發展中國家利益和訴求的分歧確實更多地暴露出來,“77國集團”加上中國的談判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增加了中國與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協調談判立場的難度[17]。
面對西方國家分化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合作關系的圖謀,中國更加需要在求同存異的基礎上,努力與發展中國家共進退,協同發揮硬實力,否則,中國就會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被動窘境,淪為西方國家所稱的歷史上“最孤獨的大國”。但是,在發展中國家陣營內部,因發展水平級差的客觀存在,當中國硬實力的運用確實無法得到更多的一般發展中國家策應時,中國可以聯合利益與自己相近的其他新興國家,共同影響多邊國際法律過程。例如,2009年以來,金磚國家領導人已經舉行了三次峰會,共謀在國際關系中的話語權。又如,2009年12月,由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四個新興大國組成的“基礎四國”,互相支持,在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上演了一場配合默契的“男聲小合唱”,顯示了巨大的影響力。
另者,在多邊國際法律過程中,如果中國無法有效地整合集團的力量發揮自己的硬實力,
應積極拓展在雙邊的和區域層面施為的空間。顯然,較之于多邊場合,在“一對一”的雙邊情形下,更能發揮中國硬實力的效用。在雙邊國際法律過程中,中國已經相當強勢,有能力維護自己應有的利益。例如,在與發達國家談判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的過程中,中國就有效地固守住了自己立場的底線。又如,在南海問題上,中國不但反對像菲律賓這樣的國家昭示的以國際司法方式解決之意圖,而且反對將之訴諸多邊外交場合,主張采取雙邊的方式解決,以有效地維護自己的海洋權益。與此同時,在區域范圍內,中國也有更大的可能發揮自己硬實力的比較優勢。例如,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中國的影響力得到了應有的顯現。又如,近年來,中國大力開展對外談判締結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活動,成效顯著,與相關國家實現了“共贏”的目標。
有的西方學者認為,現行的多邊國際制度統合了西方國家的整體實力,即便中國崛起,日后硬實力超越美國,也無法推翻西方國家主導的既有多邊國際制度。但是,為了防止中國建立自己的聯盟,應該讓中國接受多邊國際制度的約束,并抑制中國發展雙邊和多邊的國際制度[13]34-35。西方學者的這種主張恰恰從反面印證了中國積極利用雙邊的和區域性途徑發揮硬實力的必要性。
(二)軟實力的發揮與中國對國際法的影響
中國軟實力通過觀念維度影響國際法,不但存在著軟實力不足的問題,而且無論是在國家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軟實力之對外投射效用在客觀上也仍不及西方國家。
其一,在國家層面,中國軟實力對國際法之觀念維度的影響尚難擺脫西方強勢文化的集體壓迫。
西方國家的意識形態、國內制度、文化傳統等具有相當大的同質性,相互之間在軟實力上能夠形成一體,合力打造影響國際法之觀念;亦即,西方國家立基于“基督教文明”,往往可以做到合創、同守和共促國際法的價值觀。
許多西方學者認為,國際法律秩序的建立必須依托文化普世主義,實際上就是主張西方文化應在國際法中獨領風騷;而發展中國家學者普遍支持文化相對主義,強調弱小國家的文化在國際法中也應占有一席之地[18]。
在面對西方國際法文化帝國主義侵襲時,處于各種弱勢文化的發展中國家因有著共同的被壓迫命運,會群起共御。由此,如屬這樣的情形,中國軟實力的發揮往往可以爭得其他發展中國家之襄助。例如,上世紀90年代之后,在原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中,中國曾十余次挫敗西方國家的反華提案,依靠的就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
然而,由于非西方文化的多樣性,許多發展中國家分屬不同種類的文明,社會歷史傳統等有著相當大的差異,而且“事實上,發展中國家近年來正加速呈現‘大分化態勢。除‘歷史經歷大體相同和‘多數國家經濟和政治上仍處于弱勢地位兩大因素外,發展中國家的共性在減少,差異性增多。”[17]就中國而言,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等無不具有中國特色,中華文化的傳承和性格也相當獨特,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在具體價值觀上的非相合性客觀存在。因而,在國際法律過程中,中國如果不只是消極地抵御西方的價值觀,而是要積極地以自身的價值觀塑造國際法時,可能就會處于勢單力薄的狀態。
在國際法律過程中,雖然有時發展中國家也能集體發揮軟實力,合成一些共同的價值觀念,聯合構建集團的法律文化,但這方面的作為仍然是有限度的。例如,在國際人權法領域,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提出了“發展權”的概念,并強調集體人權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與關注個人權利和政治、公民權利的西方人權觀相對壘。盡管如此,中國與非洲國家、伊斯蘭教國家等之間在人權文化上的差異仍然存在[19]。
例如,中國企業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投資,出于工期緊等原因,往往要求當地雇員加班工作,即使給予額外的報酬,仍然容易引發勞資糾紛,從深層次上分析,這反映了中國與其他有關發展中國家之間在勞工標準上的理念分歧。
對于仍然充滿著西方單一文化的國際法,有的發展中國家學者不是像上世紀50-60年代發展中國家革命時期那樣主張與西方文化的對抗,而是主張跨文化對話,將反映世界各大文明的文化多樣性輸入國際法,從而推動國際法的“普遍化”過程。[注:參見:C. G. Weeramantry. Universalising International Law[M].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2004:1-31.作者為斯里蘭卡籍國際法院大法官。]應該說,通過文化滲透這種溫和的方式逐步加大發展中國家弱勢文化對國際法的影響,其本身對中國是有利的。但是,這種改良方式的倡導者并未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路徑,而且無論如何,這是一個長期的作用過程,在這期間,國際法仍然是一個缺乏多種文化營養的慢性病體。
即使以激進自由主義為根基的西方國家之“華盛頓共識”也已告失敗,但是作為中國的一種成功發展道路——“北京共識”能否最終被發展中國家廣泛接受和吸收,以聚合此等軟實力影響相關的國際法律制度,還有待觀察。有的外國學者認為,中國的發展道路“深深地根植于中國社會的諸多傳統,具有鮮明的中國特點……也正因如此,中國模式很難輸出。”[20]
假如中國過度強調“中國模式”的投射,“強人所難”,未必對自己有利。[注:例如,2009年12月9日,李君如、趙啟正、施雪華、邱耕田等四位重量級作者分別在中共中央黨校主辦的《學習時報》第515期上撰文,主張慎提“中國模式”這一概念。]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如前所述,隨著中國的迅猛崛起,在國際法律過程中,就利益之維度,中國與一般發展中國家的非相合性可能會加大。由此,容易引發人們對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之間長遠關系的擔憂。然而,應當看到,決定這種關系的不完全是利益的考量,還有觀念的維度。雖然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難以普遍地形成統一的具體價值觀,但在基本價值觀上往往并無二致,尤其是在共同抵御強勢西方文化試圖主宰國際法的過程中,共同合作和相互支持將是長期的和可靠的。更為重要的是,按照建構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觀念將會在整體上影響利益的取向。在如何對待發展中國家的問題上,無論是現在,還是將來,中國都不可能膜拜見利忘義的純理性選擇模式,罔顧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利益,而是會以自己特有的“利以義生”、“見利思義”等固有價值觀來約束自己利益的取得。
其二,在社會層面,中國軟實力對國際法之觀念維度的影響受到了市民社會不發達的制約。
軟硬實力的一個重要不同之處在于,硬實力的發揮基本上為國家所壟斷,而軟實力的推進主體除了政府之外,還有社會力量的廣泛介入,特別是非政府組織的參與。
西方國家軟實力對國際法律過程的影響不僅經由政府,來自西方社會的非政府組織已成為越來越重要的軟實力對外投射載體。據統計,國際非政府組織已從1972年的3 733個,發展到2003年的49 471個[21],
其中大部分分布在西方世界。這些非政府組織雖然標榜、因循普世的理念,但是實際上側重顯現的是西方的理念,而不是代表發展中國家的優先價值。例如,非政府組織會通過游說乃至社會運動的方式力挺勞工標準和環境保護等社會議題進入WTO,而這些社會議題一旦“入世”,非政府組織又會通過“法庭之友”等途徑影響WTO爭端解決機構對有關糾紛的裁決。事實上,無論是在WTO的立法過程之中,還是在WTO的司法過程之中,許多非政府組織都存在著過度代表西方價值觀的傾向。在國際經濟法律領域尚且如此,遑論在觀念占據主導地位的國際人權等法律領域,諸多非政府組織往往成為西方國家對弱小國家實行人道主義干預的推手。
目前,在軟實力的對外投射方面,中國基本上仍由政府主導,尚未形成政府與社會力量“兩條腿”走路此等更為有效的機制。尤其是中國的非政府組織還不發達,向世界傳播中國價值觀的社會聲音相當微弱,對國際法律過程幾無影響。這可能與中國歷來認為“外交無小事”的傳統觀念有關,以致對非政府組織參與國際法律過程持非常審慎的態度。其實,有時以政府為主體來推行軟實力,更為敏感,甚至可能產生干涉別國內部事務之嫌疑,而經由非政府組織對外投射軟實力,因它們號稱代表的是普世的價值觀,更容易為國際社會所關注和接受[22]。
2011年10月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應“開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層次對外文化交流,……增強中華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響力,共同維護文化多樣性。創新對外宣傳方式方法,增強國際話語權……”
鑒此,中國應重視培育和發揮民間力量對軟實力的推進作用[23]。
長期以來,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中國被認為是政府主導型的,西方國家在處理與中國的國際法律事務時,通常只把焦點聚集在中國政府。然而,中國有13億人口,如能充分顯示民間力量對中國意識形態、政治經濟社會制度、發展模式以及外交方針等軟實力構成因素的普遍認同和支持,則可以在國際法律過程中,通過觀念的維度對西方國家形成強大的壓力。例如,在2009年底召開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天津會議上,60多家環保領域的中國非政府組織首次亮相國際舞臺,共同發布立場,呼吁各國直面氣候變化挑戰,盡快通過談判達成協議。在2個月后的坎昆世界氣候變化大會上,中國的這些非政府組織再次活躍于會場內外,與中國政府、媒體及企業一道,向國際社會展示中國各階層的低碳實踐,加深了國際社會對中國低碳發展狀況的了解,以自己的方式更深、更廣地參與到國際氣候變化談判中。
四、結論
晚近以來,中國迅猛崛起,但是中國對國際法影響力的提升速度遠滯后于中國整體實力的增長速度。造成這種反常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從軟硬實力的構成和發揮上判斷,中國仍然只是一個“大國”,尚難以稱得上是一個“強國”。具體而言:
一是軟硬實力大小的失衡使得中國無法有效地影響國際法的觀念維度。要扭轉這種不利局面,有待于中國軟實力的大幅提升,但這絕非一日之功而能成就。雖然如此,在國際法律過程中,中國仍然可以根據軟硬實力作用的機理,通過利益和觀念兩大維度盡量做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包括要注意分清哪些是硬實力起主要作用的、傾向于追求利益的國際法律領域(如國際經濟法)和哪些是軟實力起主要作用的、傾向于實現觀念的國際法律領域(如國際人權法),以使自己的行動更加有的放矢。此外,中國應更多地選擇可有效運用硬實力的外交方式解決國際爭端,而不是盲目地擴大使用受軟實力影響的國際司法解決方式,等等。
二是軟硬實力發揮的受限制約著中國通過利益和觀念兩大維度影響國際法。在多邊場合,總量上富國和人均上窮國之混合身份可能使得中國難以“一邊倒”地依靠集團的力量運用硬實力對國際法律過程產生影響。鑒此,中國應重視以“中間人”之角色發揮硬實力的獨特方式。同時,中國應盡量拓展可增強硬實力發揮效用的雙邊和區域性空間。在軟實力的發揮上,中國可以依靠發展中國家的支持,抵御西方的國際法文化帝國主義,但應清醒地認識到,中國主動地以自己的價值觀塑造國際法律規則時,可能會面臨發展中國家集團軟實力難以聚合的問題,“強人所難”,有時未必于己有利。在社會層面,中國需重視培育和發揮國內民間力量來對外投射中國的軟實力,在國際法律過程中與西方國家非政府組織的影響相抗衡。
お
參考文獻:
[1]J. deLiselě. Chinas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J].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2000,(94):273-274.
[2]A. Hasenclever, P. Mayer & V. Rittberger.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104-113.
[3]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上)[J].國際觀察,2007,(2):20.
[4]邱永崢.未來十年,中國將面臨哪些挑戰[N].環球時報,2009-07-24(19).
[5]A. Anghie.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1-12, 310-320.
[6]A. Riles. Aspiration and Control: International Legal Rhetoric and the Essentialization of Culture[J]. Harvard Law Review, 1993,106(3):738.
[7]E. A. Posner & J. Yoo.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se of China[J].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6,7(1):12.
[8]劉國遠.中國駐世貿組織大使孫振宇:“中國逐漸進入世貿組織核心圈”[N].參考消息,2008-12-25(14).
[9] 魏森.法律文化帝國主義研究——以中國知識產權立法為中心[J].法商研究,2009,(3):120-129.
[10]A. D. Renteln. Cultural Bias in International Law[J]. 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Proceedings, 1998, (92):236-237.
[11]王鐵崖.第三世界與國際法[G]//鄧正來.王鐵崖文集.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57.
[12]Pan Junwu. Chinese Philosophy and International Law[J]. As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2011,1(2):238-240, 245-248.
[13]G. J. Ikenberry.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 Can the Liberal System Survive?[J]. Foreign Affairs, 2008,87(1):28-29.
[14]J. Kynge. Chinas Growth Dictates Fresh View of the World[N]. Financial Times, 2009-11-20(11).
[15]林靈.試析多哈回合“特殊與差別待遇”談判及中國相關立場[J].武大國際法評論,2007,(7):100,106-109,111-113.
[16]約翰?W?米勒.中國稱其有權設置高關稅[EB/OL].[2011-10-15].http://chinese.wsj.com/big5/20080729/bch133430.asp?source=whatnews1.
[17]佚名.中國要與發展中國家共進退[N].環球時報,2009-12-21(14).
[18]R. Mushkat. Culture and International Law: Universalism v. Relativism[J]. Singapor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 Comparative Law, 2002,6(2):1030-1031.
[19]C. Joyner & J. Dettling. Bridging the Cultural Chasm: Cultural Relativism and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aw[J]. California Western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1990,20(2):286-289.
[20]恩里克?凡胡爾.北京共識:發展中國家的新樣板?[N].參考消息,2009-08-19(16).
[21]Anna-Karin Lindblom.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in International Law[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19.
[22]門洪華.中國:軟實力方略[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155-157.
[23]沈澤瑋.中國軟實力傳播文化 應去“官方化”走“民間化”[N].聯合早報,2011-02-05.
Hard & Soft Competencies and Chinas Impact upon International Law
XU Chong瞝i
(Law School of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influence exerted by China upon international law is still limited, which is quite inconsistent with the unprecedented rise of such a big country. The reason of the abnormality lies mainly in the unbalance of Chinas hard and soft competencies and their constrained exercises, and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can never be reached in a short rime. However, in the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law, China should, in light of her own hard and soft competencies and by way of changing her viewpoints of values, try her best to make choices to gain maximum benefits.
Key Words:rise of China; international law; competency; soft competency; hard compete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