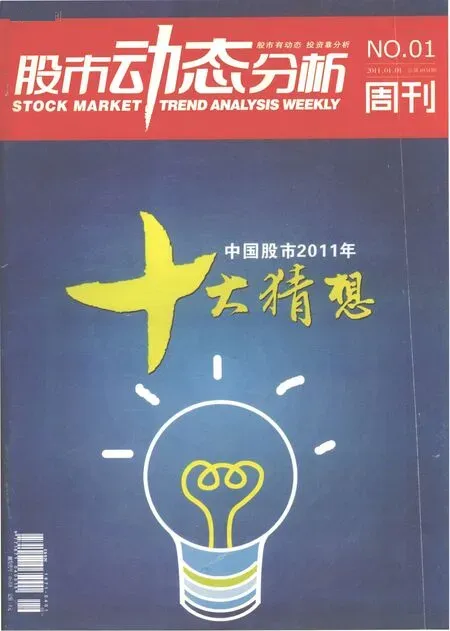高價發行不能全怪基金
鐘林
滬深交易所兩位老總在上個月2日深圳的一個金融論壇上,罕有的同時炮轟公募基金在IPO發行中的瘋狂詢價行為。上交所老總稱:“很奇怪,基金公司80倍的(發行)市盈率可以接受、90倍的市盈率可接受、150倍的市盈率也可接受,到那么高你怎么可以接受呢?”由此引發市場對公募基金系列荒誕行為的大討伐。
2011年以A股二級市場的大熊市而凄慘告終。簡而言之就是“一級市場發得太貴,二級市場輸得太慘”。股市熊得太厲害之后,極易引發投資人諸多的憤恨至極,證監當局本身就是被炮轟的主要目標。滬深交易所老總是次對公募基金的泄憤,在客觀上也有轉移市場焦點之嫌,試圖讓市場的怨憤轉移到公募基金那邊,因為二級市場上到處都是討伐證監會的怒吼。
多數輿論都認為交易所老總的炮轟很解氣,似乎找到了自2009年7月IPO第二次改革以來,市場持續出現“三高”亂象的癥結。但筆者以為這恰恰是一大誤區。滬深交易所的老總,憑什么可以將“三高”的罪名嫁禍于基金呢?
2009年7月后出臺、經過改革后的新發行制度,采用的是“荷式競價法”:最終的新股發行定價,是以入圍眾機構中的“最低價”來決定。只要你入了圍,只要最終入圍的最低價是15元/股,那么就算是先報出了60元/股的機構,最后還是按照15元/股來認購新股,根本不需要支付其申報時的高價。
這種制度的優點在于鼓勵“競價”,消除了過去機構曾經合謀壓低發行價的漏洞或弊端,但是同時又是變相鼓勵機構報高價,否則就無法獲得新股“配額”。任何有資格參與詢價的機構,只有其報價先“入圍”,后才有資格獲得配售新股;加上所有基金的資金都是基金持有人的,而不是這些基金經理自家的,他們完全就是毫不心疼的胡亂報價。直接導致所有這些亂象最后的禍根,還在IPO的這套制度、以及決定該制度的證監會那邊,上交所老總怎么會忘記了自己的江湖身份呢?
基金在IPO詢價中胡亂報高價,當然有其可恥與該討伐之處。因為他們的這種瘋狂,直接扮演“新股不敗”的丑惡推手。新股長期毫無節制的狂發,至少在二級市場,已經釀成天怒人怨,并被視為A股長期走大熊市的禍首之一。
IPO狂發,市場的流通市值爆增,卻演繹出幾大悖論。一方面,是二級市場對IPO無節制發行的憤怒;另一方面卻又是一級市場有數以萬億元計的“打新”資金,在長時間盡享打新股的快速暴利。包括所有商業銀行都開設有專門打新的、美其名曰“新股申購理財產品”的專門賬戶,并極力動員和招攬旗下萬千儲戶將其存款轉為認購新股的專項資金。
原因之二,就是擔任新股IPO詢價主角的公募基金,完全沒有起到好的作用,即沒有起到為新股“合理定價”的作用。基金公司專門享有在“網下”大筆申購新股的“特權”,他們不需要參與網上申購和競爭,就有權得到大把的新股,這是證監會為大力扶植基金這個機構投資者所給予的特權。
因為新股的炙手可熱、發行市盈率和發行價高企所形成的“新股不敗”,享有打新特權的基金,不論其每年的股票投資收益如何,僅每一次打新股的收益累積下來就相當可觀。利益關系決定了所有這些基金公司必定要把新股定價拉高,為自家牟利,此乃其一;
其二、基金的資金全部都是來自其持有人的認購。因為基金既要在一級市場申購新股,又要在二級市場買賣股份,如果遇到長期熊市和新股因過份高估而屢屢破發之時,基金在二級市場買入的新股,往往會令自家虧蝕。但證監會的硬性規定是,基金公司每年提取的巨額管理費,是不論其投資業績虧盈的旱澇保收。這種奇怪的制度決定了基金經理們對投資人的資金毫不吝惜和在意,亦直接導致其不惜在IPO詢價中亂報高價。
其三、在IPO詢價中亂報高價,基金涉嫌對發行人、對承銷中介的利益輸送,加上“人情”面子關系。因為股市這個圈子本身并不大,很多人在進入基金之前,就在證券、保險或上市公司打滾,彼此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其四、因為目前詢價中采用的“荷式競價法”,本身亦限制了報低價的行為。有很多實例證明,曾經報過低價的公募和私募機構明顯被邊緣化、或被直接逐出山門,被隱性取消詢價資格。因此,基金必須報出高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