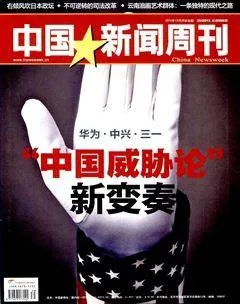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口
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不是“均貧富”,更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我們要承認合理的收入差距,需要解決的是因體制不公導致的市場機會不均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說,我們詬病的是機會的不平等,而不是結果的不平等。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即將登臺亮相。10月17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時表示,第四季度將會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總體方案。也就是說,一項醞釀8年之久的改革終于有了最終的時間表,值得期待。
收入分配改革從2004年開始啟動調研,2009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傳出調整收入分配改革的信號。2010年全國人大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專門論述“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這是《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隨后,改革總體方案的時間表幾經敲確,又一再推遲公布。這項改革之所以如此難產,是因為它涉及中央與地方、政府與企業、群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是一項極其復雜、敏感的重大改革,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
每個時代都有其特定的改革使命。30多年來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打破了權力主導下的大鍋飯式公平,提高了民眾的生活水平,推動國家財富的蛋糕越做越大。但與此同時,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產生收入差距的根源是什么?這當然不是改革帶來的副產品。從理論上講,可歸結為“公平”和“效率”之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收入存在差距是必然的,不可避免,但收入差距過大,政府則負有不可回避的責任。
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11年,中國居民收入增長遠遠低于財政收入和企業收入增長,使得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相對比重不升反降。經過國家統計局數據測算,2011年中國公共財政收入10.37萬億元,增長近25%,增幅分別是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義增幅的1.76倍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名義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業收入增長幅度為20%左右,也遠高于居民收入。這充分說明了,在初次分配中,政府、企業和勞動者分配失衡。
在中國現實情況下,由于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的改革還沒有到位,再加上戶籍制度帶來的就業求學的機會不均等、壟斷部門坐豐厚利、行政壟斷大量滋生“灰色收入”等因素,導致二次分配不是彌補一次分配的不足,而是擴大了一次分配的差距。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對部分地區的調研顯示,有的地區一次分配結果城市和鄉村的收入差距是2.9:1,二次分配后達到3.4:1。
解決收入分配差距的辦法不外乎一次、二次和三次分配。在當下中國,缺少慈善文化,加上企業家們和富人群體剛剛建立起來,財富的基礎還不扎實,指望第三次分配,也就是通過慈善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是不現實的。因此,出路還是在一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上。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雖然遲遲沒有公布,但從透露的信息來看,“提低、擴中、控高”的主線,也即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擴大中等收入階層,限制高收入群體的收入增長過高是改革的主要政策基調。在這方面,政府一直是有所作為的,如廢除農業稅、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等等,但為什么差距的鴻溝沒有縮小而仍在不斷擴大?這是因為,收入分配問題不僅僅是收入的分配一它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背后是科學發展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問題。
首先,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不是“均貧富”,更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我們要承認合理的收入差距,需要解決的是因體制不公導致的市場機會不均等而造成的收入差距,也就是說,我們詬病的是機會的不平等,而不是結果的不平等。
再者,收入差距的產生,其根本在于政府、企業和勞動者分配的失衡,因此,政府和企業應該讓利于民。最有效的是政府財政收入通過轉移支付投入民生領域,可以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在教育、醫療衛生、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四項領域,中國2003年的財政支出占收入的20%,2011年達到30.6%,而美國2001年至2011年。四項支出財政收入占52%,日本是63%,中國臺灣是53%,北歐更高。從這點看,中國財政在民生領域的投入仍遠遠不夠。
但僅僅加大財政在民生領域的投資還不夠,另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是打破國有企業行業的壟斷,引入充分的市場競爭,同時加快服務業和扶持中小企業的發展。中小企業在帶動就業方面確實發揮著重要作用,提供了80%以上城鎮就業崗位。而充分的就業是提高收入分配的前提,也是“提低、擴中”的基本。
10月18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擴大營業稅改征增值稅試點工作座談會上強調,以結構性減稅推動結構調整與改革,以營改增為重要抓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助推工業創新轉型,加快服務業和中小企業發展,改革與完善財稅體制。
可見,啟動財稅體制改革已達成社會共識,條件也最成熟。我們期待著啟動財稅體制改革,以破解收入分配體制改革,最終使收入分配改革提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