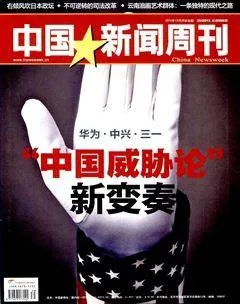不可逆轉的司法改革

從十五大開始,近十五年的司法體制改革,特別是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領導下進行的改革,為滿足人民群眾對于司法公正的需求,進行了艱辛探索,付出了大量心血,也收獲了不少成果。盡管這些改革均是在憲法框架內進行,是在落實憲法的精神、保證憲法的實施,但由于習慣思維和體制機制障礙,外部對于司法的干預始終無法消除,嚴重影響司法公正削弱司法權威。但司法改革不可逆轉。即將召開的中共十八大將對司法體制改革提出新的部署和更高要求。
10月9日發布的《中國的司法改革》白皮書發表令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徐昕感到一絲欣慰,他對《中國新聞周刊》說,“這表明了中國致力于推進依法治國和司法改革的態度和決心”,在他看來,白皮書的發表亦“使司法改革的重要性回到了民眾的視野”。
三年前,正是出于喚起民眾對司法改革重要性的了解,當時還在西南政法大學任職的徐昕主持發布首份《中國司法改革年度報告(2009)》,這個工作一直持續到今天。2012年的報告也正在起草中。
每年度的報告最終定稿都達到三四萬字,門下研究生廣泛參與,所有的修改最后都送到徐昕手上統籌,修改不下百次,“目的就是希望藉此引起官方重視,形成推動司法改革的‘官民合力’”。
“官民合力”促改革
第一份報告發布時,這種效果就開始逐漸顯現。在與正義網合辦的發布會上,除了知名學者,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改辦的官員亦有參加。
發言中,最高人民檢察院理論研究所副所長向澤選一開頭就說,“拿到這個報告翻了一下,重點看了一下檢察改革篇,有一個總體的印象就是這個篇幅好像有點少。”時任最高人民檢察院司法改革辦處長高景峰對這一點表示“很有同感”。
向澤選特別強調,“檢察改革應當說2009年還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徐昕則回應稱,報告還會做進一步的完善,并在正式學術刊物上發表。
來自檢察系統官員的敏感從側面表明了司法改革過程中在司法系統內部對權力配置的敏感。向澤選甚至細致到某些具體的文字,“也看了一下法院的改革篇,我建議這里面有一些措詞,課題組再斟酌一下。”
向澤選所指法院改革篇“主題用的是法院改革”,卻在“優化司法職權配置”中“把司法和檢察并列”。他直言不諱地說,這樣“容易讓人誤以為檢察權不是司法權。建議在法院改革篇相關部分使用優化審判職權配置,這樣更符合中國的憲政體制”。
徐昕當時就意識到,這個報告旨在形成互動的作用正在發揮出來。
高景峰承認,檢察改革篇幅偏少,“責任可能不在課題組,因為我們在搞司法體制改革研究的過程中一直堅持一個原則,這個原則不是我們制訂的,是多做少說,或者是只做不說”。
會后不久,徐昕意外地收到最高檢察院相關部門寄來的資料,包括當年度的工作總結,資料較之網上信息更為全面完整。“可以說,除了涉密的內容被刪掉之外,其他的都有。”
“說意外,是因為在起草報告的時候也聯系過,不過一直沒有下文。”徐昕由此感慨,中國的事情還是要努力往前推,或許就會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此次會議后不久,最高檢察院在《檢察日報》發布了長篇的《中國司法改革報告·檢察篇》。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首次公開發布了《人民法院年度報告(2009)》,此后一直堅持。此外,最高法院亦就如知識產權等領域的審判工作發布專門的報告。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蔣惠嶺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像司法公開這樣的問題,不是說時機成不成熟,而是必須推進的問題。”
回歸司法屬性
然而,發布會召開時的背景顯然比發布會的討論復雜得多。當時,包括強調司法的人民性、調解優先等一些新的司法理念被提出來,歷史上著名的馬錫五審判方式(抗日民主政權創立的一種將群眾路線的工作方針運用于司法審判工作的審判方式,主要內容是簡化訴訟手續,實行巡回審判、就地審判)也重新得到重視。
一些新的做法比如“放下法槌脫下法袍”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河南高院院長張立勇就質疑,“一定要像西方法官那樣戴著頭套,穿著法袍,在高堂上一槌才是好的嗎?”他建議法官改穿制服,“你要穿法袍就和群眾保持距離了”。
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張立勇說:“馬錫五審判方式在當時非常有效、管用,到今天仍然有很現實的意義。可能在上海、深圳這樣的大城市不需要推廣馬錫五審判方式,它沒有田間地頭,但我們認為在河南這樣的農業大省,在我們國家的許多地方,仍然是十分有效的”。
各種理念交鋒激烈,部分學者據此批評說司法改革缺少共識。當時甚至有人認為,“司法改革在走回頭路”。
實際上,大規模的司法重建與改革早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已開始。隨著對四人幫的審判和律師參與辯護,此后影響深遠的公開審判制度和辯護制度被重新建立起來。蔣惠嶺認為,“法制重建,法院、檢察院等司法系統重建,這是適應改革開放需要,也可以說是國家在政治民主化的一個必然選擇。”
1983年《法院組織法》和《檢察院組織法》做了比較大的修改之后,中國的司法制度相對穩定下來了。
蔣惠嶺回憶,改革開放之前,刑事案件居多,民事案件主要是婚姻家庭和債務。但是上世紀80年代中期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的多樣化,《民事訴訟法》出臺,社會對司法的需求以非常快的速度在上升。
在這個階段,審判方式改革被提出來。“機構重建起來,人員到位,案件進入法院后,法院以什么樣的方式,什么樣的態度來對待這些案子,怎么去工作呢?訴訟法寫得很清楚,但是怎么把紙上的東西變成法庭里活生生的程序?”蔣惠嶺說,審判方式改革由此開始。比如,證據制度的改革,庭審一步到庭的改革。
行政訴訟制度也在這個時期建立起來。“民告官”逐漸為各地所接受,到1989年《行政訴訟法》最終頒布。
“這個時期的改革使得全國司法機關向社會展現了司法的規律性,回到司法本身的屬性上來。”蔣惠嶺的判斷是,“任何的司法改革都是基于對現實的回應、對需求的回應才發展起來的,在上世紀80年代的中期,國家的司法建設經歷了一個有活力的、上升的時期。”
上世紀90年代之后,十四大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當時流行的一句話“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對法治的需求被進一步提出來。1995年《法官法》和《檢察官法》通過,1996年《律師法》出臺,司法的獨特性被進一步展現出來。
而1996年《刑事訴訟法》的修改,“疑罪從無”原則被寫入法律,則被看成是司法改革領域的重大進步。
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回憶,“‘疑罪從無’是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最后時刻寫進去的。”因為一次單獨面見高層領導的機會,陳光中力陳這個制度的優點,并直接促成寫入草案。
整體統籌、有序推進
1999年《人民法院第一個五年改革綱要》(以下簡稱《一五綱要》)出臺,提出一系列的改革,其中就包括司法人員職業化的改革步驟,提出把法官和普通的公務員區別開來,并且提出法官的工資制度要由國家另行規定。
作為司法人員職業化的重要改革,國家司法考試在新世紀之初被統一起來,原來分割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資格考試被合而為一,法律職業共同體成為法律人共同的夢想,北京大學強世功教授甚至推出《法律共同體宣言》來描繪法律人的使命。
然而,在真正的改革中,法律共同體仍然只是理想,作為法律共同體之一的檢察系統和檢察權面臨著現實的質疑。
國家檢察官學院院長石少俠回憶,從上世紀90年代一直到2002年,對于檢察權的改革主要有兩種觀點,“一是主張另起爐灶、推倒重來,學習英美。對現行的檢察制度從性質、地位到具體的權能全盤否定,甚至主張取消檢察院;二是主張堅持現行制度,改革體制弊端,完善制度建設。”
不僅僅是對檢察權,其他領域的問題也開始顯露,比如鐵路公檢法的問題逐步暴露出來。
鐵路公檢法由于人事財務受控于鐵路部門,存在較嚴重的部門保護主義和企業本位主義,涉鐵案件中偏向鐵路部門的司法不公問題尤為突出。例如,列車長黃建成將疑有精神病的農民工曹大和捆綁致死只被判死緩,16位公民聯合上書全國人大要求對鐵路司法權進行違憲審查,集中反映了民眾長期以來對鐵路公檢法的質疑。
刑辯律師“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問題愈演愈烈,被律師們形象地稱之為“三難”,并在《律師法》的修改中,被作為主要問題對待,但在此后多年一直成為刑事辯護領域矛盾聚集的領域,并一直等到2012年3月份《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才得以較好的解決。
實際上,從2004年開始,中央已經啟動了統一規劃部署和組織實施的大規模司法改革。按照官方的說法,“從民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和影響司法公正的關鍵環節入手,按照公正司法和嚴格執法的要求,從司法規律和特點出發,完善司法機關的機構設置、職權劃分和管理制度,健全權責明確、相互配合、相互制約、高效運行的司法體制。”
以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提出的“推進司法改革,從制度上保證司法機關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為起點,到2004年,至此中國司法改革真正走向整體統籌、有序推進的階段。
200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從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戰略高度,原則同意中央政法委《關于深化司法體制和工作機制改革若干問題的意見》。改革內容涵蓋優化司法職權配置、落實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加強政法隊伍建設、加強政法經費保障四大方面,包括優化司法職權配置等部分改革具有較強的體制性,直接涉及司法體制的轉型。
到2012年,這些改革全部完成。法學界普遍認為,這些改革中,包括政法經費保障、量刑改革、案例指導制度、職務犯罪審查逮捕上提—級、擴大司法公開、防止刑訊逼供等等改革,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
2012年10月9日的司法改革白皮書重申,“中國司法改革的根本目標是保障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公正地行使審判權和檢察權,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