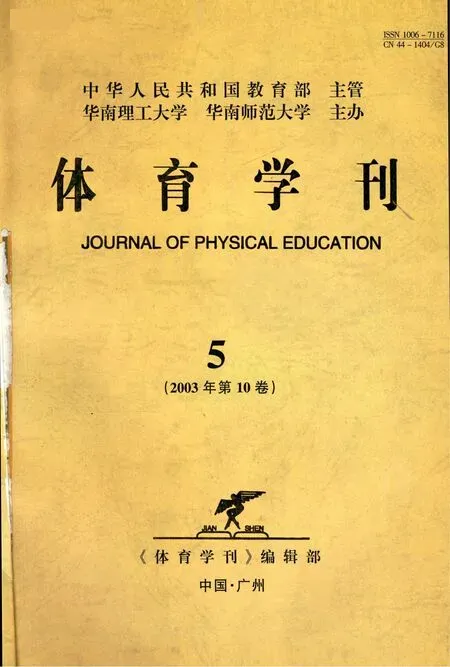江蘇省全民健身工程管理信息系統(tǒng)設(shè)計(jì)與開發(fā)
2003-04-29 11:48:53陳培友李詳晨
體育學(xué)刊 2003年5期
陳培友 李詳晨
摘要:根據(jù)江蘇省體育局全民健身工作的需要,按照軟件工程的理論、方法、步驟設(shè)計(jì)并開發(fā)了江蘇省全民健身工程管理信息系統(tǒng),以期提高江蘇省體育局的工作效率,提高管理工作的科學(xué)水平。
關(guān)鍵詞:全民健身工程;管理信息系統(tǒng);江蘇省
中圖分類號:G812.753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6—7116(2003)05—014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