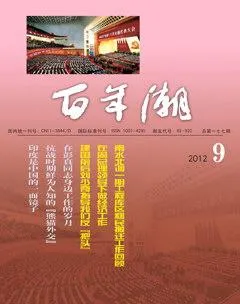我與彭老總的一段交往


1951年1月,我參加工作進了中南海,開始幾年在警衛處(后改為警衛局),后因機構改革,工作調整,又到了機要室(后改為秘書局),1971年調出,在中南海工作整整20年。
在中南海期間,我常常見到毛主席,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第一次見到毛主席時的情景。那是我進中南海的當年夏天,一天晚飯后,我們幾個小青年在勤政殿前的廣場上乘涼。突然,毛主席出現在我們面前,嘰嘰喳喳的熱鬧場面一下子安靜下來。我的心怦怦直跳,只見毛主席面孔慈祥,身材高大魁梧,穿著長袖襯衫、灰褲子。毛主席見我們其中一個小同志手里還拿著碗筷,就問他吃完飯了沒有?那位小同志緊張得竟然沒能回答出來。那一晚我興奮得久久不能入睡:我竟然見到了毛主席!
這年春節前,陳琮英同志(任弼時同志的夫人)讓我跟她到頤年堂看電影。我們去晚了,電影已經開始放映,服務員打著手電給我找了一個座位,稍一會兒我眼前一亮,發現旁邊坐的是朱總司令,我坐得直挺挺地一動也不敢動,也無心看電影,不知腦子里想些什么。這場電影演些什么,一點兒印象都沒有,腦子里一片空白。電影演完,燈亮了后,我發現毛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領導同志也在場。
以后見到毛主席的機會就多了。有一次,我騎自行車在路上碰到毛主席,警衛人員作了一個手勢,示意我下車,我就推車而過。以后遇到毛主席在路上散步,我就知道主動下車了。那些年,中南海懷仁堂常有各省的調演節目。有一次,我到懷仁堂看歌劇《劉三姐》,毛主席坐在第五排,我坐在第六排緊挨在毛主席身后的座位上。我注意到:當演到秀才唱到耕地“我在前來,牛在后”時,毛主席笑得前俯后仰。我至今難以忘懷。
1954年暑期在北戴河,7月15日那天大滿潮。我起得很早,到海邊拾貝,沒想到毛主席比我還早。毛主席與幾位警衛人員迎面走來,毛主席突然停了下來,說要下海。下海后,幾個警衛前后護著,不多一會兒,就游遠了,只能看到幾個人頭在游動,分不清哪個是毛主席,在海邊的同志們對毛主席的好水性贊不絕口。
1962年元旦,我去給毛主席送文件,到了豐澤園,看到毛主席正和身邊的工作人員照相。我真想跟徐業夫秘書說一下:自己想和毛主席合個影。但又怕秘書擋駕,沒敢開口,至今想起來非常后悔。1962年,周總理、朱總司令接見我們單位的同志時,我參加了合影,以后我還有幸多次與中央領導同志合影,但唯獨沒有和毛主席、劉少奇同志合過影,這是我此生的最大遺憾。
彭德懷同志從朝鮮凱旋回國后,住在中南海的永福堂,陳琮英同志住在彭老總前院喜福堂。
一天,彭老總與夫人浦安修來看望陳琮英同志。我給他們送上茶水后,浦大姐向彭老總介紹:“這是小王,王彬生,在琮英這里工作。”彭老總滿面笑容地看著我,并伸出他那粗大的手和我握手。浦大姐繼續介紹說:“小王在中南海文化學校上初中。”彭老總緊緊握著我的手高興地說:“哦!還是知識分子啊!青年人不僅要把工作做好,也要好好學習,不學習是要吃虧的。”從此,我與彭老總就相識了。
一天晚飯后,彭老總喊我,讓我跟他劃船去。一出門,警衛戰士給他行了一個軍禮,他駐足并回過頭來,看到是個小戰士,便說:“還是個小朋友。”小戰士臉上生起一片紅云,不知道怎么回答,竟說:“不是。”彭老總笑著說:“不是小朋友,是老朋友哇!”以后彭老總見到這位小戰士,就改口“老朋友”了。船劃到萬善殿時,彭老總提出下船看看。我們走進一座大院,彭老總指著高大的建筑說:“這就是萬善殿,當年慈禧太后關押珍妃的地方。光緒帝關在瀛臺,他晚上到萬善殿幽會珍妃。”
永福堂院里有一棵杏樹、兩棵海棠樹。果子熟了,彭老總常喊我去摘,他說:“這叫有食同吃嘛!”一次,我用竹竿打杏,彭老總說:“這樣會把杏摔壞的,你把客廳的地毯拿來,鋪上就沒事了。”
1953年,我生病在309醫院住院,出院后,陳琮英同志說:“彭老總常來打問你的病情,你出院了,就快去向他報告一下吧!”我到了他院里,看到他在客廳與客人談話,就沒有進去。
1953年8月的一天,任弼時同志的兒子任遠遠(時年13歲)放學回家,看到彭老總在院子里散步,便對他說:“彭伯伯,我這里有一個過期的膠卷,不照也是浪費,咱們還是照了吧。”彭老總哈哈大笑,說:“你這個小鬼頭!好吧,咱們就來一個廢物利用。”平時彭老總是不愿意別人給他照相的,這次任遠遠一“鬼頭”,沒想到他竟同意了。任遠遠把洗好的照片給彭老總時,他滿意地說:“這是我最漂亮的一張照片。”從這以后,彭老總的親密戰友們向他要照片時,他總是送這張。后來任遠遠也給了我一張,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想方設法地保存這張珍貴的照片。1980年6月,出版《紀念彭德懷同志》圖冊時,我珍藏的這張照片被收進了其中。
1959年廬山會議后,彭老總搬出了中南海,住在西苑吳家花園。1962年初夏的一天,我帶著女兒王晚栗去看望彭老總,我給齊秘書打了招呼,齊秘書和我是熟人,說:“去吧!”浦大姐在客廳看報,非常客氣地對我說:“多年不見了,小王你來了。”我說:“來看看彭老總。”她說:“你去吧,他在屋里。”彭老總在屋里寫毛筆字,見到我驚奇地問:“你怎么敢來看我?”我說:“我是個小蘿卜頭,怕什么。”(后來我才知道,凡接觸彭老總的人,秘書有責任都要向中央匯報)他隨即問我的工作情況,組織問題解決了沒有,我弟弟是不是還在新疆當兵,毛主席他們還跳不跳交誼舞,等等。我都一一作了回答。彭老總告訴我,他身體很好,只是這里離西郊機場近,飛機起落影響休息。接著,彭老總領我看了他種的菜、養的豬,當看到苦瓜正開著小黃花時,他說:“過一個月苦瓜就成熟了,你再來,我請你吃苦瓜。”
1979年1月,我被借調到中組部接收中央專案材料,7月正式調入。不久,浦安修同志持中央介紹信,查閱兩份有關彭老總的材料。多年不見了,她見到我非常高興,說:“你提供的彭老總相片非常好,出畫冊要用的,‘文化大革命’中彭老總的照片大都被抄家丟失了。”我說:“我知道燒了不少彭老總的相片和有眉批的書,以及何香凝畫的一幅虎圖。”我看了她拿來的介紹信后說:“您的介紹信只說查閱兩份材料,我們這里有幾鐵皮箱彭老總的材料,等我請示一下,其他的材料怎么借閱。”我當即請示了在這里負責的谷志瑞同志,谷志瑞在介紹信上批示:“所有材料都可提供。”
第二天,浦安修帶領彭老總原秘書孟慶云等三位同志來查閱材料,還特意送給我一張彭老總、浦安修、陳琮英的三人照。我給他們提供了彭老總被關押期間被迫寫的三個版本的“自傳”,他們抄了一天。離開時,浦安修提出,抄寫太慢,錯誤太多,能不能復印?谷志瑞同志表示同意。于是,他們以最詳細的一本為基礎,這本上沒有的而其他本上有的內容,就往上添加。后來,《彭德懷自述》樣書很快編出來了,他們也送給我一本征求意見。我看后,只建議加進一個情節——彭老總在一份材料中寫道,紅軍長征到了吳起鎮,彭老總收到毛主席派人送來的一首詩:“山高路險溝深,騎兵任你縱橫。誰敢橫槍勒馬,唯我彭大將軍。”他把最后一句改為“唯我英勇紅軍”,并把詩送回給毛主席。在正式出版《彭德懷自述》一書時,這個意見被采納了。書中附的毛主席與彭老總的談話,是我整理的。
很快,《彭德懷自述》出版發行,并一版再版,市場供不應求。胡喬木同志說:“至今為止,《彭德懷自述》是黨史材料中最好的一本書。”
(責任編輯 謝文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