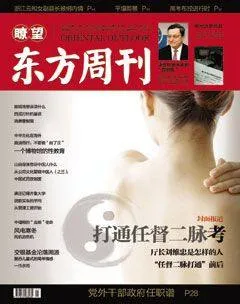復蘇兒童式的簡單情感
前不久,我在潮冷的車站上跌了個趔趄,雖然立刻就站了起來,還是把一個路過的男孩引得狂笑,他的媽媽鐵青著臉,用手狠狠擼了孩子的后腦勺一把。
這是一樁添堵的經歷。孩子和大人在這一幕面前的反應截然不同:孩子第一時間被戳中笑點;母親則沒有,不但沒有,她顯然覺得發笑是不禮貌的。
劉寶瑞先生的長篇單口《解學士》說的是明人解縉小時聰穎的故事,其中有段情節,說明了古人和今人所受的風俗道德約束的不同。
解家寒微,有一天放學回來,綿綿春雨,解縉在家門口摔了一跤,旁邊的鄰舍大人看了紛紛笑了起來。解縉爬起來之后,對眾人說:學生不才,愿為各位作一首詩。眾人稀奇,便說快快作來——其實這不是找倒霉嗎?——解縉張口道:
春雨貴如油,落地滿街流。摔倒我學生,笑壞一群牛。
這幾個觀眾當時就不干了,去找解縉的父親論理。老解出門來,問明原委,讓兒子把那兩句詩再重復一遍。解縉改了最后一句:
春雨貴如油,落地滿街流。摔倒我學生,笑壞眾朋友。
這一番口頭交鋒實在是太文縐縐了,本身沒有多大好笑的地方。大人們自找沒趣,得無聊到什么程度才會以嘲笑小孩取樂呢?隨后,他們的告狀又屬于反應過激。如果說聽這段相聲的人會感到喜悅,那無非是聽到孩子動動嘴捉弄了大人而感到一點爽快而已,而且那些大人還小題大做地把禍殃往自己身上攬——當解縉說完“笑壞眾朋友”時,大人們責備他說瞎話:“你剛才分明說我們是一群牛!”解縉作無辜狀:“爸,他們非要這么說我也沒辦法。”
非得到這時,這群大人的小題大做、狹隘自賤才能引起足夠的憎惡,讓聽故事人認同解縉對他們的折磨。

“惡魔”的放風
在網絡上看圖,最簡單的,比如一個人站在一頭海象旁邊,兩者都有一副橫著長的胡子,圖下便會有人留言說“我很邪惡地笑了”,這意思就是我心里的“惡魔”蘇醒了,我發現了某種對圖中人不利的東西。
人人心里住著個“惡魔”,但是在社交中它被看守著,壓抑著,偶爾能被釋放出來,重的形成暴力,輕的可能是個惡作劇,多數時候它是放不出來的。為了釋放,有文字的民族都生產出了自己的笑話,相聲的起源也可以追溯到這一心理需要。聽相聲時,我們認同臺上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折磨,我們內心的“惡魔”在觀看別人的互相折磨時探出腦袋:它放風的時間到了。
對比一下現在的劇場相聲和當年的廣播、電視、晚會上的相聲,就會發現劇場里的表演之所以“口味重”,是因為它要把觀眾心里的那個“惡魔”徹底趕出窩來,這不但有賴于甲——進攻方的充分使壞,還得靠著乙——防守方主動犧牲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一個周瑜、一個黃蓋的組合。
最近看郭德綱、于謙的一個視頻,郭德綱說于謙遛狗,出門二十分鐘又回來了,于問:“遛完了?”郭答:“忘帶狗了。”這時于謙有幾種接話方式:表示重度不滿的“去你的!”表示輕度不滿的“沒聽說過!”表示委屈無奈的“像話嗎?”而于謙的回答卻是:
這不就是遛我嗎?
句話甚妙,它至少有兩重功效:
其一,于謙主動增強了加到自己身上的折磨的力度。現實中很少有人會這么主動去聯想作自嘲的,但是,若是有這么一個朋友在身邊,時常對你的攻擊報以一種積極而無可奈何的反饋(“好,我服了你了”,“真拿你沒辦法”,“你的良心大大地壞了”),你早晚要引他為心有靈犀的密友;
其二,也是更微妙的一點,于謙暗示觀眾,我本人都沒拿這種折磨當回事,你又何必對我感到同情呢?
捧逗之間
要是任相聲自由施展,必然有無數這種愿打愿挨的橋段出來。所以,1950年成立“相聲改革小組”后,老藝人們找到老舍先生共謀相聲出路,因為他們清楚地知道捧逗之間這種強弱關系,如果甲乙二人的口舌都干干凈凈用在內耗里了,那還能有何正面貢獻?
因此,《白事會》、《拴娃娃》、《賣五器》這些通篇甲拿乙開涮的傳統節目就不太好演,《相面》、《夸住宅》等則需要清除一些“過分”的東西。這個變化的發生,直接導致了多少年后,常演《白事會》的津派演員還是對京派橫豎看不順眼,嫌他們太端著,太“和諧”,不敢去撩動觀眾譏刺他人的本能。
我經常舉姜昆、李文華的《談美》為例,這是他倆最早的作品之一。姜昆上來就拿李文華說事:“您在后臺,往鏡子前頭一站,弄點紅抹臉上……一站站了二十多分鐘,誰也擠不到前邊去”,李文華靦腆笑答:“我覺得我自己,越看越有看頭。”
按現在的演法,說到這一步,下面逗哏的就該“折磨”捧哏的了,比如這樣:
李:我覺得我自己,越看越有看頭。
姜:這就叫人要臉樹要皮。
李:你這話我聽著別扭。
或者這樣:
李:我覺得我自己,越看越有看頭。
姜:您的自戀讓人肅然起敬。
李:你這叫什么話?
但《談美》并沒有二人的互相嘲諷,姜昆接下去談到李文華雖然上了年紀,卻有一身合體的衣服,最后落實到主題:“這就叫愛美之心人皆有之”。
這一番開場對白,用李文華的年歲和他煞是天真的表達(“我瞧著自己那么短小精悍的”)搔搔觀眾的笑紋。演員跟觀眾維持著這樣一個共識,即,觀眾知道自己能得到什么,他們不會對演員期待得不到的快樂——放出“惡魔”后的快樂。
安全地看人出丑
那些年與相聲有關的出版物,也在向讀者解釋為什么捧逗是平等的。1988年出版的陳連升、孫立生所著《相聲群星》一書里,說到為王謙祥捧哏的李增瑞的情況:
李增瑞被固定捧哏以后,有一段時間產生了悲觀情緒,自卑感相當嚴重。由于多種原因,捧哏演員歷來被某些人所輕視,他是從小要強慣了的,在學校里總是一帆風順,想起將來的“命運”,總有許多不安,而又無法解脫……
王李的長期搭檔后來被美稱為“祥瑞檔”,很難判斷,李離開王能否有更好的發展。上面這段引文把李增瑞當成一個思想“出了狀況”的積極分子,經過批評教育、自我學習后,才認識到應以大局為重。文章要說服讀者,捧逗之間是社會分工不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
孩子的快樂很多時候得于他們內心的惡魔無人看管,他們甚至不知道嘲笑一個跌倒的人,可能會在第一時間遭致報復。相聲演員利用周瑜黃蓋式的折磨表演,設法在成人心中復蘇兒童的這種簡單情感,還得告訴觀眾,請你放心,我們是心甘情愿的。
當著觀眾,郭德綱經常說些安撫語言:“玩笑歸玩笑,日常生活中我很尊重于老師,于老師出道比我早,藝術和人品都比我高,我們是好兄弟……”云云,仿佛一團和氣,然而話內一旦冒出機鋒,觀眾立刻切換入幸災樂禍的狀態。說穿了,相聲本質上就是演員付出犧牲,給觀眾一個安全地看人出丑的機會。
弗洛伊德說,你心里的妖孽有多強大,決定了你需要為看守這個妖孽付出多少能量,也決定了你能從嘲笑別人中獲得多大的快感。同情心強的,笑得克制些,反之笑得狂放而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