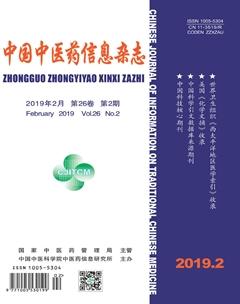趙尚華治療甲狀腺癌術(shù)后月經(jīng)不調(diào)驗(yàn)案
張彥敏
摘要:趙尚華教授參考?xì)v代醫(yī)籍并結(jié)合臨床經(jīng)驗(yàn),獨(dú)創(chuàng)治療癌癥“元宗血津復(fù)辨證法”,在臨床取得滿意療效。本文重點(diǎn)介紹趙尚華治療甲狀腺癌術(shù)后月經(jīng)不調(diào)的經(jīng)驗(yàn)及用藥。
關(guān)鍵詞:名醫(yī)經(jīng)驗(yàn);趙尚華;甲狀腺癌;月經(jīng)不調(diào)
中圖分類號(hào):R273.61???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5-5304(2019)02-0117-02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9.02.026
開放科學(xué)(資源服務(wù))標(biāo)識(shí)碼(OSID):
Abstract: Professor ZHAO Shang-hua created “Yuan Zong Xue Jin Fu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method” originally referring to ancient and modern medical books and combined with clinical experience, which has obtained satisfactory efficacy in clinic.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ZHAO Shang-huas experience and medication in the treatment of irregular menstruation after thyroid cancer operation.
Keywords: experience of famous doctors; ZHAO Shanghua; thyroid cancer; irregular menstruation
山西中醫(yī)藥大學(xué)趙尚華教授是全國(guó)第四批名老中醫(yī)藥專家學(xué)術(shù)經(jīng)驗(yàn)繼承工作指導(dǎo)老師,長(zhǎng)期從事中醫(yī)教學(xué)、科研、臨床工作,近十余年致力于中醫(yī)治療癌癥的研究,在實(shí)踐中逐步形成了獨(dú)特的的學(xué)術(shù)思想和臨床經(jīng)驗(yàn)。筆者跟師4年余,深感其遣方用藥精妙,茲將趙師治療甲狀腺癌術(shù)后月經(jīng)不調(diào)驗(yàn)案介紹如下。
1? 典型病例
患者,女,40歲,因“月經(jīng)不調(diào)2年”于2012年3月8日就診。患者自2005年出現(xiàn)甲狀腺功能減低,于2010年3月發(fā)現(xiàn)甲狀腺癌并行切除術(shù),病理示“橋本氏病、甲狀腺乳頭狀癌,并有砂粒體、鈣化”。術(shù)后化療6個(gè)周期,恢復(fù)情況良好,但術(shù)后即出現(xiàn)月經(jīng)不調(diào)。2012年2月23日復(fù)查“甲功五項(xiàng)”基本正常。現(xiàn)服用左甲狀腺素鈉片,每日3片。刻下:月經(jīng)周期前后不定,經(jīng)量少、色黯,經(jīng)期頭暈,易潮熱出汗,煩躁,氣短,納可,眠可,二便調(diào),舌體胖大,苔白,脈沉。查:頜下淋巴結(jié)腫大。有左側(cè)乳腺增生病史。四診合參,辨為沖任不調(diào)證。治以調(diào)理沖任、溫陽(yáng)散結(jié)為主。方藥:仙茅10 g,肉蓯蓉10 g,巴戟天10 g,當(dāng)歸10 g,知母10 g,黃柏6 g,山萸肉10 g,夏枯草15 g,連翹10 g,五味子10 g,茯苓10 g,炒梔子10 g,炙甘草6 g。6劑,每日1劑,水煎服。
2012年3月15日二診:患者自覺諸癥略有減輕,左側(cè)乳腺腫脹、疼痛,出汗較多,舌體胖大、有齒痕,苔白,脈沉。守方加薏苡仁30 g、澤瀉10 g、黃芪30 g。繼服6劑。
2012年3月29日三診:患者月經(jīng)將至,感覺全身不適,燥熱出汗,上次月經(jīng)時(shí)痛經(jīng),量少、色黯,舌淡紅、有齒痕,苔白,脈沉。守方繼服6劑。
2012年4月29日四診:患者服上藥3劑后月經(jīng)來潮,色黯、量可,無痛經(jīng)。自覺偶有頸部刺痛,足跟疼痛,舌淡紅,苔白,脈沉細(xì)。守方加淫羊藿10 g、僵蠶10 g、蟬蛻10 g。以此法加減治療1年,患者月經(jīng)正常,無明顯不適。
2? 討論
趙師在參考?xì)v代治癌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上,結(jié)合多年臨床實(shí)踐,總結(jié)出一套治療癌癥的“元宗血津復(fù)辨證法”,將癌癥分為元分證、宗分證、血分證、津分證、復(fù)元證5個(gè)階段。①元分證:元?dú)獍ㄔ幒驮?yáng)之氣,稟受于先天之精,賴后天脾胃化生之水谷精微榮養(yǎng)而滋生。其發(fā)源于腎,藏在丹田,憑借三焦之網(wǎng)絡(luò)通達(dá)全身,推動(dòng)全身組織器官的活動(dòng),為人身生化的動(dòng)力。元?dú)馐艿街掳┮蛩氐那忠u所發(fā)生的病變稱為元分證。②宗分證:癌毒侵襲宗氣后,形成各種不斷增生的結(jié)塊、瘤體,如菌狀、巖狀、雞冠狀、條索狀、砂礫狀等,這些通稱為宗分證。③血分證:血是飲食精微所化生而循行于脈中的富于營(yíng)養(yǎng)的紅色液體,其功能是奉養(yǎng)全身、維持全身各臟腑組織的正常功能活動(dòng)。血分受傷則全身各臟器都能受損,這些通稱為血分證。④津分證:津是人身體液的組成部分,來源于飲食水谷之精微,隨三焦氣運(yùn)行于五臟六腑,出入于肌膚腠理之間,功能為溫養(yǎng)肌肉、滋潤(rùn)皮膚。癌毒久襲,津液大傷而出現(xiàn)之證通稱津分證。⑤復(fù)元證:經(jīng)中西藥物、手術(shù)、放射等治療后的好轉(zhuǎn)恢復(fù)期病證稱為復(fù)元證。
本案患者乃術(shù)后沖任不調(diào)者,屬?gòu)?fù)元證范疇。趙老認(rèn)為,復(fù)元證階段的治療應(yīng)分虛實(shí)以善后、守成法防復(fù)發(fā)。實(shí)證如術(shù)后高熱不退之腑實(shí)者,應(yīng)治以通腑瀉熱;腫脹不消者,應(yīng)治以活血化瘀、通絡(luò)滲水。虛證如氣血大虛者,以益氣養(yǎng)血為主;腎氣虛損者,以補(bǔ)腎為主;沖任失調(diào)致病如甲狀腺癌術(shù)后月經(jīng)不調(diào)者,以調(diào)理沖任、溫陽(yáng)散結(jié)為主。虛實(shí)夾雜證需特別注意復(fù)發(fā)。
本案為女性患者,甲狀腺癌屬中醫(yī)學(xué)“石癭”“肉癭”等范疇。沖任失調(diào)是月經(jīng)不調(diào)的基本病機(jī)。沖有“沖要”之意,“沖為血海”,“為十二經(jīng)脈之海”;任有“擔(dān)任”“妊養(yǎng)”之意,任脈為“陰脈之海”,又“任主胞胎”。女子以血為本,月經(jīng)、孕育都以氣血為基礎(chǔ),故只有任脈、沖脈旺盛時(shí),氣血才能下注于胞中,或?yàn)a出而為月經(jīng),或妊養(yǎng)胚胎,故張景岳云:“月經(jīng)之本,所重在沖任。”《諸病源候論》有“月經(jīng)不調(diào)為沖任受傷,月水不道為沖任受寒,漏下乃沖任虛損”。如沖任失調(diào),沖脈、任脈氣血不足或運(yùn)行不利,可見月經(jīng)失調(diào)、絕經(jīng)或不孕等病癥。甲狀腺癌發(fā)病多從肝郁而來,肝郁則沖任失調(diào),且“肝為女子先天”,婦女經(jīng)、孕、產(chǎn)、乳均與肝經(jīng)氣血密切相關(guān),若情志不暢、肝氣郁結(jié)、飲食失調(diào),則易致氣郁痰結(jié)、肝郁化火、氣滯血瘀,故女性更易罹患甲狀腺疾病。本案乃中年女性患者,家庭及社會(huì)壓力較大,易致沖任失調(diào)而致病,故治以調(diào)理沖任為主,輔以溫陽(yáng)散結(jié),方用二仙湯加減以溫腎陽(yáng)、補(bǔ)腎精、瀉腎火、調(diào)沖任。方中仙茅、巴戟天、山萸肉溫腎陽(yáng)、補(bǔ)腎精,黃柏、知母瀉腎火、滋腎陰,當(dāng)歸溫潤(rùn)養(yǎng)血、調(diào)理沖任,夏枯草、連翹散結(jié),五味子斂汗,茯苓健脾滲濕,炒梔子清心除煩,炙甘草調(diào)和諸藥。二診時(shí)諸癥減輕,因舌體胖大、有齒痕,故酌加健脾滲濕之品。三診時(shí)月經(jīng)將至,全身不適,仍用上方繼服;四診時(shí)諸癥減輕,脈沉細(xì),酌加補(bǔ)氣散結(jié)之黃芪、僵蠶、蟬蛻,取升降散之意以升清降濁,調(diào)理氣機(jī)。以此法加減治療1年,療效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