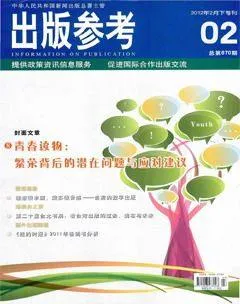讓我們善用新聞?wù)Z言
有位哲人說(shuō)過(guò):語(yǔ)言是思維的外殼,決定語(yǔ)言的是思維。要想有經(jīng)典的語(yǔ)言,就要有超人的思維。
寫(xiě)新聞報(bào)道,就得運(yùn)用語(yǔ)言,要想寫(xiě)出新聞精品,就要有超人的思維,善于運(yùn)用好新聞?wù)Z言。運(yùn)用語(yǔ)言是一門(mén)藝術(shù)。報(bào)道一件事或一個(gè)人,詞語(yǔ)豐富的人,寫(xiě)出來(lái)的新聞就有聲有色,有血有肉,具有可讀性和感染力;相反,語(yǔ)匯貧乏的人,寫(xiě)出的報(bào)道就干巴、枯燥,令人厭讀。
何謂新聞?wù)Z言?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新聞學(xué)院藍(lán)鴻文教授給新聞?wù)Z言下的定義是:“通過(guò)新聞媒介,向人們報(bào)道新近發(fā)生的事實(shí),傳播具有新聞價(jià)值的信息時(shí)所使用的語(yǔ)言”。新聞?wù)Z言是新聞報(bào)道的物質(zhì)外殼,它肩負(fù)著向受眾表述新聞事實(shí)、傳遞新聞信息的特殊使命,是構(gòu)筑新聞報(bào)道的最基本元素。
新聞?wù)Z言的特點(diǎn)究竟是什么?
新聞?wù)Z言與文學(xué)語(yǔ)言、理論文體語(yǔ)言以及公告、通知、座談會(huì)、紀(jì)要一類(lèi)文體語(yǔ)言是有區(qū)別的,譬如,新聞?wù)Z言要真實(shí),只能用事實(shí)說(shuō)話(huà),只能準(zhǔn)確反映生活,寓理于事,而不能想象夸張,而不能高于生活,新聞?wù)Z言精練、樸實(shí)、生動(dòng),而不能過(guò)于莊重、嚴(yán)肅。
毛澤東曾經(jīng)對(duì)語(yǔ)言提出過(guò)“準(zhǔn)確、鮮明、生動(dòng)”的要求。這是一個(gè)很精辟的說(shuō)法。它包括了對(duì)語(yǔ)言的最基本的要求,而且,這個(gè)排列的次序也是正確的、操作性很強(qiáng)的。
新聞?wù)Z言,是新聞這一特殊體裁的表現(xiàn)形式,與其他文體語(yǔ)言相比,有它自己的特點(diǎn),但又具有其他文體語(yǔ)言的綜合因素。如果看不到這一點(diǎn),不是文學(xué)代替新聞,就是新聞的虛假含糊、空泛晦澀、枯燥繁雜、老套粉飾。新聞?wù)Z言要量體裁衣,要符合新聞的特殊要求,要按新聞的不同內(nèi)容,應(yīng)用和內(nèi)容相適應(yīng)的語(yǔ)言,讓新聞?wù)Z言真實(shí)明白、簡(jiǎn)潔生動(dòng)、通俗具體。
可以說(shuō),一切文章對(duì)語(yǔ)言的基本要求都是準(zhǔn)確、鮮明、生動(dòng)的,新聞自然也不例外。
所謂準(zhǔn)確,就是準(zhǔn)確反映客觀事物,準(zhǔn)確表達(dá)作者的思想觀點(diǎn)。語(yǔ)言不準(zhǔn)確,還談什么鮮明生動(dòng)?
有了準(zhǔn)確還不行,還要鮮明,鮮明的語(yǔ)言才能給人以鮮明的印象;還要生動(dòng),生動(dòng)是為了增加文字的吸引力、感染力,提高語(yǔ)言的效果。
采用何種風(fēng)格的語(yǔ)言,是與新聞工作者的世界觀、價(jià)值觀、情感趨向有關(guān)聯(lián)的。古人云:“氣盛則言宜”。這個(gè)“氣”,指的就是新聞工作者的精神高度、審美境界和心理狀態(tài)。只有具備了某種信仰,著作家才會(huì)在此基礎(chǔ)上產(chǎn)生自信,產(chǎn)生一種高屋建瓴式的沖動(dòng),由此而選擇一種自己所喜愛(ài)的、能與自己的審美境界、價(jià)值取向相適應(yīng)的語(yǔ)言風(fēng)格。譬如,杜甫有“窮年憶黎元嘆息腸內(nèi)熱”的情懷,才會(huì)有沉郁頓挫的語(yǔ)言風(fēng)格;施耐庵有對(duì)市井英雄的高度贊美,才會(huì)用那種簡(jiǎn)潔、幽默、韻味悠長(zhǎng)的宋元口語(yǔ)《紅樓夢(mèng)》作者因?yàn)閷?duì)青春、對(duì)逝去的美好生活過(guò)于眷戀,才有了細(xì)膩的、經(jīng)得起反復(fù)推敲和咀嚼的描寫(xiě)。
要真實(shí)準(zhǔn)確,不要虛假。“修辭立其誠(chéng)”。新聞是新近發(fā)生的事實(shí)的報(bào)道。真實(shí)是新聞的生命。新聞要真實(shí),要說(shuō)真話(huà),不說(shuō)假話(huà),讓真心話(huà)反映真實(shí)情況,揭示出真理,不能有半點(diǎn)含糊和虛假。使用語(yǔ)言表達(dá)時(shí)要準(zhǔn)確,即遣詞、用字、造句都要符合新聞事實(shí)的本來(lái)面目,合乎邏輯,做到說(shuō)話(huà)要實(shí)實(shí)在在,概念清楚,捕捉靈感,共享經(jīng)驗(yàn)判斷準(zhǔn)確,推理正確,講究分寸,留有余地,不要虛夸和說(shuō)絕對(duì)的話(huà)。
要鮮明實(shí)在,忌含糊不清。語(yǔ)言應(yīng)簡(jiǎn)潔明了,提倡什么反對(duì)什么,崇尚什么貶低什么,表?yè)P(yáng)什么批評(píng)什么,樹(shù)立什么破除什么,旗幟鮮明,不含糊,不模棱兩可。語(yǔ)言文字鮮明包括語(yǔ)言新鮮、亮麗和新穎、獨(dú)到。新聞?wù)Z言的新穎、鮮亮,也就是說(shuō)這種語(yǔ)言是貨色生香的語(yǔ)言,像雨中的梨花、像清流中的荷葉一樣鮮亮清麗。
新聞?wù)Z言簡(jiǎn)潔明了,就是鮮明實(shí)在,簡(jiǎn)潔有力,讓讀者一看就懂,心里就清楚明白。鄧小平的語(yǔ)言很有特色,抓住要害,不冗長(zhǎng)煩瑣,簡(jiǎn)短的幾個(gè)字可以概括很多的內(nèi)容。比如,在談到長(zhǎng)征時(shí),他用了“跟著走”三個(gè)字;談抗戰(zhàn)時(shí)的感受,用“吃苦”兩個(gè)字;談解放戰(zhàn)爭(zhēng),用“最舒暢”三個(gè)字;談“文革”之前的十年工作,用“最忙”兩個(gè)字;談“文革”,用“最大的災(zāi)難”五個(gè)字;得知林彪摔死后,用“林彪不亡,天理不容”八個(gè)字;談到自己三落三起時(shí),用“忍耐”三個(gè)字;談世界問(wèn)題,用“東西、南北”四個(gè)字;談精簡(jiǎn)軍隊(duì)的問(wèn)題,用“腫、散、驕、奢、惰”五個(gè)字……我們運(yùn)用新聞?wù)Z言,應(yīng)該學(xué)習(xí)這種語(yǔ)言特色,做到鮮明實(shí)在,不要含糊不清。
要通俗簡(jiǎn)潔,讓受眾愛(ài)聽(tīng)。常言道:“話(huà)須通俗方傳遠(yuǎn)。”新聞是寫(xiě)給受眾看的、聽(tīng)的,要求用語(yǔ)要通俗有趣,深人淺出,不要晦澀費(fèi)解。新聞媒體是通過(guò)自己的作品來(lái)具體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這一偉大宗旨的,新聞?wù)Z言要振聾發(fā)聵,影響受眾,其第一位的要求就是有的放矢,在弄清宣傳對(duì)象的接受能力、思想狀況的基礎(chǔ)上,力求使受眾都能看得懂、易理解,通俗生動(dòng),樂(lè)于接受。新聞工作者學(xué)會(huì)用群眾的語(yǔ)言著文講話(huà),容易把抽象的道理講得形象具體,感情上也能更好地貼近受眾。會(huì)不會(huì)講群眾的話(huà),不是單純的語(yǔ)言表達(dá)問(wèn)題,反映的是新聞工作者的思想作風(fēng)和工作作風(fēng)。只有密切聯(lián)系群眾,真正了解群眾,才能學(xué)會(huì)群眾的語(yǔ)言,講出受眾愛(ài)聽(tīng)的話(huà)來(lái)。
要使新聞?wù)Z言通俗,不晦澀,需要始終注意以下幾點(diǎn):不用或少用生僻字詞;不用或少用公文語(yǔ)言;慎用古漢語(yǔ);盡可能避免技術(shù)性、業(yè)務(wù)性很強(qiáng)的術(shù)語(yǔ)和行話(huà)。
要生動(dòng)活潑,切忌死板老套。豐富多彩的客觀世界和瞬息萬(wàn)變的現(xiàn)實(shí)生活,決定了我們的新聞作品必須擯棄刻板、老套和形式主義,代之以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喜聞樂(lè)見(jiàn)、特色鮮明的表達(dá)方式和格調(diào)。新聞?wù)Z言應(yīng)該活潑,不呆板、不沉悶、不死氣,活靈活現(xiàn),讀起來(lái)感到勃勃有生氣。比如鄧小平用“不管白貓黑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這樣的語(yǔ)言來(lái)講生產(chǎn)力標(biāo)準(zhǔn),就非常形象生動(dòng)。
毛澤東一貫提倡生動(dòng)活潑的文風(fēng)。1951年6月6日,他親自修改審定了《人民日?qǐng)?bào)》社論《準(zhǔn)確地使用祖國(guó)的語(yǔ)言,為語(yǔ)言的純潔和健康而斗爭(zhēng)》,號(hào)召大家將文章寫(xiě)得準(zhǔn)確些、生動(dòng)些。1955年12月,他在《合作社的政治工作》一文按語(yǔ)中指出:“我們的許多同志,在寫(xiě)文章的時(shí)候,十分愛(ài)好黨八股,不生動(dòng),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這就要求我們的報(bào)紙和刊物的編輯同志注意這件事,向作者提出寫(xiě)生動(dòng)和通順文章的要求,并且自己動(dòng)手幫作者修改文章。”
要一點(diǎn)平實(shí)樸素,少一點(diǎn)裝腔作勢(shì)。所謂樸實(shí)就是樸素和實(shí)在,不刻意雕琢,不矯揉造作,不擺官腔,這是新聞報(bào)道特有的風(fēng)格。寫(xiě)文章并非架子拉得越大越好,調(diào)門(mén)起得越高越好,相反的卻是越平實(shí)就離讀者越近,越自然就離讀者越親,越樸素就越為讀者所喜聞樂(lè)見(jiàn)。那種語(yǔ)言“驚天動(dòng)地”、說(shuō)理“高深玄妙”、格調(diào)“超凡脫俗”的文章,欣賞者除了作者本人以外,不會(huì)太多。
凡大家的作品,無(wú)一不是平實(shí)樸素見(jiàn)長(zhǎng),有道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廢華采,去文繡,未必?zé)o美人也。”清朝時(shí)候,北京某胡同有個(gè)人叫王婆,家里富有,做了口棺材,要一位道士給題個(gè)好名稱(chēng)放在棺材前面。道士苦思冥想,題上了這樣一個(gè)名目:“翰林院侍講大學(xué)士國(guó)子監(jiān)祭酒隔壁之隔壁王婆之樞”。多唬人吶,可實(shí)際上不就是個(gè)平民百姓“王婆”嗎?為什么要干這種貽笑大方的事情呢?為人為文還是樸實(shí)一點(diǎn)為好。第十七屆中國(guó)新聞獎(jiǎng)消息一等獎(jiǎng)作品《火車(chē)首次跨越“世界屋脊”》以樸實(shí)的敘述為主,僅用了“世界為之矚目”“扎西德勒”“夢(mèng)想成真”“為沿線風(fēng)光陶醉”“重寫(xiě)歷史”等,就將這一舉世矚目的壯舉生動(dòng)地展現(xiàn)在受眾面前,讓人感到樸實(shí)自然。新聞?wù)Z言樸素平實(shí),才具有感染力。
“天意君須會(huì),人間要好詩(shī)。”時(shí)代和人民呼喚文風(fēng)好、質(zhì)量高的著作文章,需要新聞工作者加倍努力,做到善用新聞?wù)Z言,寫(xiě)作新聞精品。
自得方為貴,功夫在文外。“自得”并非無(wú)性。新聞?wù)Z言不是很容易就學(xué)好的,運(yùn)用好的,需要下苦功夫,在實(shí)踐中錘煉出來(lái)。駕馭語(yǔ)言的能力,也得多練、多學(xué)。學(xué)什么?從哪里學(xué)?自然是向書(shū)本學(xué),讀前人的優(yōu)秀作品,但不是照搬照抄,尋章摘句,而是領(lǐng)會(huì)其精神,增加語(yǔ)匯。
注意多向生活學(xué)習(xí),向群眾的語(yǔ)言學(xué)習(xí)。豫劇《朝陽(yáng)溝》風(fēng)行全國(guó),長(zhǎng)盛不衰。劇作者楊蘭春出生在太行山區(qū),有著豐富的生活底蘊(yùn)。他抗戰(zhàn)時(shí)期就投身革命,與農(nóng)民有著同甘共苦的歷練。他為農(nóng)民寫(xiě)戲。楊蘭春對(duì)弟子的教導(dǎo)中有條死規(guī)定:“走馬觀花不如下馬看花,下馬看花不如親自種花。每年用三個(gè)月時(shí)間深入生活,至少一個(gè)月同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dòng)。”他創(chuàng)作的《朝陽(yáng)溝》語(yǔ)言精美生動(dòng),充滿(mǎn)強(qiáng)烈的農(nóng)村生活氣息,創(chuàng)造了一種完美的語(yǔ)言范式。如,“墻上畫(huà)馬不能騎,鏡子里的燒餅不能充饑,好牛不調(diào)不能拉犁”,“給你一個(gè)手電筒好照路,給你一雙膠鞋好踩泥。”“蘿卜青,青凌凌,麥籽個(gè)個(gè)飽盈盈,白菜長(zhǎng)得瓷丁丁。”《朝陽(yáng)溝》作為一個(gè)有著極強(qiáng)地方色彩的戲種,之所以受到不同地域、不同方言人群的至喜至愛(ài),一個(gè)根本的原因就是語(yǔ)言和文風(fēng)代表了老百姓的方向,是綠色的語(yǔ)言和綠色的文風(fēng)。新聞工作者應(yīng)該從中領(lǐng)悟到:向生活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群眾語(yǔ)言,新聞?wù)Z言怎能學(xué)不會(huì)、用不好?
刪繁就簡(jiǎn)出短文,字斟句酌鑄美言。新聞?wù)Z言都是改出來(lái)的。這是一條寫(xiě)作規(guī)律。清代史學(xué)家、文學(xué)家趙翼說(shuō):“詩(shī)家好作奇句瞀語(yǔ),必千錘百煉而后能成。”杜甫主張“為人性僻耽佳句,語(yǔ)不驚人死不休”。賈島的推敲精神讓人感動(dòng),“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的佳句讓人難以感懷;還有那盧廷讓“吟安一個(gè)字,拈斷數(shù)莖須”的“煉字”精神,真可謂風(fēng)范可嘉。
編輯改稿時(shí)所要做的,主要是:增、刪、改、調(diào)。“增”,就是增加、補(bǔ)充初稿中疏漏不全的材料,增加文字欠通暢和不夠準(zhǔn)確的詞句。“刪”,就是刪去,刪去那些無(wú)用的空話(huà)、大話(huà)、套話(huà)。“改”就是更改、變動(dòng),將文章中表達(dá)不正確、不全面、不貼切的病語(yǔ)及錯(cuò)別字,改為準(zhǔn)確、通順。“調(diào)”,指詞句的調(diào)動(dòng)。經(jīng)過(guò)調(diào)整、調(diào)動(dòng),使稿件內(nèi)容層次分明,語(yǔ)句通暢。首屆中國(guó)新聞獎(jiǎng)一等獎(jiǎng)作品《老臺(tái)胞尋女奇遇記》,從采寫(xiě)到見(jiàn)報(bào)四易其稿,終于深化了主題,突出了情感,強(qiáng)化了細(xì)節(jié)描寫(xiě),語(yǔ)言也更加練達(dá)生動(dòng)。
(作者系安徽省委《江淮》雜志社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