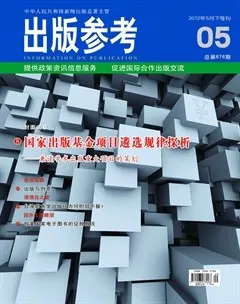臺灣的大學出版社為何積弱不振?
臺灣的大學出版社常年積弱不振,出版品雖然偶有佳作,但是出版量極少,且很難在圖書市場上看到,這也算是臺灣出版市場的怪現象之一。
臺灣的學術出版一直由其他類型的出版社支撐,也孕育出了不少知名品牌,如專門出版法律的三民書局、五南文化,出版社會學的巨流、群學等。
不懂其中緣由的人,經常把矛頭對準大學出版社,批判大學出版社不愿承擔學術出版的責任。實際上,臺灣的大學出版社之所以在學術出版領域缺席,有其不得已的原因。
臺灣的大學出版社,最早源于上世紀六十年代,當時的臺灣有兩家大學出版社,分別是天主教私立輔仁大學、私立文化大學出版社。在本土學術出版品尚屬稀少的年代,他們出版過不少好書,且銷售成績不錯,特別是輔仁大學社的文史哲社科出版品啟蒙了許多日后走入上述領域的學者教授。
然而,不知曾幾何時,這兩間大學出版社悄悄地沒落了,縮減到以經營自家大學的教科書出版為主,甚少再有新書出版。
直到2000年,臺灣的大學法修法,正式將出版納入大學法之中,成為大學的任務之一,大學自此取得了出版的法源,不少大學紛紛成立出版中心。
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臺灣的大學出版中心的出現,除了法令之外,某種程度上還與近年來臺灣各個公私立大學得到的教育補助金額減少有關。
大學因為補助款縮水,紛紛自籌財源,不少學校成立“校務基金”,只要有賺錢的機會,全都不放過。不少大學才陸續(xù)有了大學出版中心,畢竟光是出版本校學生使用的通識及必修課程的課本,每年也是一筆穩(wěn)定的財源。
不過,不少大學雖然成立了出版中心,卻因為組織、人事等問題,編制新書的功能不多,印制講義、教科書、畢業(yè)紀念冊等服務學校事務需求的印刷出版反而是主要任務。
大學出版社要進入市場,除了要定期推出新書,還要與經銷商、書店、媒體打交道,遵循出版市場的賬務規(guī)則等。
舉個例子,臺灣大學為激勵研究風氣,提升教學質量,出版學術著作及期刊,經校務會議通過,于1996年成立臺大出版中心,設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本校教授兼任,任期四年,可連任一次,處理出版中心日常業(yè)務。出版中心分設編輯出版與銷售發(fā)行。
臺大出版中心創(chuàng)立初期,遵循的正是前述提及的印務模式,只是將教務處的印務單位獨立出來,主要的工作仍以印制講義與書籍為主,實行預算制,由學校每年編列一筆預算給出版中心。
后來接手的出版中心主任決定轉型,向學校爭取預算,著手進行出版中心的改造計劃,立志要讓臺大出版中心成為大學出版社中的領導品牌,承擔學術出版的重責大任。
目前的臺大出版中心,一年約出版40本書,其中70%為學術叢書、教科書、知識書籍、學術期刊、多媒體DVD資料的編輯出版業(yè)務,另外30%為與外部單位的合作,協助將研究計劃出版成書。
銷售方面,積極轉型之后的臺大出版中心,委托圖書經銷商,將出版品鋪貨到一般實體書店。另外,臺大出版中心與臺灣的網絡書店簽訂直接往來的銷售合約,直接供貨給網絡書店。中心還與Google Book Search合作,透過搜尋引擎就能搜尋到臺大出版中心所出版的出版品資料。
至于近年來非常夯的電子書銷售,臺大出版中心以統包的方式,將已經出版的450種書,委托單一合作廠商,以包裹式銷售法主攻海外圖書館市場。臺大出版中心也積極參加書展,舉辦演講、新書發(fā)表會等活動,發(fā)展“手術式營銷法”。
然而,因為臺大出版中心畢竟是公立大學成立的行政單位,受采購法的限制,只要十萬元以上的支出,就得開標案。
此外,出版中心的所得營收必須全部上繳校務基金,形成中心營運成本來自校內編列預算,所得全部上繳學校的獨特的財務模式,財政無法獨立。若是將來學校高層不再支持出版中心,恐怕將后繼無力。
臺大出版中心尚且要面對如此多的障礙,其他大學出版中心就更不易了。況且,在臺灣,出版又不是一個能賺大錢的行業(yè),學術評級制度也不鼓勵學者出版專書,這些都不利于出版中心的發(fā)展,是臺灣出版界的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