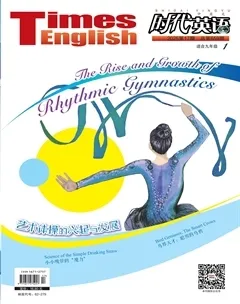Listening Training 4
第一節(jié) 聽下面5段短對話,選擇正確答案。
1. What is Linda doing now?
A. Watching TV. B. Eating an apple.
C. Doing the housework.
2. How much is the cap?
A. $3. B. $4. C. $7.
3. What is the model house made of?
A. Wood. B. Plastic. C. Newspaper.
4. How will the man help the woman?
A. By carrying the bag.
B. By opening the door.
C. By looking for the key.
5. Who is Jane?
A. Kate’s friend. B. Kate’s classmate.
C. Kate’s neighbor.
第二節(jié) 聽下面5段長對話或獨白,選擇正確
答案。
聽第6段材料,回答第6、7題。
6. How long will the man stay in Shanghai?
A. Two days. B. Four days.
C. Five days.
7.What will the weather be like in Shanghai tomorrow?
A. Sunny. B. Rainy. C. Cloudy.
聽第7段材料,回答第8至10題。
8. Who are the speakers talking about?
A. John’s cousin. B. John’s brother.
C. John’s uncle.
9. What clothes is Frank in?
A. A blue jacket. B. Black jeans.
C. A black jacket.
10. What does Frank eat every day?
A. Eggs. B. Vegetables.
C. Hamburgers.
聽第8段材料,回答第11至13題。
11.What does the woman want to buy for her son?
A. A storybook. B. A novel.
C. A geography book.
12. When is the son’s birthday?
A. Next Tuesday. B. Next Thursday.
C. Next Sunday.
13. What is the man good at?
A. Playing the piano.
B. Playing the violin.
C. Playing basketball.
聽第9段材料,回答第14至16題。
14. Why does the woman come to the man?
A. To greet him.
B. To borrow something.
C. To talk about the neighbors.
15. Where are the speakers?
A. In Sydney. B. In Chicago.
C. In London.
16.What is the woman going to do this Saturday?
A. Drink tea. B. Meet old friends.
C. Attend a party.
聽第10段材料,回答第17至20題。
17.How many hours is the Water World open on Tuesdays?
A. 10. B. 8. C. 6.
18.In which month can’t people visit the Water World?
A. February. B. March.
C. September.
19.Where can people see the short film about the sea?
A. In the Visitor Center.
B. In the dining room.
C. In different halls.
20.When must you arrive to have a good seat to see the dolphin show?
A. At 1:45 pm. B. At 2:15 pm.
C. At 2:45 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