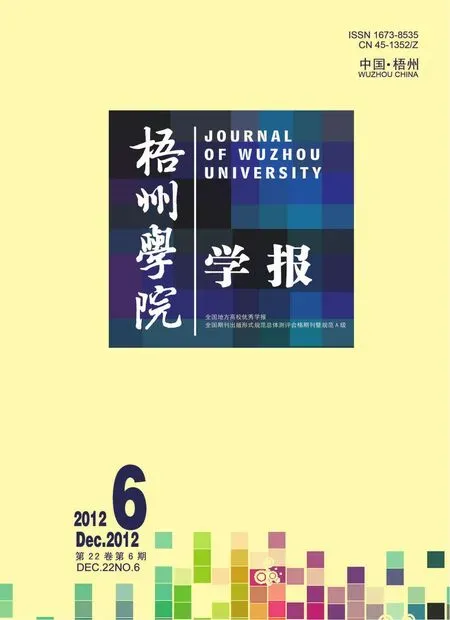量子力學中的若干基本概念
隆寅,韓鋒
(1.2.河池學院物理與電子工程系,廣西宜州 546300)
量子力學中的若干基本概念
隆寅1,韓鋒2
(1.2.河池學院物理與電子工程系,廣西宜州 546300)
量子力學中若干基本概念的理解經常存在著一些很難解釋的困惑,使得人們對這門學科整體產生了誤解。該文主要就波粒二象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對物理實在的認識、對坐標與動量的測不準關系的理解以及由此發展出來的互補原理及其哲學思想,進行了一些基礎性的討論。
量子力學;波粒二象性;測不準關系;互補原理
1 引言
量子力學和相對論是近代物理學的兩大支柱。而量子力學又由于其研究對象遠離我們熟悉的宏觀世界,其基本概念的革命性使很多學者甚感疑惑。以玻爾為首的哥本哈根學派和以愛因斯坦為首的一批物理學家,就量子力學的完備性問題曠日持久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就充分地證明了這一點。
量子力學在對微觀現象的描述上,給出了與經典觀點全然不同的圖景,從而引發了人們極大的困惑和爭論。現在的量子力學理論體系,是建立在五個基本假設基礎上的,這就是:1.波函數的幾率解釋;2.力學量的算符表示;3.態疊加原理;4.薛定諤方程;5.全同性原理。這些基本原理和從它們推出來的一系列推論,構成了量子力學的理論結構,它是自洽的,其數學計算結果也與實驗符合得很好,這一點已經得到學術界的公認[1]242。爭議主要發生在對量子力學若干基本概念的詮釋問題上[2]。
在對量子力學概念的詮釋問題上,愛因斯坦最不滿意的就是對波函數的幾率解釋,以及作為它的基礎與結果的波粒二象性和測不準關系。經過幾次論戰,愛因斯坦提出的一系列反例質疑都一個個地被玻爾所推翻,但他至死也不接受量子力學的統計解釋,相信量子力學的背后一定隱藏著決定論的東西,他的名言是:“上帝是不擲骰子的”。
從今天物理學的發展來看,量子力學的理論體系不但是自洽的,而且對它的詮釋也是完備的。大多數物理學家都已經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哥本哈根學派對量子力學基本概念的詮釋。愛因斯坦等人挑起的這場曠日持久的大論戰,則幫助人們逐步澄清了量子力學的許多基本概念,從而促進和推動了量子力學的發展。
現在,所有涉及物質屬性及其微觀結構的當代高新技術都是建立在量子力學的基礎之上的。電子計算機與信息技術是直接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的,沒有電子能帶理論,就沒有半導體集成電路,就沒有今天的電腦和手機。沒有能級間的“粒子數反轉”,就不能引發大量光子雪崩式的受激輻射——激光。沒有計算機輔助設計與制造技術(CAD/CAM技術),也就不會有自動化和機器人技術。當前人們特別關注的是建立在量子糾纏態基礎上的量子隱性傳輸技術,即“量子計算機”。雖然現在還處于實驗室階段,但量子密碼的不可破譯性則引起了人們很大的興趣。以上這些在實際應用中的大量事例,當然不是本文所要論述的主題,對它們哪怕是最粗略的說明,也要占去相當大的篇幅。但是,對于它們的物理能夠不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正確地剖析量子力學的基本概念就顯得特別重要。
2 關于微觀粒子的波粒二象性
德布羅意“物質波”的思想是在愛因斯坦“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并且微觀粒子的這種奇特性質最終導致了量子力學薛定諤方程的發現。關于實物粒子(如電子)是否也如光一樣具有波粒二象性的問題,實驗已經給出了無可置疑的證明。然而,這似乎才是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電子怎么可能既是粒子又是波呢?或者說,粒子與波這樣兩個互斥的形象怎么可能統一在一個微觀的客體上呢?如果真是這樣,那么物質的本性又該作何理解?
光的粒子性最早是愛因斯坦為解釋光電效應而提出來的。眾所周知,光的干涉現象和衍射現象充分說明光具有波動性,它其實就是電磁波。但在光電效應中,為了解釋“紅限”的存在,就必須假設光是一束粒子流(光量子流)。這樣一來,光在不同的實驗安排中,可以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形象——波動性和粒子性,所以說光具有波粒二象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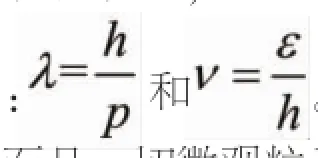
怎么理解波粒二象性?也就是說,微觀粒子究竟是什么?怎么理解它既是粒子也是波?這個問題逐層遞進地分析如下。
首先,微觀客體最終表現為粒子還是波,完全取決于實驗的布置。歸根結底,“我們想看什么,我們才能夠看到什么。”(倪光炯語)如果我們的實驗布置是單狹縫或雙狹縫,看到的就是粒子的波動性所表現出來的干涉和衍射現象。如果我們的實驗布置是一個散射實驗,比如盧瑟福散射,就必須把α粒子當作一個粒子來處理。更簡單的,我們控制電子發射裝置而讓電子幾乎一粒一粒地打在熒光屏上,在屏上留下的就是一個一個的光點,這正是電子具有粒子性的表現。由于不同的實驗布置,這兩種互斥的性質是不可能同時出現的。
話又說回來,在沒有具體進行實驗觀測之前,微觀客體究竟是以什么形態出現的?這是一個令人很難回答的問題。其實,早在康德的批判哲學中,這個問題已經說清楚了[3]。微觀客體在沒有通過某種操作對它進行變革之前,它是“自在之物”,客觀存在著但并不能給出任何信息,或者說它有可能被提取的信息都是潛藏著的。我們的實驗操作使這種“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這就成為我們所說的“現象”。所以惠勒說:“現象非到被觀察到之時,絕非現象。”一個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的事物在未被測量之前,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一種絕對的東西,不包含任何信息。在它被測量之后,由于測量的作用,我們觀察到的已不是“自在之物”本身而是“為我之物”的“現象”。換句話說,“自在之物”在未被測量之前是沒有性質的,在實施測量之后,物質就被賦予了意義,變成了“為我之物”。
微觀客體到底是粒子還是波,在沒有觀測以前,問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在觀測發生以后,它就是一種在宏觀上看來有時候像波,有時候又像粒子的東西。我們的波和粒子的概念都是來自宏觀經驗的經典概念,嚴格說來,它對微觀現象的描述是不適用的。對于微觀世界的現象,為了把它用我們宏觀人類所能理解的語言描述和表達出來,就必須不得已地使用已經習慣了的經典概念。微觀客體就是這樣一種有時候像宏觀的波,有時候又像宏觀的粒子的東西。打一個比方:從來沒有用過筷子的西方人,該怎么稱呼筷子呢?英語中筷子是“chopsticks”,chop是“劈”的意思,sticks是“木棍”的意思,那么筷子難道就是劈成的兩根木棍嗎?當然不是。可是說筷子就像劈成的兩根木棍也并無大錯,這就有如把微觀客體說成像粒子和波那樣的東西也沒有錯一樣。
有些人認為波粒二象性難以理解,所以在講量子力學時刻意避開它,而從幾率幅講起,其實大可不必[4]。有人比喻說:一個人表現為兒子,要看他是在父親面前還是在兒子面前而定。同樣的,一個電子表現為波還是粒子,也要看測量儀器是什么,這是理所當然的。我們再一次看到,科學的發展就是對常識的逐步跨越。當我們對微觀世界的圖景違反“常理”的困惑釋然以后,我們的認識也就跨進了一大步。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的這句話,就是波粒二象性本質的真實寫照。
3 測不準關系
uncertainty relation現在一般譯為不確定關系,目的在于回避其與測量之間的關系,試圖表明:不管測量還是不測量,有些物理量就是沒有確定的數值。從上面的分析可知,這種理解是不對的。正是測量這種變革,才造成了坐標與相應動量的測不準關系,以及時間與能量的測不準關系。“測不準關系”這個譯名比較準確地反映了量子力學測量問題的本質,也比較符合海森堡的原意。如果把它譯作“不確定關系”,反倒掩蓋了問題的實質,是很不可取的。現在,中國物理學名詞委員會已決定將“測不準”和“不確定”并用,在新版的《物理學名詞》上予以公布執行[5]。

剛開始海森堡是通過一些思想實驗來論證他的測不準關系,其中尤其是海森堡仔細分析過的“γ射線顯微鏡”理想實驗[6]。玻爾認為測不準關系在物理上的基礎就是微觀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其后,從E.Kennard(1927)開始,陸續對這個關系式給出了嚴格的數學證明,Kennard指出:不確定度數學意義其實就是方差,方差是樣本中各數據與樣本平均數的差的平方和的平均數。準確地說,是這個方差的平方根,稱為“標準差”,在物理上它一般被稱為“漲落”,它是這個力學量的測量值依一定的幾率分布圍繞平均值的彌散度。
一個粒子客觀存在著的位置坐標和相應的動量竟然是不可能同時準確測量的,這使人們大惑不解。這里所說的客觀性是指無論你是否對它進行測量,像坐標和動量這些量的值就是在那里存在著的,但是這個認識正確嗎?否。

為什么測不準關系來自波粒二象性,這還要多說幾句。對于一個粒子來說,它在空間的位置是與它的粒子性聯系在一起的,而相應的動量則與它的波性聯系在一起,這可以從物質波的波長很容易看出來。粒子性和波動性不能同時顯現,相應地,坐標和動量也就不能同時測準。
至此,我們明確了,測不準關系是微觀現象的本質反映,并不是由于儀器的精度不夠造成的誤差,無論儀器如何改進,精度再怎么提高,這個關系給出的限制是不可能消除的。因為它是一個本原性的東西,所以一般也稱它為“測不準原理”。
4 互補原理
以玻爾為首的哥本哈根學派對量子力學基本概念的詮釋,已經被大多數物理學家所接受,成為一種最有影響的觀點,被稱為量子力學的正統解釋,它也是大多數量子力學教科書所采用的解釋。在這個解釋中,波粒二象性和測不準關系是兩個支柱性的基礎,而玻恩對量子行為的幾率解釋則是它們的直接后果。把這些理論觀點概括上升到物理哲學層面的,是玻爾的互補原理。
互補原理認為,有些物理概念和物理圖景在經典物理學中本來是互相聯系、結合成為一個統一的觀點體系的,但在量子物理學中它們卻不能兩立,處于“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互斥關系之中。但是,這些互斥的概念和圖景又都不可缺少。只有在不同的條件下分別承認它們,才能構成對觀測對象的“完備的描述”,在這個意義上,它們又是互補的[10]。玻爾的互補原理使我們自然地聯想到哲學中的對立統一規律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陰陽學說,它們之間既有共同點,也有不同的地方。
對立統一規律(或者說“一分為二”)是說,任何事物都有互相對立的兩個方面,它們既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它們各以對方為自己存在的前提,并在一定的條件下向對立面轉化。任何事物中存在的這種矛盾的兩個方面,總是同時存在的,當一方消失以后,另一方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而同時消失。互補原理則認為,這樣互斥而對立的兩個方面,是可以不同時存在的。比如波粒二象性,當波性顯現出來的時候,粒子性是不顯現而潛藏著的。波性和粒子性將此隱彼顯、此顯彼隱地交替出現,不可兼得。正是這樣兩個不同時顯現的兩個方面,構成了對微觀客體的完整描述。

作為一個哲學原理和思想方法,互補原理的意義可能早已經遠遠超出了物理學,它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廣闊領域都有重要的啟發作用。它不僅揭示了對立面是統一的,還揭示了對立面如何統一的多種形式,這對辯證哲學是一個重大的貢獻。玻爾以他那追求真理的真誠精神和對世界和平的良好愿望指出,文化背景不同的民族之間往往都表現出一些相反相成的、既互斥又互補的特點,代表著一個世界整體的兩種互斥的圖像,然而它們又是互補的,因為只有它們的共存(互為補充)才給出了我們這個世界完整的圖像。互補原理揭示了世界的和諧,它也將有助于形成一個和諧的世界[12]。
[1][6]周世勛.量子力學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79:242,92.
[2]田松.為什么量子力學會引起我們的困惑——兼談玻爾的“現象”概念及互補原理[J].自然辯證法通訊,2010(5):32-33.
[3]韓鋒.自然科學的歷程[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282-283.
[4]關洪.光是一種概率波嗎?[N].科學時報,2006-12-07.
[5]王正行.建議“測不準”與“不確定”二詞并用[J].物理,2005(3):230.
[6]關洪.量子力學的基本概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182.
[7]E.H.威切曼.量子物理學[M].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18.
[8]倪光炯,王炎森.物理與文化[M].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288.
[9]倪光炯,陳蘇卿.高等量子力學[M].2版.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450-452.
[10]戈革.量子力學的興起和哥本哈根學派[J],華東石油學院學報,1984(增刊).
[11]韓鋒.試論互補原理—兼論量子力學的哥本哈根詮釋[J].科技導報,1993(9).
[12]韓鋒.物理哲學—觀控相對論的元物理學[M].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6:46.
O3
A
1673-8535(2012)06-0055-05
隆寅(1980-),女,壯族,廣西田陽人,河池學院物理與電子工程系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理論物理學。
韓鋒(1943-),男,山西文水人,河池學院物理與電子工程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理論物理學與物理哲學。
(責任編輯:高堅)
2012-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