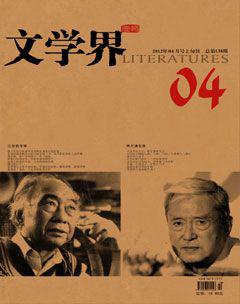作為抒情詩的散文化小說
施叔青 汪曾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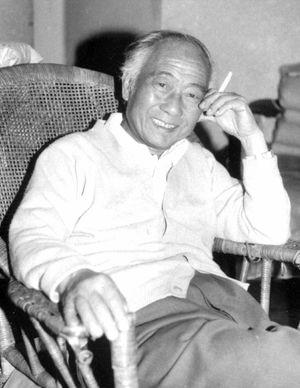
一、中國的各種運動,我是全經歷過的
施叔青:你是江蘇高郵人,出身當地的書香人家?
汪曾祺:祖父是有功名的,還是個會治眼病的大夫,我父親種花養鳥,斗蟋蟀,注重生活情趣,自己有畫室,從小我也學著涂鴉,日后把繪畫里的留白用到小說里來了。
母親去世得很早,記得父親糊了全套冥衣,用各色花紙,單夾皮棉,講究得很。啟蒙老師就是高北溟。《徙》里寫的都是真事,他教我們讀歸有光、“五四”時期作家的作品。
高中畢業,本想考杭州藝專,怕讓人瞧不起。十九歲獨自到香港,經越南坐滇越鐵路到昆明。得了瘧疾,差點沒能參加考試。我讀的是中文系,選了沈從文先生三門課,他教過我的事跡在《沈從文先生在西南聯大》一文提過。記得沈先生曾把我二年級的作業拿給四年級的學生去學去看,他也公開說我是他最得意的學生。
施叔青:西南聯大,的確出了不少人才。
汪曾祺:美國有人專門研究西南聯大的校史,才短短八年出的人才比清華、北大、南開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當時宿舍、教室條件都很差,宿舍是草棚頂,土墻,窗戶上也沒有玻璃,就是土墻上開個洞。搞戰期間,大家生活都很不安定,學生窮得不可想象,褲子破了拿根麻線扎扎。為什么能出這么多人才?我想當時集中了北方幾個大學最好的教授,學校校風自由,你愛講什么就講什么,誰也不管你。還有就是很多教授對學生實行天才教育。
施叔青:像沈從文先生的作文課。
汪曾祺:還有聞一多先生。
教授當中,只有朱自清先生上課是很認真的,他很不喜歡我,他說我不上他的課。我當時在學校里經常不上課,老是晚上到系圖書館去看書到三四點鐘,早上起來也不上課。
朱自清教宋詩,他的教書方法很正規,每次都帶一疊卡片,照著講,還留作業,月考。
施叔青:記得你寫的第一篇文章嗎?
汪曾祺:前幾年有的同學找了出來,其中有一篇《花園》,寫我們家廢棄的花園,帶點回憶性質,也有點描寫景色氣氛。最近編本集子,找出了一篇在二十四歲時候寫的小說,叫《小學校的鐘聲》,就是寫離開我們的縣里,在小鎮上遇到一個小學的女同學,含含糊糊一種情緒。當時很多人不同意我這種寫法,說這有什么社會意義?我的女兒說我這一篇寫得非常坦率。二十歲到二十三歲期間的作品,一個是不容易找,一個是太幼稚了。
施叔青:《職業》是何時寫的?
汪曾祺:大約1945年,已經畢業了。
施叔青:你是1958年才被打成右派,這很不尋常。
汪曾祺:當時每個單位都有指標,算算不夠,把我補上去了,就那么簡單。我寫過一篇很短的黑板報的稿子,對人事工作提出一點意見,這稿子還是當時黨支部動員我寫的,引蛇出洞嘛!
施叔青:當了戴帽右派,讓你下地勞動?
汪曾祺:嗯,到張家口附近農業科學研究所勞動,我主要分配到果園工作。《看水》那篇東西里的小孩實際上就是我。
施叔青:四年的下放,談談你的感受?
汪曾祺:從某個角度看當然是很倒霉了,不過,我真正接觸了中國的土地、農民,知道農村是怎么一回事。晚上就在一個大炕上,同蓋一個被窩,虱子很多,它們自由自在,從東邊爬到西邊的被窩去。農民與我無話不談,我確實覺得中國的農民,一身很沉重的負擔,他們和中國大地一樣,不管你怎么打法,還是得靠他們,我從農民那兒學到了許多東西。
施叔青:真正下去改造自己啰!
汪曾祺:對,當時的右派言論,讓我從心里覺得是錯的,應該下放勞動改造。我體力不是很好,但盡力去做,能扛兩百七十斤重的麻袋,現在要我扛二十七斤,我也扛不動。我這個人在逆境中還能感受生活的快樂,比較能適應。
施叔青:你一直有親民思想……
汪曾祺:主要是我小時候的環境,就是生活在這些人當中,鋪子里店員、匠人、做小買賣的這些人。你發現沒有,我筆下的小民百姓,沒有壞人,有人寫評論,說我將所有人物雅化。
施叔青:你一生當中沒遇見壞人?
汪曾祺:當然有,但我不愿去寫他。為什么?這跟我儒家的思想宗旨有關。我下放勞動,艱苦受難,也就是那么一回事,捱過了。
施叔青:聽說你還是個馬鈴薯品種專家?
汪曾祺:我是治晚瘟病的能手,硫酸銅加石灰水噴在馬鈴薯葉子上,不能太稀,要恰巧留在葉子上,才能起作用。勞動是很辛苦的,克服了,也挺有意思。我有本書沒出版,挺遺憾,我畫過一本馬鈴薯圖譜,現在還很懷念那種生活,每天天剛亮起來,地上全是露水,摘幾片馬鈴薯葉子,采一朵盛開的馬鈴薯花,對著畫。那時沒人管我,也不用開會,也不用檢查,自由自在,正巧碰到三年自然災害,也沒怎么挨餓,畫完了就把它吃掉了。(笑)
施叔青:“文革”時,你的遭遇尤其傳奇。
汪曾祺:你也聽說了,“文革”一開始,我是老右派,自然跑不掉,江青親自下命令把我解放的。
施叔青:為什么?
汪曾祺:因為她要用我,是在1968年,“文革”開始不久,所以我在牛棚里待的時間不是很長。1962年初我到了京劇團,從張家口回北京,原來單位不接收我,恰巧我寫了《范進中舉》的劇本,京劇團有名額,我就去了。
后來,我寫《沙家浜》,江青說唱詞寫得不錯,她就記得我了。
我的解放是非常富于戲劇性的,白天我還在勞動抬煤,有人跟我說,你不用抬煤了,回去寫個檢查,下午開會,你講一講,我就回去。后來又說你不用檢查了,上去表個態,幾分鐘就行了。“京劇團要使用我,我一定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完了”。接著通告,你解放了,今天晚上江青要審查《山城旭日》這個戲,你坐在江青旁邊看戲。(大笑)我當時囚首垢面,臨時去買了一件新衣裳穿上。
施叔青:那時候的感覺?
汪曾祺:只覺得如在夢中,不真實,弄不清楚這是怎么回事,中國的各種運動,我是一個全過程。江青垮臺之后,我還得檢查一次。(大笑)審查我跟“四人幫”的關系,還給我立一個專案。我說,我是工作人員,她要我寫戲,要我怎么寫,我就怎么寫,那時候我不寫,不這樣寫,不可能嘛。
施叔青:你對于“文革”的否定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汪曾祺:很明確的時候,還得是中央對“文革”的否定。
施叔青:你比較后知后覺。
汪曾祺:那個時候有些現象你覺得莫明其妙,你也是跟他跑。另外,我一開頭被關在牛棚里,外面什么事都不知道。
施叔青:你的作品中,直接反映“文革”的,好像極少?
汪曾祺:寫了一點,后來沒選入集子里。寫了一篇九百字的小小說《虐貓》,背景是“文革”搞運動,貼大字報,開批判會,孩子們也跟著起哄,學校的玻璃打碎了,路燈的燈泡打破了,能玩的大都試過了,后來想出法子去虐待一只貓,把胡子剪掉了,貓爪放入瓶子蓋……最后想從六樓把貓扔下摔死,一看宿舍前面圍了一圈人,其中一個孩子的父親從六樓跳下去,尸體被搬走了,這幾個孩子以后不再摔貓了,把貓放了。
施叔青:這是寫“文革”對孩子心理的一種摧毀,總的來說,你的作品還是遠離政治的!
汪曾祺:我不會寫政治。《虐貓》里政治只是一個背景,不是題材本身。有些作家現在還誤解,寫改革文學,還是本末倒置。
你看我寫作也是斷斷續續,1947年出版《邂逅集》,六十年代初期,寫過一本《羊舍的夜晚》,以后停筆,一直到1979年。長期以來,強調文藝必須服從政治,我做不到,因此我就不寫,邏輯是很正常的。
那時你要搞創作,必須反映政策,圖解政策,下鄉收集材料,體驗生活,然后編故事,我卻認為寫作必須對生活確實有感受,而且得非常熟悉,經過一個沉淀過程,就像對童年的回憶一樣,才能寫得好。
二、《受戒》是寫初戀的感覺
施叔青:你寫童年,寫故鄉,寫記憶里的事物與人,是因為……
汪曾祺:因為印象深,記得很清楚,時間久了,慢慢琢磨,對人物掌握比較準確,對那個社會也有我自己的看法。
施叔青:在這么冷硬的制度下,你的作品卻令人感到溫馨。
汪曾祺:這與個人的氣質有關系。世界上都是悲劇作家也不恰當。有人說我從來沒有對現實生活進行過嚴格的拷問,我是沒有這個勁頭,我承認這樣的作家是偉大的作家,但是我不屬于這類作家,這點我很有自知之明。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但是我不排斥冷峻思考的作品。有一位學化工的大學生看了我的《七里茶坊》后給我寫了封信說,“你寫的那些人就是我們民族的支柱”。我要寫的就是這些東西,樸素的、有希望的。
施叔青:沈從文筆下寫的主要是農民、士兵,你從小在市鎮上長大,你寫的是———
汪曾祺:小市民,我所熟悉的市民。好些行業我真的非常熟悉。像《異秉》里的那個藥店“保全堂”,就是我祖父開的,我小時候成天在那里轉來轉去。寫這些人物,有一些是在真的基礎上稍微夸張了一點。和尚怎么還可以娶個老婆帶到廟里去,小和尚還管她叫師娘,和尚賭錢打牌,過年的時候還在大殿上殺豬,這都是真的,我就在這小廟里住了半年,小英子還當過我弟弟的保姆。
施叔青:想到《受戒》,你說過是寫你的初戀,一個幾十年前的夢……
汪曾祺:不是寫我的初戀,是我初戀的一種朦朧的對愛的感覺。
施叔青:你企圖在《受戒》里表現什么?
汪曾祺:我有一種看法,像小英子這種鄉村女孩,她們感情的發育是非常健康的,沒有經過扭曲,跟城市教育的女孩不同,她們比較純,在性的觀念上比較解放。《大淖記事》里那些姑娘媳婦敢于脫光了下河洗澡,有人說怎么可能呀?怎么不可能,我都親眼看到過。
施叔青:農村婦女心理比較健康,擺脫禮教束縛。
汪曾祺:這是思無邪,詩經里的境界。我寫這些,跟三中全會思想解放很有關系,多年來我們深受思想束縛之害。
施叔青:《受戒》的和尚廟有無任何影射意義?
汪曾祺:有很多人說我是沖破宗教,我沒這意思。和尚本來就不存在什么戒律,本來就很解放。很簡單,做和尚是尋找一個職業。
我在張家口戴右派帽子下放勞動,當地的青年媳婦很多,經常跟小和尚有關系,那個地方有個口頭語:“石頭壘墻墻不倒,大官跑了娘不找,和尚進門哥不饒。”
施叔青:《大淖記事》里,貞操觀念也頗淡薄,是不是和婦女從事挑夫的行業有關?
汪曾祺:可能是。那里娶媳婦沒有拿花轎抬的,都是自己走來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個媳婦,在丈夫之外,再“靠”一個,不是稀奇事。
施叔青:你這樣寫出,人家不會以為你在侮辱工農兵的形象?性開放的現象,在你小說里,只限于勞動階層,對知識分子從不觸及,為什么?
汪曾祺:讀書人表面上清規戒律,沒鄉下人健康,其實他們曖昧關系還是很多。我寫《受戒》,主要想說明人是不能受壓抑的,應當發掘人身上美的詩意的東西,肯定人的價值,我寫了人性的解放。有一個公社的書記,他說很奇怪,老中青三代都喜歡你的作品,還告訴我一件事情,有一天開公社干部會議,第二天整理會場準備再開會,看見桌上的膠臺布上寫的,是《受戒》里小英子跟小和尚的對話,一個人寫一句,全能背下來,可見人人追求一種優美、自然的情緒。
施叔青:引發你創作的,是先有意象的觸動,或是人物?
汪曾祺:作家想寫一篇作品,總有他創作的契機,不完全是一樣的,可能是一句語言而引起,可能是某個時刻,可能是一個愿望。一般來說,引發我的還是人物,先有人物,可加上想象,沒有情節可編情節,沒有細節可編細節,最后決定作品的是作家的思想。
三、小說的散文化
施叔青:你說過“我的一些小說不太像小說,有些只是人物的素描……”談談你對小說下的定義?
汪曾祺:一定要我下個定義,小說應該就是跟一個可以談得來的朋友很親切地談一點你所知道的生活。
施叔青:散文也有這種功能,何必動用小說?
汪曾祺:它總是有點人為的熱情,有點故事,小說總是有些虛構,總是有些編造。
施叔青:你說過“散文詩和小說的分界處只有一道籬笆,并無墻壁”。
汪曾祺:我一直以為短篇小說應該有一點散文詩的成分,把散文、詩歌融入小說,并非自我作古,屠格涅夫的《獵人筆記》有些近似散文,契訶夫有些小說寫得輕松隨便,實在不大像小說。阿左林的小說稱之為散文未嘗不可,小說的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說的一種(不是唯一的)趨勢。
施叔青:你的《釣人的孩子》《職業》《求雨》這幾篇作品,真有散文詩的味道———印象派詩的寫法。
汪曾祺:這和我的氣質有關。拿繪畫來說,我也愛看金碧山水和工筆重彩人物,但我畫不來,我的調色碟里沒有顏色,只有墨,從渴墨焦墨到淺得像清水一樣的淡墨,我的小說逸筆草草,不求形似。
施叔青:中國作家中,具有散文化的小說,近代廢名該是始作俑者吧?
汪曾祺:廢名的《竹林的故事》可以說是具有連續性的散文詩。蕭紅的《呼蘭河傳》全無故事,沈從文的《長河》是一部相當特別的長篇,沒有大起大落,沒有強烈的戲劇性,沒有高潮、懸念,只是平平靜靜,漫漫向前流,這是一部散文化的長篇小說。
如果說,傳統的、嚴格意義上的小說有一點像山,而散文化的小說則像水。
施叔青:再往上推,跟中國古代的散文有淵源吧?
汪曾祺:對。我喜歡宋人筆記勝于唐人傳奇,除了短,它還不像唐人傳奇那樣偏重講故事。
施叔青:你似乎很強調小說的重點不在于講故事,因此情節的安排被認為很次要?
汪曾祺:我承認我不善于講故事。散文化的小說最明顯的特征就是結構松散,你拿莫泊桑和契訶夫的小說比較一下,就可看出結構上的異趣。莫泊桑、歐·亨利耍了一輩子結構,但他們顯得很笨,實際是被結構耍了。這兩個作家的小說,人為的痕跡很重。倒是契訶夫,他好像完全不考慮結構,寫得輕輕松松,隨隨便便,瀟瀟灑灑,他超出了結構,于是結構轉變多樣。
打破定式,是這類小說結構的特點,古今中外作品,不外是呼應和斷續,超出了,便在結構上得到大解放。
施叔青:你不喜歡在小說里說故事,所以故意把外在的情節打散,而專寫些你經歷過的人與事。
汪曾祺:對。我覺得情節可以虛構,細節絕不能虛構,必須有生活的感受。
施叔青:散文化的小說,還具有哪些特性?
汪曾祺:一般不寫重大題材。在散文化小說作者的眼里,題材無所謂大小,他們所關注的往往是小事,生活的一角落、一片段。即使有重大題材,他們也會把它大事化小。
散文化的小說不大能容納過于嚴肅的、嚴峻的思想,這類作者大都是性情溫和的人,不想對這世界做拷問和懷疑。許多嚴酷的現實,經過散文化的處理,就會失去原有的硬度。魯迅是個性格復雜的人,他的《故鄉》《社戲》里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惆悵和凄涼,如同秋水黃昏,沈從文的《長河》,牧歌式抒情成分大大沖淡了描繪農民靈魂被扭曲的痛苦。
散文化小說是抒情詩,不是史詩,它的美是陰柔之美、喜劇之美,作用是滋潤,不是治療。
施叔青:對人物的塑造刻畫呢?
汪曾祺:這類作者不大理解,也不大理會典型論。我同意海明威的說法:不存在典型,典型是說謊。要求一個人物吸進那樣多的社會內容,是很困難的,透過一個人物看出一個時代,這只是評論家分析出來的。
散文化小說的人像要求神似,輕輕幾筆,神完氣足,《世說新語》就是最好的范本,這類作品所寫的常常是一種意境。
四、字里行間,無字處皆有字
施叔青:“常常是一種意境”,有人評你的小說沒有主題?
汪曾祺:我沒寫過無主題的小說。我用散文式的語言來說明我的主題。作者完成一篇作品的深、淺色調,決定于作者對生活本身的思索。我不同意用幾句話就把主題說清楚,我認為應該允許主題相對的不確定性和相對的未完成性。“文革”時我搞的樣板戲,江青每一個戲都規定這個戲的主題是什么,必須明確,形成我后來對“明確”兩個字很反感,主題一明確就簡單化了、膚淺化了。
施叔青:都說得很清楚了,就表面化了,你好像要給讀者留下回想的余地?
汪曾祺:作者寫完了這篇作品,他對這段生活的思考并未結束,不能一了百了,只能說思索到這里。剩下的,讀者可繼續對我所提供的生活思索下去。作者不是上帝,什么都知道。我最反對從一個概念出發,然后去編一個故事,去說明這概念,這本身是一種虛偽的態度,作品要容許一定的模糊性,不是故弄玄虛。我這個說法可能兩種人都不同意,正統派的那些人認為怎么可以說得不清楚;另外年輕的也不同意,他們就是不要那個思想。
施叔青:你說過“除了語言,小說就不存在”。談談對語言的要求?
汪曾祺:我是繼承了中國傳統語言表達特點,語言本身是一種文化現象,我也受到西方語法的影響,但更多的是晚唐詩的影響。
我愿意把平淡和奇崛結合起來,一般來說,我的語言是流暢自然的,但時時會跳出一兩個奇句、古句、拗句,甚至帶點洋味,敘述方法上有點像舊小說,但是有時忽然來一點現代派的手法。但我追求的是和諧,希望容奇崛于平淡,納外來于傳統,能把它們揉在一起。
施叔青:你的文風很平淡———
汪曾祺:老年之后才逐漸平淡,但不能一味地平淡,流于枯瘦,枯瘦是衰老的跡象。年輕時的語言是很濃的,而且很怪。我要求語言要準確、樸素。我下去生活的那段期間,和老百姓混在一起,驚訝地發覺群眾的語言能力不是一般知識分子所能表達的,很厲害,往往含一種很樸素的哲理,用非常簡樸的語言表達出來。我覺得新潮派的年輕作家,要補兩門課,一門是古典文學的課,一門是民間文學。
施叔青:民間文學……
汪曾祺:比如說佛經的文體,它并不故作深奧,相反的,為了使聽經的人能聽懂,它形成獨特的文體,主要以四個字為主體,我嘗試用通俗佛經文體寫了一篇小說《螺螄姑娘》,其實各種文體都可以試試。
施叔青:你認為字里行間,無字處皆有字,是否太玄了?
汪曾祺:一點也不。清朝的包世臣,有個精辟的比較,他以趙子昂跟王羲之的書法來比,他說趙子昂的字寫得很平均,好像是跟夫人過窄胡同,彼此互相依賴,但是爭先恐后,扯著往前走。王羲之的字像老頭帶著小孫子,顧盼有情,痛癢相關。單獨的語言是沒有美的,必須組織在一起,產生一種運動,產生一種關系,產生內在的流動。
施叔青:怎樣才能使你的文字功夫達到那個境界?是否天生的?
汪曾祺:可能有天賦的成分,但主要是后天涵育的功夫,我妻子常說,怎么不把我這套功夫傳給我兒子,怎么傳授呢?
我認為作者敘述的語言和他創作的氣氛一定要跟人物本身協調。文學和繪畫永遠不能等同。我到桂林去,我覺得桂林“宜畫不宜詩”,文字是靠感覺的,起的作用不一樣,各有所長,各有所短。
施叔青:你作品中有不少是組合式的,一般都是三篇,是否有一定聯系?思想上或題材上?

汪曾祺:原來也不是有意識寫那種組合式的小說,通常有內部的聯系,就是三篇的思想有它一定的關系。比方說《釣人的孩子》《撿金子》《航空獎券》,其實都是寫的貨幣,寫貨幣對人的影響,這三個故事沒什么關系。
施叔青:三個故事都極短?
汪曾祺:我對短小說興趣很大,也不是自我獨創的。聽人說,中國現在寫筆記型小說的,一個是孫犁,一個是我。對這桂冠我不準備拒絕,真是可以這樣說,而且影響了一些人。我希望小說不要寫得很長,短并不只是篇幅上的問題,也不是說現在讀者太忙了,讀不了長的作品,這個邏輯不能成立。當代作家對小說形式希望有所突破,嘗試新的文體、新的寫法,寫得少了其實是寫得多,寫得短了其實是寫得長,短了容量就更大了,留給讀者余地,讀者可以在你的基礎上進行他們的創作。作者跟讀者共同完成的,應該留給他一部分創作的余地,你都給他說了,還要讀者干什么,就沒有用了。
施叔青:小小說是———
汪曾祺:是短篇小說越來越講究留白,像繪畫一樣,空白的藝術,小小說本來就是空白的藝術。
施叔青:總結一下你小說、散文所傳導的感情?
汪曾祺:歸納一下,可分三種,一種屬于憂傷,比方《職業》;另一種屬于歡樂,比方《受戒》,體現了一種內在的對生活的歡樂;再有一種是對生活中存在的有些不合理的現象發出比較溫和的嘲諷。
我的感情無非憂傷、歡樂、嘲諷這三種,有些作品是這三種感情混合在一起的。
施叔青:你寫小說也編京劇劇本,兩者異同在哪里?
汪曾祺:劇本、戲劇和小說不一樣,戲劇是不容深思的藝術,它當場給人感受,不可能供人思索。“寫詩文不能寫盡,只能說二三分,寫戲必須說盡,十分就得說出十分”,這是很有道理的。戲劇的結構是屬于一種建筑,小說的結構是樹木。
施叔青:最近上演的京劇《一捧雪》,本子是你改的,因你不滿意別人曲解這個戲,變成斗爭什么的。
汪曾祺:我改這個本子,目的很清楚。為什么莫成輕易從死,很簡單,奴才應該替主人去死。我改的時候,基本沒大動,只在莫成替主人去死,獄卒給他喝酒時,加了大段唱工,把莫成的心理層次一層層揭開。另外我在這戲里加了兩個報幕,讓他們對劇情有所評述……
施叔青:非常布萊希特的手法……
汪曾祺:這樣讓看老戲的過癮,也吸引年輕觀眾。京劇的出路,就是要吸收現代主義的東西,老的東西不能一下改,改得面目全非,我在演出之前的告觀眾書上寫道:
“望你們一面看這個戲,欣賞唱腔、做工的同時,能思索一下歷史,為什么會發生這樣的現象,莫成為什么作出這樣的決定?希望你們想一想過去,也想一想今天。”
結果上座很好,觀眾大叫好,這在改編的戲是少有的現象。京劇的問題很嚴重,編導人才太缺乏、藝術觀念太狹隘,沒有追求,一代不如一代,十分危險。
(原載《上海文學》198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