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huì)變局中的知識(shí)論爭(zhēng)
劉昕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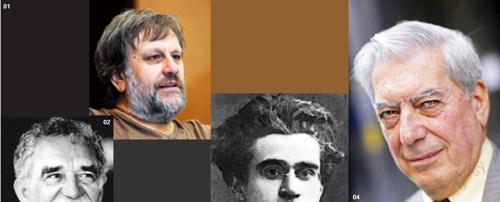
1976年,“拉美文學(xué)爆炸”的兩位主將,也是至交好友加西亞?馬爾克斯與巴爾加斯?略薩在墨西哥的一家影院門口大打出手。關(guān)于這次決裂,坊間傳聞是因?yàn)榕耍俜秸f法是友誼破裂,但是也就是在那個(gè)揮拳相向的夜晚之后,這對(duì)曾經(jīng)的親密戰(zhàn)友漸行漸遠(yuǎn),最終“大路朝天,各走一邊”。馬爾克斯始終無悔青年時(shí)代的選擇,堅(jiān)守左翼政治的抱負(fù),不遺余力地抨擊美國對(duì)于拉丁美洲的政治經(jīng)濟(jì)殖民。略薩則迅速切換跑道成為新自由主義擁躉,甚至一度代表右翼政黨角逐總統(tǒng)候選人。
2010年當(dāng)略薩終于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jiǎng)加冕,跟馬爾克斯“打了個(gè)平手”之后,全世界的讀者都翹首期待這兩位才華橫溢的拉美作家冰釋前嫌,共同沐浴在諾貝爾的普世榮光中。書商們更是加緊策劃兩人的合集,推動(dòng)互作序言的“文字外交”。不過當(dāng)事人似乎并不領(lǐng)情,依舊以一副老死不相往來的樣子,繼續(xù)別扭著。第三世界知識(shí)分子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chǎng)、道路選擇,成為這場(chǎng)持續(xù)30多年的分道揚(yáng)鑣背后,真正的春秋大義。
文壇風(fēng)云
有“學(xué)術(shù)搖滾明星”之稱的斯洛文尼亞學(xué)者齊澤克,曾提出一個(gè)觀點(diǎn)來理解知識(shí)群體的論爭(zhēng):即那些表面看上去似乎純屬秀才掐架的口水官司,其實(shí)內(nèi)里聯(lián)系著遠(yuǎn)為寬廣的社會(huì)空間,牽涉著政治乃至經(jīng)濟(jì)實(shí)力的明爭(zhēng)暗斗,同時(shí)也意味著文化格局的重新排兵布陣。正是社會(huì)群體、政治聯(lián)盟不斷地利益分化,使得知識(shí)群體對(duì)不同立場(chǎng)、不同道路的選擇,最終以文字硝煙乃至文化風(fēng)云的樣態(tài)浮出歷史地表。所以,當(dāng)保羅?德曼在二戰(zhàn)時(shí)期的反猶寫作,觸發(fā)了整個(gè)學(xué)界對(duì)于解構(gòu)主義批評(píng)的質(zhì)疑與辯護(hù)時(shí);當(dāng)“卡索爾大戰(zhàn)”挑起人文-自然知識(shí)分子兩軍對(duì)陣時(shí),那并非是簡單的文人相輕,也絕不是厚黑學(xué)的文壇實(shí)踐,而是以晴雨表般的敏銳泄露了真切的政治動(dòng)蕩,見微知著地率先提示了正在分化重組中的利益格局。在此,走上“占領(lǐng)華爾街”街頭,忙著將政治事件理論化的齊澤克,也再度打開了理論事件政治化的空間與希望。
倘若切換回中國頻道,無論如何都不能錯(cuò)過的人物恐怕要算魯迅,他當(dāng)之無愧應(yīng)是現(xiàn)代文壇上參與論戰(zhàn)最多、最長、也最知名的文化人。晚近研究對(duì)于魯迅嬉笑怒罵的雜文,以及他貫穿了上世紀(jì)幾乎整個(gè)20~30年代的筆頭論戰(zhàn),或是抱著同情之理解的態(tài)度,舉證魯迅大義當(dāng)頭,絕無私怨;或是在和平主義的旗幟下,評(píng)判魯迅刻薄有余,溫厚不足。如果以齊澤克的觀點(diǎn)看去,“雜文”本就是一種現(xiàn)代性文體,它恰好是現(xiàn)代知識(shí)分子在現(xiàn)代傳播媒介(報(bào)紙)中,與他所處時(shí)代的社會(huì)思想、文化現(xiàn)實(shí),遭遇并發(fā)生有機(jī)聯(lián)系的重要而有效方式。硝煙四起的文字疆場(chǎng),正是激蕩時(shí)代里社會(huì)癥候的表征,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多重角逐在這個(gè)疆域里公開扭結(jié)、顯影放大。
上個(gè)世紀(jì)20~30年代的中國,外國勢(shì)力忙著尋找本土代理人,民族資本家急于站穩(wěn)腳跟擴(kuò)充實(shí)力。遺老與海龜、舊派文人與新文化旗手,不約而同地在“五四”的余波裊裊中,重新辨明方向,再度整裝待發(fā)。現(xiàn)代化的泰坦尼克巨輪已然出港,若隱若現(xiàn)的冰山各就各位,蠢蠢欲動(dòng),危機(jī)四伏。
就在此時(shí),一個(gè)幽靈,一個(gè)叫魯迅的幽靈,在中國文壇上游蕩。他直指文化保守主義的軟弱—“明知道讀經(jīng)不足以救國”,卻以明確的后撤姿態(tài),朝向傳統(tǒng)文化尋求庇佑。魯迅與學(xué)衡派的論爭(zhēng),不僅漸次拉開了20年代中國的文化帷幕,也使得從此以后,張皇四顧下傳統(tǒng)文化的每一次復(fù)興,都不得不面臨魯迅早已戳破的幻象:在被無情卷入資本主義現(xiàn)代性進(jìn)程之后,未經(jīng)染指的所謂國學(xué)國粹早已無處可循,更沒有如處子般純潔的傳統(tǒng)文化,撫慰知識(shí)分子們?cè)陲L(fēng)雨飄搖中忐忑不安的心情。如果已經(jīng)沒有回頭路可以返折,那么中國以何種方式完成現(xiàn)代性轉(zhuǎn)型,加入全球性民族-國家角逐,依靠何種力量,團(tuán)結(jié)哪些階級(jí),就成為曾經(jīng)同仇敵愾的新文化陣營里,每個(gè)知識(shí)分子必須重新做出的思考與判斷,這也必然導(dǎo)致整個(gè)知識(shí)界在持續(xù)的論戰(zhàn)中,走向不斷分化與裂變。
對(duì)于大多漂洋過海、負(fù)笈歐美的現(xiàn)代中國知識(shí)分子來說,西方是一個(gè)多重糾葛的沖突所在,相對(duì)于“落后”的中國,它是文明的至高點(diǎn),面對(duì)民族家國,它又是殘暴的侵略者,在仰視西方文明的目光中,直面帝國的陰影與血腥,這是一個(gè)知識(shí)挑戰(zhàn),亦是一個(gè)政治困境。同時(shí),對(duì)于大多出身富庶之家的知識(shí)階層來說,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態(tài)度與軍閥官僚、強(qiáng)權(quán)政府劃清界限,未嘗不是亂世離恨的首選之策,但是敢不敢、能不能、愿不愿肯定群眾運(yùn)動(dòng),將他們作為未來中國的政治主體,并與他們并肩作戰(zhàn),則是一個(gè)實(shí)實(shí)在在的政治抉擇。
社會(huì)變局
所有這些論爭(zhēng)中,不是沒有人世糾葛,也絕非全無利益纏繞,龍爭(zhēng)虎斗、陳倉暗渡恰恰是社會(huì)變局的產(chǎn)物,是知識(shí)論爭(zhēng)背后真正的歷史主謀。今天我們依然繞不開魯迅,或情愿或不情愿地提起他,究其原因,不僅在于他的骨頭是最硬的,更因?yàn)樵跉v史的每一個(gè)關(guān)口,社會(huì)的每一個(gè)拐點(diǎn),他都以親歷者少有的清醒,參與了歷史進(jìn)程,不向權(quán)勢(shì)投降,也不向利益低頭,所以他確乎有資格站在現(xiàn)代中國激蕩風(fēng)云的入口處,說一句“一個(gè)都不寬恕”的終結(jié)之語。魯迅“一個(gè)都不寬恕”,照樣也不需要被寬恕,對(duì)于現(xiàn)代中國來說,他就是一道血淋淋的傷口,不結(jié)痂不愈合,每到文壇風(fēng)云又起的時(shí)候,看著知識(shí)界再度舊瓶裝新酒般地一路左搖右擺。
完全從道德學(xué)、倫理課的角度,評(píng)價(jià)歷史進(jìn)程中知識(shí)分子的堅(jiān)守與妥協(xié),抗?fàn)幣c沉默,不僅有失公允,更有偷梁換柱、欲蓋彌彰之嫌。知識(shí)論爭(zhēng)在幾度沉浮中,始終是隨著歷史主體更迭交替,在社會(huì)進(jìn)程中調(diào)整轉(zhuǎn)向。
“知識(shí)分子”是一個(gè)現(xiàn)代的概念。借用皮埃爾?布爾迪厄刻薄但不乏真知灼見的諷刺是,誰會(huì)關(guān)心有關(guān)知識(shí)分子的話題呢,也只有知識(shí)分子自己。縱觀思想史哲學(xué)史,提出過、研究過知識(shí)分子問題的,也多是轉(zhuǎn)折年代里,被何去何從的選擇焦慮癥困擾的學(xué)者們。這其中不能不提及的是葛蘭西關(guān)于“有機(jī)知識(shí)分子”的構(gòu)想。在葛蘭西看來,正是社會(huì)群體的不斷分化,多重利益的盤根錯(cuò)節(jié),使得知識(shí)分子的概念,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擴(kuò)充,學(xué)者、藝術(shù)家、媒體人、電影從業(yè)者都在成為廣義上的知識(shí)分子,當(dāng)他們自覺參與到特定利益集團(tuán)的構(gòu)建與發(fā)展中時(shí),就擔(dān)當(dāng)起了“有機(jī)知識(shí)分子”的角色,所以在當(dāng)代社會(huì)利益主體不斷多元化的背景下,每一個(gè)階層聯(lián)盟、每一個(gè)身份群落都擁有自己的“有機(jī)知識(shí)分子”。這一方面回應(yīng)了齊澤克的觀點(diǎn)—表面上的筆墨官司里,激蕩著社會(huì)變局,時(shí)代風(fēng)云;同時(shí)也意味著,知識(shí)分子將以各種各樣的文化生產(chǎn),參與到歷史進(jìn)程中,智識(shí)生活并非被隔絕在校園高墻和特定專業(yè)領(lǐng)域之內(nèi)。
我們?cè)?jīng)在柏林墻倒塌、冷戰(zhàn)終結(jié)的喜悅中,期待一個(gè)一笑泯恩仇的喜劇故事。誰知倏忽之間,全球性的貧窮柏林墻、隔離帶正在重新堆砌起來,在新一輪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政治動(dòng)蕩中,貧富對(duì)峙、資源爭(zhēng)奪以空前的緊迫性,再度提醒我們,百年來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模式之痛還在繼續(xù)腫脹,中國現(xiàn)代化的進(jìn)程依舊步履沉重。曾經(jīng)迫使魯迅著文回應(yīng)的挑戰(zhàn),照樣還在困擾著當(dāng)代中國的知識(shí)分子們。所以,知識(shí)論爭(zhēng)有待在政治化的語境中,重新被評(píng)估與書寫,重要的不是分出勝負(fù),而是讓矛盾糾葛、利益沖突浮出歷史地表,再度改寫知識(shí)生產(chǎn)的起點(diǎn)與地平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