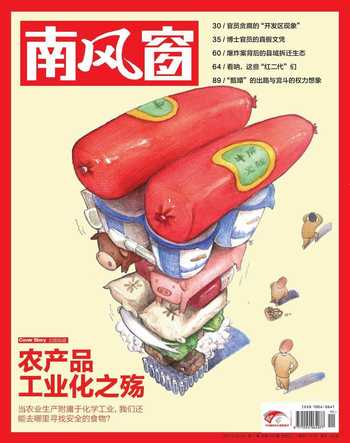反壟斷的雙重標準
邢少文
5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出臺《關于審理因壟斷行為引發的民事糾紛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這是《反壟斷法》自2008年8月1日實施以來,最高法首次出臺相關司法解釋。根據該司法解釋,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因壟斷行為遭受損失等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應該受理;而達成壟斷協議的壟斷企業,一旦被訴應承擔舉證倒置責任。
有意思的是,并非所有人都那么痛恨壟斷,對于這一司法解釋的出臺,有人肯定,也有人持反對態度。反對者認為所謂的“壟斷協議”很難界定,多數時候它其實是市場自發的行為,而不是勾結行為,他們引用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納德·科斯的話說:“我被《反壟斷法》煩透了。假如價格漲了,法官就說是‘壟斷定價;價格跌了,就說是‘掠奪定價;價格不變,就說是‘勾結定價。”
壟斷有市場自然形成的壟斷和行政壟斷之分,在中國,還有行政壟斷和國企壟斷的結合。在反壟斷的立場上,常會衍生出雙重標準:有人堅決反對行政壟斷和國企壟斷,但不反市場壟斷;有人卻只反市場壟斷,不反行政壟斷和國企壟斷。這樣的雙重標準,吊詭得很。
自由市場信仰者認為市場形成的壟斷會因技術創新和其他競爭者進入而消解,不用反。但問題在于沒有法制約束的市場經濟往往充滿叢林法則,利用自身壟斷地位強行限制其他競爭者和傷害消費者合理權益的行為常有發生,這本身并不利于競爭和創新。
如果說反市場壟斷的行為有可能會傷害競爭,只是在于反壟斷法案對于壟斷行為認定上如何更加仔細甄別而已,而不是放縱。
而在一部分計劃經濟支持者的眼中,私人資本只會無限追逐利潤,形成資本霸權的壟斷,侵害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他們只反市場壟斷,不反行政壟斷和國企壟斷。
中國《反壟斷法》從討論到出臺到實施,正在驗證這樣一種思維,《反壟斷法》第7條規定實際已給予行政壟斷和國企壟斷很大的豁免權:“國有經濟占控制地位的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行業以及依法實行專營專賣的行業,國家對其經營者的合法經營活動予以保護,并對經營者的經營行為及其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依法實施監管和調控,維護消費者利益,促進技術進步。”
國企壟斷的背后往往伴隨著行政壟斷,這一條款實際也為國企壟斷做了解脫,雖然個別條款上適用于國企,但國企壟斷往往借代表行業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名義得以豁免。《反壟斷法》實行4年來,反的基本是跨國公司和小公司,大型國企安然無恙。
既然國企代表了“人民的利益”,它的發展壯大和保持壟斷地位就具有了天然的合理性,占據了道德高地。然而實際上,它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凌駕于人民利益之上。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反壟斷法》實際是一部阻礙競爭的法律,只拍蒼蠅,不打老虎,對行政壟斷和國企壟斷的豁免本身就阻礙了競爭。
對于壟斷地位的辯解,往往賦予了國企社會責任之說,最近,在陜西和山東,分別發生了地方電廠、民營發電廠與國家電網武斗事件。民營發電廠提供了更便宜的電價,國家電網壟斷地位受到威脅。而發改委官員則表態說,民營發電廠不履行環保責任。
問題是,環保監管責任不是政府部門嗎?如果說國企和民企在環保責任履行上有雙重標準,那是誰制造了這種雙重標準?誰給予了保護?
維護真正平等有序的競爭,既要反市場壟斷,也要反行政壟斷和國企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