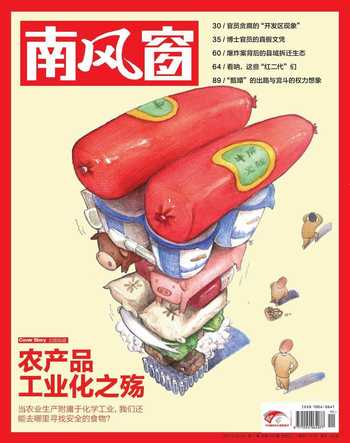中國周邊的“FTA”戰爭
雷志華
在5月13日第五次中日韓峰會上,三國領導人同意年內啟動中日韓自由貿易協定(FTA,Free Trade Agreement)談判。僅僅一天后,中韓第一輪雙邊FTA談判在北京舉行。顯然,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導致雙邊和區域FTA日漸活躍,這一趨勢在東亞這個最具經濟活力的地區表現得尤為明顯。
東盟內部以及東盟與中、日、韓分別簽訂FTA之后,東亞FTA談判的焦點開始轉向中日韓之間。作為東亞前三大經濟體,中日韓雙邊或三邊FTA談判的結果,無疑將影響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和走向,但不要忘了還有一個推銷“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的“區域外超級大國”,它加入東亞峰會之后,原本就躊躇不前的“東盟+中日韓(10+3)”、“東盟+中日韓澳新印(10+6)”等一體化方案也平添變數。對于大國來說,FTA戰略從來都不只是經濟問題,而帶有強烈的政治動機。美國跟以色列、約旦簽訂雙邊FTA,就與其中東政策相配套。現階段美國力推的TPP,同樣也超越了經濟范疇。
韓國:東亞FTA領跑者
韓國是目前東亞地區唯一同時與美國和歐盟簽訂雙邊FTA的國家,正是這一點奠定了韓國在東亞FTA的領跑者地位。從韓國政府的FTA戰略來看,與大型、先進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締結FTA是其重要原則。“在FTA戰略上,韓國的做法很聰明,希望能在東亞FTA問題上充當‘輪軸國角色。”中國社科院亞太所所長李向陽在接受《南風窗》記者采訪時說,“從理論上說,‘輪軸國在雙邊FTA中獲益最大,所以,韓國在與美國、歐盟和中國這世界前三大經濟體談判時,都選擇雙邊FTA。”
從金大中、盧武鉉到李明博政府,韓國的FTA戰略經歷了從“防御型”到“進取型”的轉變;在談判策略上,也經歷了“以東亞為中心”到“先外圍后東亞”的轉變。韓國在東亞首個FTA談判對象是日本。出于恢復經濟和防范新的金融危機的考慮,1998年金大中訪日時提出了建立韓日FTA的構想,此后兩國智庫著手相關研究。2003年盧武鉉上臺后,韓日之間進行了6輪FTA談判,終因日韓產業競爭性大于互補性,且韓國處于明顯的弱勢而作罷。隨后韓國將目光轉向外圍,與智利、新加坡、東盟以及美國簽署了首批雙邊FTA。李明博任內,久拖未決的韓美FTA獲得美國會批準,韓國與歐盟的FTA簽署并實施。
中國目前是韓國第一大貿易伙伴,2011年中韓雙邊貿易額為2200億美元,韓國順差478億美元。中國在韓國的對外貿易中地位舉足輕重,但這并未影響韓國推行FTA戰略的節奏,韓國也沒有因此把中國列為FTA優先談判對象。“從韓國的FTA戰略來看,跟美國談完后,與歐盟談判時就有了更多的籌碼;跟歐盟談完后,與中國談判時就有了更多優勢。”李向陽分析說,鑒于中國迫于美國TPP的壓力而急于推進東亞區域經濟合作,韓國在中韓FTA談判中可能獲得更多優勢,比如在農產品問題上迫使中國做出更大讓步。“如果韓國跟美國、歐盟和中國都簽訂FTA,與日本談判時韓國的優勢就更明顯了。”
日本:糾結的貿易大國
中韓FTA談判提上議事日程,對日本企業界刺激不小,這也是日本對中日韓FTA的態度從觀望轉為積極的重要原因。中國是韓、日的最大貿易伙伴,韓日兩國企業競爭優勢有著高度的重合性,如果韓國搶先與中國簽訂FTA,那么日本企業在中國市場將面臨巨大壓力。早在2004年,韓國智庫就發表報告稱,韓日FTA必須推遲到韓中簽署FTA之后進行,或者是韓中日FTA建立之后。從目前的情況看,在爭奪中國市場方面,韓國按計劃邁向既定目標,而日本已經先輸一局。
與韓國一樣,日本的FTA戰略也經歷了一個轉變的過程,不過是從“定位明確”轉變為“搖擺不定”。2002年10月,日本外務省制定了《日本的FTA戰略》,決定以韓國和東盟為中心,在東亞和世界范圍內開展雙邊自由貿易,推動建立東亞自由貿易區。李向陽分析說,日本原本是想通過主導東亞經濟一體化,來復制上個世紀80年代美日歐經濟“三足鼎立”的局面,但在經濟規模被中國超越后,日本對主導東亞經濟合作越來越力不從心了。
日韓FTA談判陷入僵局,主導東亞經濟一體化無望,日本既定的FTA戰略事實上已經瓦解,在東亞FTA競爭中也亂了陣腳。針對中國倡導的“10+3”框架,日本針鋒相對地提出“10+6”方案,客觀上遲滯了東亞經濟一體化進程。而當奧巴馬政府宣布推動TPP談判,野田首相一改其前任的模糊態度,表現出參與TPP談判的積極姿態。可是,在TPP問題上遭遇國內強烈反彈,中韓FTA談判即將啟動的情況下,日本的視野又回到了東亞。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區域合作室副主任沈銘輝對《南風窗》記者說:“我們通過測算發現,日本無論加入中日韓FTA還是加入TPP,在經濟收益上基本相當,僅從經濟角度看,日本就左右為難。”而在加上“中國”這個政治因素后,日本的兩難處境更明顯。“日本立場舉棋不定,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國內對國家的重新定位存在分歧。”李向陽分析說,如果日本局限于東亞合作,未來就可能依附于中國,與美歐形成“三足鼎立”的將是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所以日本選擇跟美國合作。但與美國合作的同時,日本的商界又不愿意放棄中國這個日益擴大的市場,所以日本在中美之間搖擺。
從目前日本官方的表態來看,日本對中日韓FTA和TPP都持開放態度,甚至可能同時推進。李向陽認為,日本做兩手準備,為的是在談判時對美國打中韓牌,對中韓打美國牌。中國社科院亞太所安全外交室學者楊丹志表示,如果日本加入TPP,事實上將形成美日主導的局面,而美日發揮主導作用的TPP,將是一個把中國排除在外的地區貿易體制,這可能導致東亞的分裂。
美國力推TPP的虛實
5月8日至18日,參與TPP談判的9國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小鎮達拉斯舉行第12輪談判。這輪談判距今年3月在澳大利亞舉行的第11輪談判僅兩個月,足見奧巴馬政府對于年底前就TPP達成協議的緊迫感。
TPP的創始國是新加坡、新西蘭、文萊和智利,這四國在2005年簽署協議,致力于通過締結優惠貿易安排,在APEC內部推動貿易自由化。但直到該協議2006年生效,美國一直都未將其納入考慮范圍。隨著華爾街金融危機的蔓延,出于推動美國出口、防止經濟惡化的考慮,時任布什政府的貿易代表蘇珊·施瓦布,在2008年9月宣布美國將加入TPP。由于布什政府任期即將結束,美國在參與TPP方面沒有實質性動作。
奧巴馬起初沒有對TPP表現出明顯的興趣,但進入2010年,奧巴馬政府“重返亞洲”戰略成型,TPP也成為這一戰略的重要支柱。這一轉變的動機是,防止美國在東亞區域合作中被邊緣化。里根政府時期的國務卿詹姆斯·貝克20多年前曾發出警告,如果美國允許在太平洋畫一條線,把美國和亞洲國家隔離開,那將是美國的戰略失誤。克林頓政府從1993年開始重視亞太經合組織(APEC),目的也正在于避免此一后果。
但克林頓政府整合亞太的努力不太成功,9·11事件后美國的注意力又轉向反恐。正是在此期間,東亞區域合作如火如荼,而且中國在其中的影響力日漸突出。布什政府后期重新把注意力轉向亞太,并在2006年組建了一個研究小組,評估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的可能性。2007年悉尼APEC峰會上,布什政府正式提出構建FTAAP。奧巴馬政府上臺后,把TPP作為打造FTAAP的手段,在“重返亞洲”戰略的包裝下強勢推出。
美國力推TPP有經濟動因,也有戰略考量。沈銘輝認為,美國是想在中美實力對比出現變化的情況下,用TPP來提前制定一個適用于未來的貿易規則,通過保證美國企業的競爭力來維護美國的國家競爭力。李向陽說:“美國人也清楚,中國經濟規模超過美國只是時間問題,美國真正擔心的不是這一點,而是經濟規模被超過以后,中國會否對美國主導的國際規則和國際體系提出挑戰,這是中美之間真正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