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再出發
趙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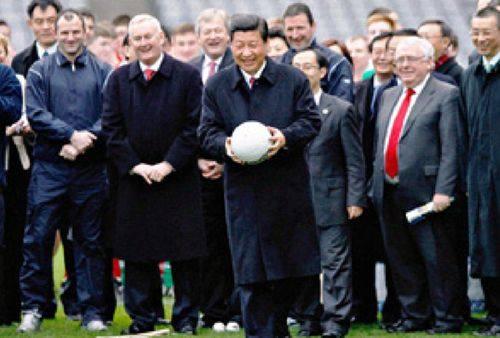
和最近幾次黨代會一樣,改革同樣是十八大政治報告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字眼之一。執政黨的十八大之所以舉世矚目,一個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人們希冀借此觀察中國未來改革的走勢。
眾所周知,因為社會利益、價值觀的多元化,以及既得利益問題,中國的改革事業的確遭遇到了比較復雜的情況。其中,有的改革遲遲沒有進展,引起了社會的不滿;有的改革在方向上存在重大分歧,甚至難以調和;有的改革則需要比較長的時間周期,短期之內很難取得重大成效,而民眾的期望形成了比較大的壓力。
但毫無疑問的一點是,今天的情況,不是要不要改革的問題,而是如何盡快在重要領域改革上取得共識和突破,以避免陷入“改革看上去無處不在,實則名存實亡”的尷尬境地。這是執政黨回應“世情、國情、黨情繼續發生深刻變化”情況下挑戰的需要,是讓社會各界對于國家未來形成穩定預期的需要,也是讓國際社會進一步“理解”中國的需要。在中國,沒有什么比推動改革更能考驗執政黨回應挑戰的領導力。
改革論述的變化
與十七大相比,十八大的政治報告論述到的改革內容,絕大多數保持了延續性,但亦有值得注意的新的變化。十八大報告對于改革事業的最終目標進行了界定:“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所謂定型,意味著圍繞科學發展的制度體系的確立,換句話說,就是更加清晰的“中國模式”的出場。正因如此,十八大報告論述的改革內容必然會涉及一些事關改革走向的根本問題。
比如,十八大期間,11月9日十八大新聞中心組織了第一次記者招待會。當時有外國媒體記者提問時質疑中國在政治體制方面沒有太大的改革和變化,中組部副部長王京清就回答說:“在政治體制改革這個問題上,我們黨的態度是鮮明的,決心也是堅定的,推動是有力的。”十八大報告第五部分題目中加入了“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字眼。與十七大相比,十八大報告對于政治體制改革的論述增加了不少可以期待的內容,比如,“支持人大及其常委會充分發揮國家權力機關作用,依法行使立法、監督、決定、任免等職權,加強立法工作組織協調,加強對‘一府兩院的監督,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還包括降低人大代表中領導干部比例、提高專職委員比例等)。
“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這句話用在這里的改革內容也合適。“全口徑”包括了政府的非稅收入,2012年政府的稅收收入增速比2011年下降,一些地方非稅收入猛增,人們普遍擔心存在“過頭稅”和亂收費、亂攤派、亂罰款。而決算的軟約束也導致了持續多年的年底突擊花錢現象,帶來極大的財政浪費。更關鍵的是,約束政府權力的膨脹,不僅需要“人人起來監督政府”,更關鍵的是權力之間的制衡。從預算民主入手推動國家民主化水平的提高,這在社會各界也有著廣泛的共識。新華網報道中,就引用專家的話說,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執行,應當提高立法機關行使預算權的能力、加強管理,勇于行使否決權。
圍繞政府的改革,在十八大報告關于改革的論述中分量明顯加重。對于經濟體制改革,報告明確將其核心問題界定為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對于行政體制改革,報告提出: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繼續簡政放權,推動政府職能向創造良好發展環境、提供優質公共服務、維護社會公平正義轉變。這些都是十八大報告新出現的改革論述(十七大報告在提及行政審批時只是提出要減少和規范行政審批)。
這意味著,在中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方向20年后,政府改革仍是改革的重中之重。“簡政放權”的背后是這些年政府權力再次擴張的事實。著眼于部署未來5年甚至10年改革發展戰略的十八大報告,亦不能不對此明確回應,否則,科學發展的制度體系的“定型”就會大打折扣,“壞的市場經濟”卻可能得到固化。事實已經證明,“自己改自己”是很難的,也很難持續。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是,十七大和十八大報告都提出要減少“領導職數”,說明這一問題的存在很“頑強”。“自己改自己”已經遇到了天花板,如果沒有更強有力變量(比如人大的監督)的引入,具體的改革可能就會淪為中繼站式的層層傳達,但沒有實質性變化。
改革的中央權威
十八大報告對于社會的重大改革關切亦進行了回應,比如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改革征地制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比例分配,等等。和正在進行的絕大多數改革一樣,新增加的改革內容,在確立目標上相對容易,但同樣也面臨著如何深化的瓶頸。
對于改革推進的阻力,人們一般都會歸結為既得利益的阻撓。值得思考的是,既得利益問題,任何時候都會存在,為什么有時候改革就成功了,有時候就失敗了,今天的改革為什么尤為艱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在于,隨著權力碎片化趨勢,改革本身實際上也在碎片化。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司長管改革”現象。
十八大報告提出,要維護中央權威。這也應當體現在改革事業上。改革的頂層設計不能最終只是變成(中央)部門的頂層設計;改革的中央權威也不能最終只是變成(中央)部門的權威。在過往采訪中,記者了解到,有的改革人士感覺到現在的改革是“宏觀上讓改,微觀上管住”,這其實就是改革權力碎片化的表現。同樣,地方先行先試,本是改革取得突破的一個方法,在實踐中也往往更多的是爭取更多政策優惠、項目和財政支持,而體制改革本身受制于各種部門化的管制,步履艱難。
因此,在十八大報告提出“完善體制改革協調機制,統籌規劃和協調重大改革”之后,有學者提出,應當設立專司改革的協調機構,擺脫部門自身利益對于體制改革的困擾,類似于當年的體改委。但改革的“超級機構”是否也會落入權力部門化的窠臼,仍是個問號,畢竟今天的改革環境已非當年可比。
在有的綜合性改革中(比如醫改),最常見的改革統籌和協調機制是成立領導人擔任組長、相關部門組成的領導小組。地方政府采取的也是類似的模式。這可能仍是未來統籌改革的主要思路,即領導人主持、多部門聯動推進改革。
但可以肯定的是,改革設計提高獨立性,才能更好地維護改革的中央權威,反過來也是一樣,設計的獨立性也需要中央權威的保證。這和在分配領域,切蛋糕的不能分蛋糕,分蛋糕的不能切蛋糕是一個道理。只要是涉及“自己改自己”內容的,都應當提高設計的獨立性。
獨立性和專業化是聯系在一起的。比如對于政府職能轉變,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周志忍教授就認為,政府職能轉變尚停留在“行政格言”的水平,還沒有一套具有可操作性的“示標體系”,對政府職能結構特征進行量化顯示。有了一套量化指標,比如政府總支出在各個職能領域(社會保障、生產性投資等)的配置,才能對政府職能結構現狀有科學、準確的理解,對于改革步驟的設計才可能量化。
總之,今天改革的再出發,起點就是建立體制改革協調機制,即對改革本身進行一次改革,挽回改革本身的信譽和公信力。在改革所涉利益錯綜復雜的情況下,這對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