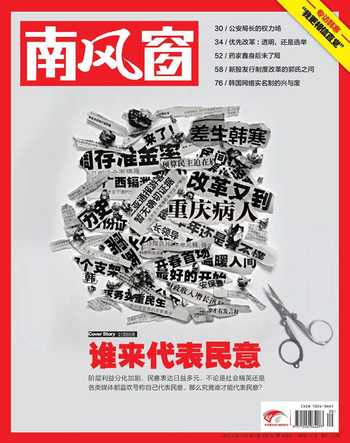民族國家的重生
丹尼.羅迪克
我們這個(gè)時(shí)代的其中一個(gè)根本性謬論就是全球化正迫使民族國家走向消亡。我們被告知說交通與通訊技術(shù)革命已經(jīng)消弭了邊界,讓世界變得更小。從跨國監(jiān)管者網(wǎng)絡(luò),國際公民社會(huì)組織到多邊機(jī)構(gòu),新的治理模型正在超越并取代那些只為單一國家服務(wù)的立法者。而據(jù)說各國國內(nèi)的政策制定者們在面對全球市場之時(shí)也相當(dāng)軟弱無力。
但全球金融風(fēng)暴卻粉碎了這一謬論。是誰救助了銀行,注入流動(dòng)性,啟動(dòng)財(cái)政刺激計(jì)劃,為失業(yè)者們提供了社會(huì)安全網(wǎng),并以此遏制了災(zāi)難的進(jìn)一步升級?是誰重新制定了金融市場的監(jiān)管規(guī)則以避免重蹈覆轍?是誰在事態(tài)惡化之時(shí)承擔(dān)了大部分罪責(zé)?答案總是那么一個(gè):國家政府。跟它們比起來,G20、世界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巴塞爾銀行業(yè)監(jiān)管委員會(huì)都只是些跑龍?zhí)椎摹?/p>
即便是在區(qū)域性機(jī)構(gòu)勢力相對強(qiáng)大的歐洲,主宰政策制定的還是國家利益和各國國內(nèi)的政策制定者。但即便民族國家得以生還,其本身的聲譽(yù)卻依舊岌岌可危。知識(shí)界對它的攻擊主要集中于兩種形式:首先,在那些將政府視為商品、資本和人才自由流動(dòng)障礙的經(jīng)濟(jì)學(xué)家眼中,必須阻止國內(nèi)政策制定者利用法規(guī)和壁壘來干涉全球市場,市場才能管好自己,并在自救的過程中建立一個(gè)更統(tǒng)一也更有效率的世界經(jīng)濟(jì)。
但除了民主國家之外,誰能提供市場所需的法則和監(jiān)管?放任主義只能換來更多的金融危機(jī)和更強(qiáng)勁的政治反作用力。此外,這還需要將制定經(jīng)濟(jì)政策的任務(wù)委托給那些跨國機(jī)構(gòu)里的技術(shù)官僚,這些人完全與政治絕緣——而這一立場又嚴(yán)重限制了民主以及政治問責(zé)制度的作用。
簡而言之,放任主義和國際技術(shù)官僚并不能提供一個(gè)民族國家以外的可靠替代品。事實(shí)上,只要我們依然缺乏全球治理的有效機(jī)制,民族國家的失效對全球市場都沒什么好處。
其次,有些世界倫理學(xué)家一直在譴責(zé)人為設(shè)立的國家邊界。哲學(xué)家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說,通訊革命已經(jīng)產(chǎn)生了一個(gè)“全球受眾”并因此為一種“全球倫理”打下了基礎(chǔ)。如果我們以某個(gè)國家來定義自己,那么我們的道德也會(huì)局限于一個(gè)國家。而一旦我們逐步將自己與整個(gè)世界結(jié)合起來,我們的忠誠也將因此獲得延伸。同樣,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jiǎng)獲得者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也認(rèn)為我們擁有“多重身份定義”—民族的,宗教的,國家的,本地的,職業(yè)的和政治上的—而其中許多定義都是無國界的。
很難說上面這些說法有多少是一廂情愿,又有多少是基于身份定義和情感的真實(shí)轉(zhuǎn)變。因?yàn)橛姓{(diào)查發(fā)現(xiàn)人們對民族國家的情感依附依然相當(dāng)強(qiáng)烈。
幾年前,“世界價(jià)值觀調(diào)查”行動(dòng)詢問了數(shù)十個(gè)國家的民眾對本地社區(qū),國家和世界整體的情感依附狀態(tài)。不出意外,那些將自己視為某國公民的人數(shù)遠(yuǎn)遠(yuǎn)高于將自認(rèn)世界公民者的數(shù)量。但令人吃驚的是,在美國、歐洲、印度,中國和其他大部分地區(qū),人們更傾向于認(rèn)為自己是某一國的公民,而不是屬于某一當(dāng)?shù)厣鐓^(qū)。
而調(diào)查也發(fā)現(xiàn)年輕群體,高等教育群體,以及那些自認(rèn)上流階級的人都傾向于將自身與世界聯(lián)系起來。但仍然難以界定哪些人類群體對全球社會(huì)的情感依附會(huì)高于對國家的依附。
雖然交通和通訊的成本都大幅下降,但地理的作用卻并未磨滅。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和政治活動(dòng)依然圍繞著某些偏好,需求和歷史軌跡展開,而這些基本要素互相之間差異極大,無法在全球?qū)用嫔蠈?shí)現(xiàn)統(tǒng)一。地理距離也跟半個(gè)世紀(jì)前一樣深刻影響著經(jīng)濟(jì)交換行為。甚至連互聯(lián)網(wǎng)也不像想象中那樣沒有邊界:一項(xiàng)研究發(fā)現(xiàn)美國人更喜歡訪問那些鄰近國家的網(wǎng)站,即便在排除了語言,收入和其他因素的影響之后也是如此。
問題在于我們依然沉迷在民族國家衰落的謬論之中。政治領(lǐng)袖們以此為自己的軟弱無力辯護(hù),知識(shí)分子們?nèi)栽诨孟胫莻€(gè)可行性極低的全球治理方略,而全球競爭中的失敗者也把矛頭指向移民或者進(jìn)口產(chǎn)品。一旦說起重新向民主國家授權(quán)的話題時(shí)那些達(dá)官貴人們避之唯恐不及,好像這會(huì)傳染瘟疫似的。
但可以肯定的是,情感依附和身份定義的地理因素不是固定不變的,事實(shí)上它一直都隨歷史的進(jìn)程不斷改變著。這意味著我們不應(yīng)完全否定一種真正的全球意識(shí)以及跨國政治社群在未來出現(xiàn)的可能性。
但當(dāng)今的挑戰(zhàn)無法依靠那些尚未設(shè)立的機(jī)構(gòu)來應(yīng)對。今時(shí)今日,人們依然要從本國的政府那里尋求解決方案,而這也依然是集體行動(dòng)的最佳選項(xiàng)。民族國家可能是法國大革命留給我們的遺產(chǎn),但它也是如今我們唯一能依靠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