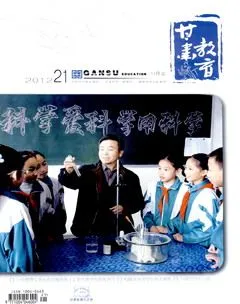對“求學之痛”的另類思考
文雨
10月4日發生在云南省彝良縣龍海鄉的山體滑坡,最終導致18名8至12歲的小學生遇難。那里不久前剛剛遭遇了一場地震,這些孩子在地震中安然無恙,卻被另一場“意外”奪取了生命。在國慶長假的旅游喧囂聲中,這起嚴重災害很快便淹沒在了各種各樣的假日信息當中。
這一事件讓人不由想起了汶川地震,想起那些被瞬間倒塌的教學樓掩埋了的眾多生命。看到那樣的場景,任何一個有人性、有良知的人,內心都會承受極大的痛楚。記得當時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在如此強烈的地震面前,如果一定要房倒屋塌的話,我們寧愿相信,承載著這些花季生命的校舍是最后一個倒下去的,否則我們的內心將永遠無法安寧。時至今日,我們確實沒能擺脫留存于心底的那種深深的悲哀。
現在,這樣的場景又一次出現在我們面前,而且是在舉國上下享受快樂假期的時候,在學校本不該上課的時候。
也許,這只是一場天災,但在天災的背后,總是閃現著“人禍”的影子。而這樣的“人禍”,卻又無法確切地指向某個人或某些人,因為它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現行體制的缺陷,整個社會人本理念和人文關懷的缺失,教育的完全功利化等,都在發揮著相應的助推作用。
雖然在我們的每所學校里都可以看到有關教育方針的表述,但現實情形下,我們始終搞不明白教育最終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我們教育的對象,是一個個有著喜怒哀樂的鮮活的生命個體,還是工業化生產線上需要統一加工的產品?我們的學校,是以孩子的健康快樂成長為目標,還是為了達成某種功利目的,把他們當作會說話的智能機器,按照成人的意愿,變成應試的工具?
“天堂里沒有做不完的作業”,這是對汶川地震遇難孩子的最后告慰。網傳的這句話,曾經讓無數人傷心落淚。但時過境遷,我們已經沒有了為此而作進一步反思的欲望,也無暇靜下心來對以往的所作所為加以審視:究竟是什么重要的東西,需要以犧牲孩子的快樂童年為代價?與生命的價值相比,還有什么是不可以忽略的?比如剛剛遭受了地震災害的學校,少上幾節課又有什么關系呢?據媒體對災害現場的報道,那些被山體掩埋在教室里的孩子,在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仍然保持著讀書握筆的姿勢。當悲劇定格成這種景象,我們是否還能心安理得地把它當作一次純粹的自然災害,一次湊巧的“意外事件”?
在一個物化了的浮躁社會當中,應該沒有多少人能夠停下腳步去嚴肅認真地思考人生,思考生命的真正價值所在。在現實生活的各個層面,由于對所謂“成功”的畸形追捧,使得重“術”輕“道”成為了一種普遍社會現象。人們執著于對各種技能、技巧、手段等“術”的追逐,而忽略了人生之“道”,即建立在人性基礎之上的人生方向、理想追求和精神境界。而教育因為承擔了“改變命運”的“崇高”使命,便在關乎人生成敗的競技場中扮演起了某種悲情角色。教育已不再是完善自我、健全人格、提升生命品質的需要,而是改變個人和家庭命運的希望所在。所以接受教育、學習知識本身也就變成了一種謀生之“術”。而這種“術”的價值,又以考試成績的形式來體現。所以,所謂“知識改變命運”,自然也就變成了“考試改變命運”,求學求知的目的也就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教育本身也就成為了各種利益交織的綜合體,從而實現了本質上的異化。
人不能“不學無術”,不能沒有安身立命的基本技能,但人生更不能缺失了應有之“道”,不能沒有基于人性之上的正確的人生理念與價值追求,不能讓生命迷失了方向。對于我們的下一代而言,以考試為目的的書本知識的學習,不應成為他們童年生活的全部,更不該把它作為未來是否成功的唯一前提。“風物長宜放眼量”,應該從生命的完整鏈條中把握人生的走向。如果我們懂得了這一點,就不會在人生的某一個節點上,因一時一事的得失而心神不寧、焦慮不安,非要想方設法找補回來不可。對孩子們的成長來說,生活本身讓他們學到的東西,可能遠比那些看似重要的課程有用得多,也深刻得多。
但是我們確實病了,病得有些不可理喻。我們眼前所呈現的,依然是“沉舟側畔千帆過”的景象,沉痛慘烈的悲劇,根本不足以改變類似情況的繼續發生,因為它已是一種社會常態,盡管不時遭遇“意外”,卻不會給現行秩序帶來多少沖擊。所以,包括遇難者在內的所有孩子,都不可能明白為什么非得這樣“學并痛苦著”,甚至要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寧可終生無“道”,不可一日無“術”,這是一種十分可怕的社會價值取向。當我們的教育缺失了應有的“道”,完全淪落為功利的“術”的時候,各種悲劇的發生似乎是在所難免的。